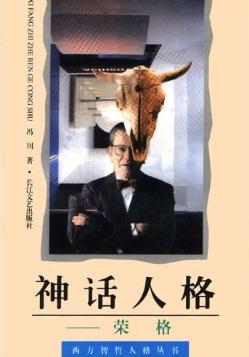人格裂变的姑娘-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去女修道院上音乐课。
海蒂的梦想破灭了。海蒂自己也病了。她得了舞蹈病,一种使她扭曲抽搐的肉体的病痛。但也有精神因素。这种精神神经病闹得愈来愈凶,使一家人在上楼时先得脱了鞋子,以免惊扰海蒂。全家的盘子也得放在法兰绒上面,因为海蒂受不了那盘子碰击的咯吱声。这些让步虽然同家人的缺乏教养不甚协调,但在她病重时始终如此。
为梦想破灭而进行的反击,并不是公然反抗,不也是彻底对立,而是通过开玩笑或恶作剧这类小动作来进行的。海蒂成为家中常讲使人难堪的话或常提出使人难答的问题的孩子。法语叫作enfant terrible,意思是爱磨人的儿童。有一个常开的玩笑,与海蒂到牧场牵牛回家的任务有关。牧场离家不远,在埃尔德维里市的边缘地区。她一路上东逛西荡,甚至顺便探亲访友,而安德森一家和这些奶牛都等得急不可待。
还有一个玩笑是专门冲着温斯顿来的。他是卫理公会唱诗班的指挥。海蒂被他指派来拉那教堂管风琴的风箱。有一个星期日,还剩下最后一首赞美诗没有唱,海蒂就跑掉了,扔下那风箱和她父亲不管。温斯顿·安德森身穿他那艾伯特王子式的外套,刚刚举起指挥棒准备指挥唱诗班高唱入云,而那管风琴却哑然无声。他那漆黑的眼珠里差一点冒出火来。
当她父亲年过五十,开始感到他在战争中受的老伤闹腾起来的时候,海蒂又一次反击了。他的肩部吃过一颗子弹,一直没有取出,如今影响了血液循环,引起两腿肿胀,肿得非要两个人才能把他抬起。当他开始饮酒止痛时,他老婆和孩子吵吵嚷嚷起来,家里就不存酒了。但当温斯顿设法自己弄到了酒时,家里就选海蒂来侦察。这位侦探发现钢琴后面的搁板上放着满满一排的酒瓶子,便得意洋洋地发问:“音乐家藏酒瓶子还会藏到哪里去呢?”她父亲曾使她遭受挫折,如今她也要使他尝尝挫折的滋味。
在她父亲生前,她对他满怀怨恨。在他死后,她把心里的怨恨变成了偶像崇拜和病态的依恋。在她爱抚他遗下的吸烟服时,这种病态依恋表现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有时海蒂说:她有点“麻烦事”,应归咎于她父亲。她从来没有说这麻烦事究竟是什么,但凡认识她的人也都知道她的确有问题。这麻烦事集中体现在海蒂由一本杂志上剪下来并与其他大量纪念品一起保存的一张相片上。这是一个站在篱笆旁的有魅力的姑娘的相片。标题是:不,她并不特别被人所爱。她感到了这一点。
海蒂·安德森不被人所爱,也不能去爱别人。她自己缺少教养,也不去教养别人。她自己在大家庭中是一个孤僻的人,她后来就在感情上去孤立她的独生女儿,由于音乐事业的梦想破灭而引起的愤怒,终于使西碧尔成为发泄的对象。
艾莲这位母亲,在海蒂嘴里,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她没有什么感情方面的特殊问题,只是在听任她丈夫在家中实施暴政方面过于迁就了些。但四个儿子似乎有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而且传给他们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自杀。在八个女儿中,有四个(其中包括海蒂和大女儿伊迪丝)都是行为放肆,性情反复无常的。伊迪丝更是家中女孩的暴君。另外四个女儿则过于驯良、过于沉默寡言、过于与世无争,而且全都嫁给了暴虐的夫丈。最小的妹妹费,体重达二百磅。
海蒂和伊迪丝,在身材、面容和脾气方面都非常相象。后来,她们都患有相同的症状:剧烈头痛、极高的血压、关节炎和含含糊糊的所谓神经质。海蒂的神经质是在突然辍学后开始的。海蒂的精神分裂症始于四十岁,即西碧尔诞生之时,这是确切无疑的。但不清楚伊迪丝是否也患精神分裂症。
伊迪丝的几个儿子有溃疡病和哮喘病等各种身心相关的疾病。她的女儿曾有一些无名的病痛,后来她成为一个宗教狂,并参加了一个信仰治疗小组,居然神气地宣称自己恢复了健康,但这位宗教狂的女儿得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病,终生处于半病残状态。伊迪丝的一个孙女几乎患上了海蒂的全部肉体疾病和感情方面的问题,只是程度较轻。
与西碧尔的疾病有关的,更重要的是有两个家庭成员………海蒂最小的弟弟亨利·安德森和伊迪丝的孙女丽莲·格林表现出多重人格(至少是双重人格)的迹象。
亨利有时会突然离家出走,消声匿迹,并由于记忆缺失而无法回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有一次,他还染上了肺炎,当一位救世军①工作人员找到他时,他正发烧说胡话。后来在常规检查他的衣物时发现了他的身份证,才把他送回埃尔德维里。
丽莲已经结婚,并有子女三人,常常不打一声招呼便弃家外出。如此发作多次以后,她丈夫干脆雇了一个侦探去追踪她,把她带回家来。
亨利和丽莲的情况,提示西碧尔的疾病有一种遗传易感性。但威尔伯医生始终认定她的病根不在于遗传,而在于幼年时代的环境。
安德森在埃尔德维里的家,看起来远不象是精神神经病的温床。因为,在西碧尔每年夏天访问埃尔德维里两周的时间里,一切都洁净无瑕,连海蒂的暴虐和变态也完全停止了。在这里,西碧尔的虚拟世界似乎变成了现实。
这里的阿姨和舅舅搂她,吻她,把她举在半空,专注地倾听她的歌唱和朗诵,并说她所做的一切都妙不可言。
如果西碧尔不去电影院,那么,这次访问就不能算是尽善尽美。她的姨妈费,在无声电影时代担任钢琴伴奏。西碧尔坐在琴凳上,贴着她的姨妈。电影院虽然没有观众,电影虽然没有放映,钢琴键极轻地弹下去虽然无声,西碧尔觉得她自己在为电影伴奏。而在费伴奏的午后专场电影过程中,西碧尔抬头望着她姨妈,幻想她就是自己的母亲。
直到该动身回威洛·科纳斯的时候,西碧尔才大梦初醒似地觉得自己多么希望留在埃尔德维里不走。有一年夏天,她对她姨妈费说:“你会把我留下吗?”费抚摸着西碧尔的头发,说:“你是多塞特家的人。你得跟多塞特住在一起。你明年夏天还要来的。”
在连续九次愉快的暑假中,在埃尔德维里发生了两件事,使西碧尔虚拟世界的幻想轰然倒塌。
1927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西碧尔和她的表妹卢鲁在安德森家的厨房里,帮她姨妈费洗盘子。费姨妈天天看见卢鲁,而只是夏天才能看见西碧尔两个星期,所以对西碧尔分外关照。费姨妈离开厨房给安德森外祖母送茶时,卢鲁和西碧尔仍在默默地干家务。西碧尔手里正在擦拭银汤匙,但她眼睛离不开卢鲁手里擦拭的那只盛腌菜用的水晶刻花盘子。它所发生的虹彩,五色缤纷,实在太美丽了。突然,那虹彩飞了起来。原来,卢鲁把那盘子朝那通往餐室的法国式门扔去。随着水晶玻璃的碎裂声,西碧尔脑袋里一阵阵抽痛起来,屋子似乎在旋转。
玻璃碎裂声招来了许多阿姨和舅舅。玻璃已经打碎的房门猛然打开。他们全都盯着地下那摔成八瓣的盘子。
成年人开始盯着两个孩子,孩子也瞅着他们。“谁干的?”他们脸上全都写着这三个字。一阵紧张的沉默。卢鲁声明:“西碧尔干的!” “是你打碎的,”海蒂遣责的话声奔向西碧尔。 “喂,海蒂,”费告诫她,“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看在大地份上,费,你瞧,她不是失手掉在地下。她是故意扔的。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孩子?”
西碧尔一颗泪珠也没有地站在那里。而卢鲁却哭了起来。“西碧尔干的,”卢鲁边哭边说,“西碧尔干的。”
这时,海蒂的女儿走到餐室窗前,双拳击打窗玻璃,恳求道:“放我出去,噢,请放我出去。不是我。是她干的。她撒谎。让我出去。求求你们!”西碧尔已经变成佩吉·卢。 “回你屋去,”海蒂下令。“坐在墙角的椅子上,等我叫你时再说。”
西碧尔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但佩吉·卢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重温和重演了许多次。1954年10月至1955年10月,在纽约进行心理分析的第一年,佩吉·卢不但打碎了威尔伯医生诊室的窗玻璃,还在第五号街的几家店铺里打碎了价值两千美元的老式水晶玻璃器皿。每次出事,西碧尔都得再次现身对店员说:“我实在对不起,我来赔。”
扰乱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的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27年7月。海蒂跑到庭院里,以她的特殊方式纵声大笑。一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西碧尔就从厨房桌子旁站了起来,紧跨几步,通过厨房窗户向外窥看,看见她母亲一个人站在牛棚附近。那笑声又来了。
西碧尔看见她表哥乔耶和她舅舅杰里离她母亲五英尺远,抬着一个西碧尔原先曾在厨房桌子上看到的盒子。费姨妈这时来到窗前,站在西碧尔身旁。海蒂平时是尽量不让亲属听到她这种怪异的、无缘无故的笑声的。西碧尔为她母亲的失态(特别是当着亲戚的面)而感到羞耻,不由得战栗起来,便扭转了身子不再去看。
“我们到里边去,西碧尔,”费柔声说道,“我们在钢琴上来个四手联弹吧。”
“等一等。”西碧尔不能动身离开那扇窗户。
于是,西碧尔听见费姨妈隔着窗户叫乔耶和杰里。这两人正跟海蒂说什么话。乔耶的话声从庭院传来:“你别打扰她,费,”西碧尔知道海蒂是乔耶最喜欢的姨妈,而他正在设法保护她。
一口棺材,西碧尔看到乔耶和杰里两人抬着的盒子便这样想。它比她在威洛·科纳斯家后面的殡仪馆里常常见到的盒子和棺材要小一些……还是马西娅把这没有句号的想法补充完毕:不过这盒子要装妈妈还绰绰有余。
马西娅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继续沉思冥想:盒子也跟树木和人那样不断在长大。这盒子会愈来愈大,会装得下妈妈。马西娅觉得自己应该出去止住乔耶和杰里,不让他们把那盒子放在运货马车上;又觉得自己应该为她母亲担忧;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担忧,因为她愿意她母亲死!
可是马西娅当时不可能知道:在小女孩中,希望母亲死掉的想法是屡见不鲜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女孩们首先是爱父亲;而且这种想法在不断增长,因为她们发现自己的母亲在争夺自己父亲的爱。
但当平时在埃尔德维里表现良好的海蒂纵声大笑起来,一如她在威洛·科纳斯那样肆无忌惮时,她女儿不由得平添了几分怒气,使这种愿意母亲死掉的想法更为强化了。
马西娅为自己这种想法而感到十分内疚,便把这想法摒弃,并把躯壳还给了西碧尔。西碧尔并不知道马西娅有小盒会长大的胡思乱想。
《人格裂变的姑娘》作者:'美' F·R·施赖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十章 威拉德
威尔伯医生独自一人反复思考多塞特这一病例时,一次又一次地回顾了一个孩子被虐待、被污辱、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生活,并为了生存下去这个最荒谬的原因而被赶入精神性神经病的境地的怪异家世。但所有的事实根据,都出自一个来源………西碧尔及其化身。威尔伯医生明白,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
那位母亲早已去世。除了患者本人以外,显然只有父亲是唯一的人证。将近三年的心理分析也只能靠他来核实。因此,在1957年4月,医生在仔细地探索了母女关系以后,决定把威拉德·多塞特引进病例调查。西碧尔写信要他来纽约。
如果这里是司法的法庭而不是人类感情的法庭,威尔伯医生和西碧尔对于把七十四岁的威拉德·多塞特从他居住的底特律(还在那里高兴地再次结婚并继续工作)请到纽约来这件事都会比较乐观。但威拉德同他女儿和医生的关系已经紧张,恐怕不会肯来。
威拉德早已讲清:西碧尔已经三十四岁,不应再由他来供养了。其实,在她来纽约快到两年把钱用完的当口,他曾同意替她支付生活费用,使她能继续治疗。这里要补充一句,她来纽约一年后把心理分析的事情告诉了他。
医生认为这种经济资助是还债,是父亲替他那奋力通过心理分析而恢复健康的女儿还债。他对她的资助是吝啬的,不定期的。但在她这个生活阶段,她没有存款,没有固定职业。她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偶尔卖几幅自己的画,做家庭教师,间断地在韦斯特恰斯特医院担任美术治疗学家的半日工作。医生还认为威拉德·多塞特之所以负有义务,是因为他花掉了女儿的钱。他卖掉了西碧尔的钢琴、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