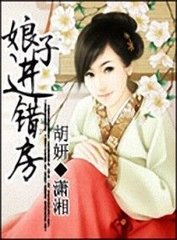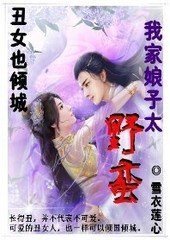状元娘子-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天上事,枉缘书札损文鳞。
途看之下,蔼如只懂得两句。“浪迹江湖白发新”有着感叹于岁月蹉跎,时不我待的意味。“文鳞”是用的尺鲤传书的典故。这句诗就字面解释,是说白白写了一封信,引伸其意便是不如不写;或者所以不写。
写信无用的原因是在第一句和第三句上。蔼如不知“龙津”作何解?查了好些书,才知道龙津就是龙门。这一下,豁然尽解了。
科举得意,犹如“鲤鱼跳龙门”,所以说“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而且试院的正门,就叫“龙门”,这也是蔼如听洪钧谈过的。所谓“未知何路到龙津”,与下句合看,自是一种“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觉。至于“大罗天上事”,在这里当然是指殿试以后的风光而言。想到上一科的乡试同年,金殿胪唱,春风得意徒然羡慕而已。此所以为“空记”。
想到这里,她完全了解了洪钧“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原因,只为两榜未曾及第,一切无从谈起,故而远远避去,连信都不写,写亦无用。
到此算是彻底谅解了,同时也心平气和了!只有为洪钧感到委屈的一种难宣的抑郁,叹口无声的气,再看最后一首:彩服何由得尽同?雪霜多后始青葱。
念到这一句,大受鼓舞,她不自觉地伸一伸腰,扬一扬眉,再看下去:天涯海角同荣谢,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二十八个字,在蔼如是无比的安慰。前两句是为洪钧想,可以放心了。虽有牢骚,并未颓废;而且他也想通了,人世科名,穷通富贵,各有迟早,何得尽同?唯有不堕志气,不废所业,经得起风霜雨雪的磨练,则自有青葱发皇之日。
后两句是为自己想,可以放心了。“天涯海角同荣谢”,无异海誓山盟,哪怕在天之涯海之角,终归要在一起共患难,同甘苦。她记得洪钧乡试那一年,从江宁寄来的四首诗,最后一句集的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不过是指两情相感,而这相通的一点灵犀,是说她应有彼此祸福,乃至生死相共的默契。
“难怪他不写信!原来他是这样想。”蔼如不自觉地自语着,将那张涛笺细心折好,放在紫檀嵌螺甸的首饰箱里。
就这时听得“呀”然一响;心无旁骛,已忘却身在何处的蔼如,不觉一惊。转脸看时,原来是霞初在推门。
“我在外面等了好半天了!”霞初满面含笑,显得异常快慰地。
“怎么不进来呢?”
“我怕打扰你,不敢进来!”霞初带些顽皮的神态,“这下可放心了吧?我在外面张望,只看你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楞,到最后可是又抹眼泪又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了!”
蔼如脸一红,羞涩地笑着问:“怎么说我抹眼泪,我自己都不知道。”
“谁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霞初一眼瞥见桌上一块湖色杭纺手绢,赶紧捡起来捏一捏,振振有词地说:“喏,证据在这里!看你用的这块手绢儿,可不是湿的?”
这可赖不掉了。蔼如笑一笑不再多说,只问:“潘二爷还没有回来?”
潘司事一下船,就为特地去迎接的牛八爷截住了。他先派人拿行李和洪钧的信送了回来,又写张便条附上,也就是转告洪钧所说的不负蔼如的那句话。他自己还跟牛八爷在谈事,可能今夜不会回望海阁。
“他不回来最好。”霞初笑道,“今晚上我们一床睡,聊它一个通宵。”
“发疯了!有什么聊不完的,要聊一夜?”
“聊你的三爷啊!”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九转眼到了十月里。潘司事寄了信来,决定明年此时,迎娶霞初。
这一下倒勾起了蔼如的心事。她默默在想,明年此时,洪钧就该打点从苏州起程北上了,这笔盘缠一定不在少数。她听洪钧谈过,进京会试,各人的情形不同。有一种是寒士,一路搭便车、搭便船,甚至靠两条腿走到天子脚下。在京里当然是住不须房钱的会馆,三餐在同乡家轮流就食,或者一处处“告帮”,能凑个数十两银子,便可捱过试期。
另一种略略好些,在家乡由亲友资助盘缠,精打细算,极其俭省。大致要到二月下旬,保和殿举人复试之时,方始赶到。四月初会试发榜,倘或名落孙山,没有资格参与殿试,立即出京,多一天都不敢住,为的是怕盘缠不够。
再有一种便纯然是纨绔的味道了。怒马鲜衣,仆从簇拥,早在年前就到了京。逛“胡同”,捧“相公”,敞开来先大玩一阵。盘缠是再也不用愁的,早有几千两银子从原籍汇来,存在银号里陆续支用。如果不够,一封信去,必有接济。
洪钧当然不能,也不会学纨绔的派头。可是像寒士那样萧索艰窘,在蔼如也觉得太委屈了他。总要不丰不俭,有个排场,像个样子才好!
她决定写封信给洪钧。他们的书函往还,一向都是洪钧先施,蔼如后报,谈什么、接什么,问什么、答什么,不生困难。有时两函一复,更不愁没话可说。而这一次是她主动,便不知从何说起了。
就这样临笔踌躇,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房门上又剥啄作响,开门一看,是小王妈。
“有事吗?”她问。
小王妈不即答话,望着桌上的笔砚笺纸说:“小姐又在作诗了。”
“不是!是要写信。”
“给三爷写信?”
“嗯。”蔼如无心跟她闲话,又问一句:“有事吗?”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明天谈也不要紧。”小王妈笑一笑,“我不打扰小姐跟三爷谈心了。”
这一下点醒了蔼如,心想:写信不就是谈心吗?所不同的是以笔代口而已!自己只当与洪钧觌面相对,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有何难处?
于是,等小王妈一走,随即在“三爷大鉴”之下,信笔而书。自我的拘束一解,文思便很活泼了;先从天气谈起,接着用“凉风起天末,君子意何如”的诗意,说到思念远人的情怀,这样,便很自然地问到洪钧和他一家的近况。
问完别人,少不得就要谈到自己;旁及望海阁中的上上下下,便顺理成章地透露了霞初的喜讯。
信写到这里,就像谈得投机那样,话题随心所欲,无须顾忌。但她仍旧用了一句假托之词,说有人在筵前谈到明年的试事,秋闱之后,便是后年的春闱,因而想到洪钧在明年此时,或者已经北上,不知可有便中一聚的机会?
有这样情深意殷的几句话在前面,以下的话便更好谈了。不过她还是很谨慎、含蓄地说,长途跋涉,其事至艰,劝洪钧及早绸缨。如果有她可以为力之处,决不敢辞,不过希望他早早告诉她,以便从容措手。
※ ※ ※信到洪钧手里,正是冬至那天。“冬至大如年”,南北皆然。洪家这天祭祖,家祭祝告,乏善可陈,所以清清冷冷,绝少过节的情趣。
祭毕“散福”,洪钧意兴阑珊,酒不多吃,话不多说。而就在这时候,民信局的差役来叩门了。
“哪来的信?”他听他家的老仆洪福在问。
“山东来的!”
听得这一句,洪钧的精神一振。全家亦都知道,山东的来信,寄自何人;以及洪钧对山东的来信,如何重视。所以任他中途离席到书房或是卧室中去看信,没有人说一句留他吃完了饭的话。
信是很快地就看完了,可是想却尽有得想。因此,洪钧在书房中一坐一个钟头,不曾动过地方。
“唷!炉子都快灭了,也不续炭。”
洪钧一惊,定神看时,才发觉是洪大太在说话。同时,也发觉自己手足冻得发痛,一个取暖用的炭炉,只剩下白灰中的星星之火,真的快将灭了。
他没有答话,起身捻亮了美孚油灯,将信放入抽斗,还上了锁。清脆的“卡答”一响,在洪太太的感觉,仿佛洪钧锁上了心扉,而自己是被摒拒在门外了。
“冬至大如年!”洪钧的声音中有着掩抑不住的感慨,“一年又快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明年不知道怎么样?”
“明年这一年顶要紧,熬过明年就好了。”
洪钧懂她的意思,她也是指望着后年春闱丈夫会升腾飞化,一举成名。可是,明年这一年又如何熬得过?
洪太太在等他答话,而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够安慰妻子而又能自慰的话好说。见此光景,洪太太的心又冷了半截。可是,她始终不曾忘记她的责任,境遇不论如何拂逆,做妻子的必得体谅丈夫。
“你也不要烦!船到桥门自会直。凭你的本事,凭你的人缘,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现在要守,‘守得云开见月明’,日子也快了!”
这样的话,也不知说过多少遍!而且,每一次说这话的态度和语气都很认真,是确知必然如此的神情;丝毫看不出她是有心安慰,更不是随意敷衍。
因此,洪钧起初觉得好笑,渐渐感动,明知她是捡好的说,亦装做受了鼓舞,摆出愁怀一放的样子。可是现在不同了,试期渐近,该有个切实打算,不能你骗我,我骗你,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守也得有个守的办法。”他抑郁地说,“不光是一日三餐糊口糊得过去,就守得出名堂来的。明年这一年,我要好好用一用功。”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如何用功,用不着跟妻子谈,跟她谈了她也不懂。这样转着念头,神魂飞越,又到了望海阁上。晴窗雨夜,红袖添香,读书有何心得?“大卷子”写得可有进境?便都有可谈的人了!
“我知道!”洪太太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至多让你苦到端午,明年下半年,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管。”
“谁管?”洪钧脱口相问,听来完全是诘责的意味。
洪太太不答,走到床后摸索了一会,捧出来一个描金的红漆小皮箱,伛偻着腰,而且脚步蹒跚,一望而知箱子很重,捧它不动。
洪钧急忙上前,为妻子接力。箱子入手,果如所料,不由得便问:“是什么东西?”
洪太太依然不答,从梳妆台的抽斗中取出钥匙开了锁。箱盖一掀,便有一只银光灿烂的大元宝,耀眼生花。此外还有四五个“元丝”,好些散碎银子。再有一张红纸,上面歪歪扭扭地标着一些不知什么文字还有符录。
“这是什么?”洪钧拿起那张纸问。
“是我的账。”
“原来是‘码子’!”洪钧定神看了一下,递还给妻子,“只怕你自己都看不懂。”
“看不懂我记它做什么?”洪太太看一看账说,“一共一百十五两多,半年的家用够了。”
怪不得说他只须“苦到端午”,原来已有准备。可是,“这是哪里来的呢?”他问。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洪太太也掉了句文,“是我平常省下来的。其中,其中— ”她终于说了出来:“有一笔是八月初从山东汇来的。”
“什么?”洪钧既惊且怒地问:“你怎么不跟我说?”
洪大太不怕丈夫发脾气,只怕丈夫连脾气都懒得发,此时平静地反问:“你为什么不问我?”
“奇了!”洪钧火气益大,“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问什么?”
这一下,是洪太太大出意外,急急问说:“中秋之前,她不是来了信,没有告诉你?”
“没有!”
“这才真的是奇了!我以为她一定会在信里要提到,可是你没有问!我想,一定是你不愿意提这件事,我为什么要开口惹你心里不舒服?”
细舷想去,妻子的话,理由十足,竟无法驳她一个字。洪钧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这件事错得没有道理,既不知应该怪谁,亦不知如何补救。无可奈何之下,唯有付之抑郁难宣的一叹。
“你也不必叹气,钱还在这里!”洪太太取出十两一个的元丝四个,放在桌上,“我没有动过。要寄还她也不迟。”
“这件事窝囊透顶了!”洪钧答非所问地说:“她是度量很宽的人,或者不致于不高兴。不过,我们自己想想,未免对不起人。”
“她的度量很宽,我的也不狭!”洪太太针锋相对地回答,可是词锋虽利,却并无负气的意味。
洪钧心中一动,试探着说:“‘若从内助论功勋,合使夫人让诰封’,你的度量不见得会那样宽吧?”
他念的是袁子才的两句诗。乾隆年间的状元毕秋帆,早年与京中名伶李桂官结为“腻友”,曾多方激励毕秋帆上进。后来毕秋帆点了状元,李桂官便被戏呼为“状元嫂”。袁子才的诗,便是描写的这一段佳话。洪钧一时想到,遽尔引用,洪太太却听不懂他念的什么?少不得要追问一句:“你说什么?是什么我度量不宽?”
洪钧无法为她细作解释,“我是说笑话。”他顾而言他地说:“你把银子收起来吧!既然够了半年的浇裹,我也可以松一口气,但愿明年老太太身子健旺,平平安安,无事为福。”
“这一层,你尽管放心好了。老太太自有我照应。”
由这句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