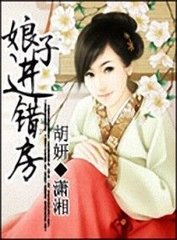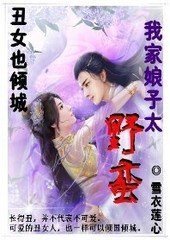状元娘子-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爱亲结亲,彼此总要体谅,再说争气也不争在一时,是争在结局上。你说,我的话是不是呢?”
蔼如一时听不明白,只觉得她母亲的意思是还要她迁就。“那么,”她问:“娘,你说要迁就到什么地步?”
“迁就一顶花轿!大红裙子,将来你总有得穿的。那条裙子要你自己挣来穿,面子上才有光采。”
“越说越玄了!”蔼如笑道:“我倒不知道怎么个挣法。”
“全看你自己。到了何家,上上下下说你贤惠,自然就会拿你扶正,前房儿女给你磕头'奇書網整理提供'叫娘,这条红裙穿在身上,才有味道。”
蔼如有些好笑,转念又想,母亲用这样的说法来劝自己让步,用心甚苦,不是件好笑的事。默默地将前后对话细想了一遍,知道事已不谐。但此时先不忙作何表示,且等小王妈回来再说。不论如何,当初既是为了安慰亲心,自甘委屈;如今不管事情怎样变化,亦总是以不伤亲心为主。
主意打定,便笑笑答道:“此刻说亦是白说。等我好好想一想。”
虽无确实的答复,但女儿的态度平和,在李婆婆亦是一种安慰,觉得有了这一个伏笔在,等黄委员一到,三方面开诚相见,不论成与不成,都会有个确确实实的结果。
一直到了晚上,才见小王妈回来,只是她一个人,脸色不恰地说道:“到天黑才见着。他说:他实在不好意思;这件事无法交代。我问:”是不是何老爷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他说:“他没有什么好为难的。’这句话是个漏洞,我就钉紧了问,既不是为难,那么,总有个说法;是不是看不中我们家小姐?他让我逼得没法子,说了实话— ”
说到顶要紧的地方,小王妈突然顿住;神气之间,迟疑瞻顾,倒像是自悔失言似地。因而连原来不甚关心的蔼如,也忍不住疑云大起,急着要追问究竟。
“什么实话?”李婆婆的脸色苍白,颤巍巍地问:“莫非黄老爷拿我们当要,根本没这回事?”
“怎么没有这回事?黄老爷还拿信给我看。我就说我不识字,问他,何老爷信上怎么说?他说,信上大骂了他一顿。”
“大骂?”蔼如双眉一扬,仿佛为黄委员不平,“凭什么大骂?骂些什么?”
“骂他,”小王妈知道无法隐瞒,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隐瞒,照实答道:“何老爷骂他荒唐,骂他异想天开,骂他— ”
不必再说下去了!尽够了!小王妈深深失悔,不管能不能瞒得住,这两句话总是说错了!只见李婆婆的身子发抖,想站起来而双腿发软,手还扶着桌角,身子已经歪着往下缩,瘫倒在地上了。
“娘!娘!”
蔼如急喊着想去扶她,已自不及。小王妈大惊失色,脱口喊道:“别乱来!等我看看!”
走上前去,蹲下身子一看,她忧虑的事情发生了!李婆婆口眼歪斜,手脚抽搐,得病甚重。可是,她不敢说破。
“小姐!”她说,“赶快扶婆婆坐直!”
李婆婆的身材高,身子重,蔼如与小王妈竟抬她不动,只好喊阿翠唤人来。刚拌过嘴的厨子与打杂,合力将病人抬到床上,靠枕而坐,蔼如与阿翠左右夹护,小王妈发号施令,指挥急救。
“快去接大夫!”她望着打杂的说,“接张大夫。”
“哪个张大夫?”
“上个月还在这里请过客!”小王妈呵斥着,“领赏的时候,你倒不问,哪个张大夫!”
“喔,喔。北大街的!”打杂的掉身就走。
“你去煎碗姜汤来!”
“还有啥?”厨子问说。
“拿楼底下、楼梯口的灯都点起来。”小王妈转脸又对阿翠说:“你到松寿堂去敲门,买一服‘通关散’来。再问问那里的司务,急救中风要什么药?叫他们拿给你。”
于是厨子和阿翠亦都下楼而去。小王妈拿灯到床前,照见李婆婆的脸,紫涨成猪肝色,眼闭口噤,喉头“呼噜呼噜”地不住上痰,不由得脸色更沉重了。
“要紧不要紧?”蔼如眼泪汪汪地问。
“不要紧!”小王妈安慰她说,“是受了气,一下子闭住了。”她又不胜悔恨地,“都怪我!黄老爷的话,不说也就好了。”
“不托他更好。”
“不要!”小王妈以指撮唇,然后指一指李婆婆,又摇摇手,意思是,要防着病人仍有知觉,听见女儿的话,心里更为难受。
其实蔼如又哪里再会谈下去?如坐针毡似地只觉等药等医生的辰光难挨。好不容易听见楼下有了人声,抢着迎到楼梯口问道:“阿翠,药买来没有?”
“买来了!”阿翠答道:“松寿堂说,药不好乱吃。我一定要,吵了半天,给了一包,药名写在上面。”
蔼如接到手里,进屋念给小王妈听:“苏合香丸。九闭证、心痛、卒中、厥逆。每股二、三包,开水下。”
小王妈点点头,先用通关散吹人李婆婆鼻孔,一无效应。于是只好撬牙关为病人用温开水灌入药。
李婆婆的牙关甚紧,蔼如又不敢过分用力,撬拨了半天,尚未能开。幸亏张大夫赶到— 这张大夫亦是蔼如裙下的不叛之臣,从睡梦中被唤醒,听说是李婆婆中风,一破深夜不出门,有急病只指点学生代诊的惯例,亲自赶来。当然,诊治得十分尽心,而且医道也相当高明,望闻问切之后,凝神思索了好一会,方始提笔开了一张方子,君臣佐使,斟酌尽善,到松寿堂会配了药来,亲自看着煎好,撬开牙关,灌了下去。
“痰大概会下去。只要痰一下去,就不要紧了!”
“多谢张老爷!”蔼如由衷地感激,而声音却因有抑制而显得平静,“等我娘好了,我到府上给张老爷上匾磕头。”
“上匾不敢当;磕头更不敢当。”张大夫说:“我倒是有件事托你,今天没功夫说,改天详细谈。”
即使张大夫有意谈下去,蔼如亦无心听他。在她,此时一切都不关心,关心的,只是母亲的病。口中与张大夫交谈,双眼却不断瞟向病榻— 看是看不到什么,听倒听出名堂来了。
“张老爷,你听!”她兴奋地说:“痰好像下去了些。”
于是张大夫细看静听,点点头说:“有转机了!”
不懂医道的人也看得出来,李婆婆的病,确是有了转机。最明显的自然是喉头不再像抽风箱般那样“呼噜、呼噜”地上痰;眼睛虽还闭着,眼皮却不时跳动;嘴角也一牵一牵地;在在叫人相信,昏迷的李婆婆是在逐渐恢复知觉之中。
“脉也好得多了!”张大夫提出警告:“不过,虽有转机,未脱险境,你们要格外当心。”
“是!”蔼如答说,“我亲自看着。”
“最好轮班看护,这个病最麻烦,不是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张大夫很关切地,“你可不要累倒了。”
“不会!”蔼如强笑着。
“明天中午我再来。如果情形有变,即时打发人通知我,不拘什么时候,无须顾忌。”
“我知道!”蔼如感激得要掉眼泪,“什么叫‘医家有割股之心’,我今天算是领悟了。”
“真是!”小王妈也说,“像张老爷这样的热心肠,不知积了多少阴功?少爷大富大贵的日子在后头。”
张大夫矜持地微笑着,别无表示。蔼如送客出门,回到楼上与小王妈计议轮班守护,“四更天了!”她说,“你去睡吧!白天非你不可。以后都是这样,你上半夜,我下半夜。”
“这样也好。”小王妈接着问道:“明天、后天都有客人定了地方— ”
“这怎么行!”蔼如不等她说完,便即抢着打断。
“我也知道,第一,没有人手;第二,病人要清静;第三小姐也没心思应酬。不过,客人不是这么想。”
“不这么想,怎么想?”
受了抢白的小王妈,不再接口,停了一会说道:“明天一早,得我亲自去走一趟;人家帖子都老早发出去了,要趁早请人家改期。”
“改期也不行!不知道哪天才能请客人上门。”
小王妈的脸色越发阴沉了。蔼如不免奇怪,家有病人,不能如常待客,暂时闭门息个一两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以她放出这副嘴脸?倒要问上一问。
“怎么?有什么不对?”
“没有什么?”小王妈避而不答,“等婆婆好点再说。”
听她这一说,蔼如也就懒得再问了。等小王妈和阿翠料理茶水,检点灯烛,掩门而去,东海初日,已经冉冉而升了。
但李婆婆卧室中,却仍如深夜。老年人畏风、畏光亮、畏喧耳的涛声;窗户密闭,还遮得厚厚的窗帘;即使是在白昼,如果不点灯,亦必是漆黑一片。
此时的蔼如,孤灯独对,守着濒死而未脱险境的老母,那份凄凉忧惧的心情,是她从未经验过的。回想这几年的飘泊沦落,既未能积下一笔大大的缠头资,让母亲得以安享余年;又不能脱籍从良,觅个好好的归宿。抛头露面,忍辱含垢,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样想着,立刻便对眼前的生涯,起了无限的厌倦之感。可是“牌子”一日不除,便一日不能拒绝生张熟魏上门。想起刚才谈到暂时谢客,小王妈那种面有难色,不以为然的表情,她不仅深感委屈,而且有些愤懑。
只等母亲病好,得要好好作个计较,再不能这样子得过且过了!她在想,怎得有个识见高超而又可以肺腑相见的人,促膝深谈,为自己筹划出一条妥善的路子来。
紧接在这个念头之后,脑中随即出现了洪钧的影子。一缕情丝荡漾,倏忽之间延伸蔡绕,将她一颗火热的心包得紧紧地,有着抑制不住的思慕;恨不得孤灯的另一面便坐着洪钧,即令不言,只默然相对,便是一种无可代替的安慰。
然而这是空想!怅惘之余,觉得唯有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借纸笔片面倾诉那些不肯为他人道的话。
这也是排愁遣闷的好法子。主意既定,回自己画室去取来纸笔;先到床前看一看母亲,病势似乎又平伏了些,便越发放心,剔亮了灯,伸纸磨墨,咬着笔管想第一段。
第一段构思很顺利,照例的问讯以外,便叙她母亲得病的情形,不提黄委员,更不提何百瑞,只说遭遇意外的拂逆,急怒攻心,因而中风。初步虽已脱险,却仍怕会有变化。接着提到洪老太太的伤寒,说她与洪钧的境遇相似,却故意不用“同病相怜”这句成语,只说由自己此时的心境,体会到洪老太太起病之初,洪钧的忧急痛苦,才知道他的不进京赴会试真是明智的决定。不然,亦一定因为心悬两地,文思窘涩而像吴大澄一样,虚此一行。
由这里便转到洪钧的动向了。目的是劝驾,希望能早日相晤。但话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洪钧设想,烟台旧游之地,宾主相得,气候宜人,是读书用功,准备下科出人头地的好地方。
再一种是从自己这方面着笔,直截了当地说:如今老母病重,前路茫茫,不知何以为计?自觉可与商议大事的,只有洪钧一个人。倘或堂上已占勿药,盼他早早回烟台。
前一种说法太泛,后一种说法则又太切。蔼如握笔踌躇,反复考量,终于发觉,最好的说法,是将两者合而为一。
这样的长信,又有许多事实,无限深情,要委婉地含蓄在内,在蔼如自是件煞费经营的事;而况还要照料病榻,所以断断续续一直到第二天才写完寄出。
幸喜李婆婆大致是转危为安了。举家上下,还有张大夫,无不欣慰。话虽如此,张大夫还是千叮万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风全靠调养看护,越周到越细心越好。因此,蔼如丝毫不敢疏忽。这样半个月下来,李婆婆已能够开口说话,模模糊糊地大致可晓。左半身虽无知觉,右手右足,总算可以动弹,而蔼如却快累得病倒了。
“小姐!”小王妈不能不提醒她了,“你自己要当心;照照镜子看!”
揽镜自顾,蔼如吓一跳!镜中是自己的影子吗?她忍不住惊疑,脸色黄黄地,两颊和眼眶都凹了下去,双唇没有血色,头发缺少光泽。似乎只有一双黑眼珠和一副白牙齿没有变化;可是相形之下,黑的太黑,白的太白,反而显得有些怕人。
虽知忧能伤人,而。瞧淳一至于此,蔼如也不免心惊肉跳。可是有什么法子能长保艳光呢?“吃不下,睡不好!”她叹口气:“唉!”
“小姐,我有个念头,转了好几天了。我先说出来,你看行不行?不行,我们再商量。”
“你说!”
“我在想,养病要静。现在客人是少得多了,不过三天两头还有人来打茶围,婆婆在床上听见了,难免操心,再说— ”小王妈欲言又止,却瞪着蔼如看,希望她能意会。
“怎么不说下去?”
看她确是茫然,一点都摸不到自己的意思,小王妈觉得非直说不可了,“婆婆在这里养病,就不能摆酒。”她说,“支撑一个门户不容易,总不能靠当当过日子!”
这一下,蔼如恍然大悟;连母亲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