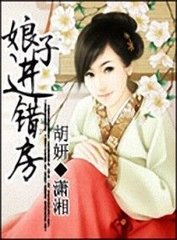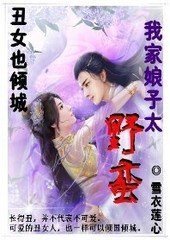状元娘子-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为的不是我,人家才会佩服。”蔼如答得很快,“为了想做状元娘子,去造就一个状元出来,无非为的自己,这是私心!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的口气倒真不小!”李婆婆忽然笑了,“状元!谈何容易?文曲星下凡,百神呵护;皇帝都没有一定把握,说能造就哪个中状元。你就敢说这话了?”
“我没有说一定可以造就他中状元,原是娘这么说,我才以话答话,作个譬仿。不过,帮他图个两榜出身,我是有把握的。”蔼如怕自己的话说得狂了,又惹母亲起反感,所以紧接着补了一句:“他的笔下、人品,原就是一定能中进士的。不过要让他肯下苦功,肯上进而已。”
“那么,你打算怎么个帮他的忙?”
当着小王妈的面,蔼如不愿明说;而谈到紧要关节上,却又不能不说,想了好半天,总算想到了一句小王妈不懂,而爱听昆腔的李婆婆一定会懂的话。
“娘总听过‘绣襦记’?”
李婆婆自然听过,知道蔼如是拿李亚仙资助郑元和的故事,表示要接济洪钧。提到这一层,她觉得不能随便许诺,因而保持着沉默。
蔼如不怕她母亲反对,因为她自信能够说服。就怕她母亲沉默,说不进话去。为了打破僵局,她向小王妈问道:“你看洪三爷为人怎么样?”
“她自然说他好!”李婆婆插进来说,“阿培要人家照应,哪会不好?”
这话出于李婆婆之口,格外有讽刺的意味。因为当时她从成山回来,正逢洪钧大醉,初次留宿望海阁的那天,小王妈对洪钧并不见得恭维;如今要说他是怎么、怎么好,岂非前后不符。
小王妈自然能辨别她话中的味道,不便多说,但也不能不说,“洪三爷的为人,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她说,“行得好心有好报!只看他待万大爷的义气,将来不会不好。不然,世界上还有哪个肯做好人。”
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那一句“行得好心有好报”,恰好打入李婆婆的心坎,默然不语,表示不反对蔼如的想法了。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四就在张仲襄护送万家眷属上船,盘灵回原籍的第二天,正式证实了江宁克复的消息。那是六月十六中午的事,曾国荃所部将领,挖掘地道,用炸药轰坍了二十余丈长的一段城墙,官军一拥而进,搜杀了三昼夜,肃清全城,并捉住了“太平天国”的第一流人物李秀成。曾国藩亦已由安庆启程,亲自在江宁主持抚生恤死的善后工作。
接着,普颁恩诏,大封功臣。据说咸丰在世之日,曾有诺言,凡能平定洪杨者封王。但清朝在三藩之乱以后,异姓不王,已成禁例。所以满朝亲贵大臣对如何实现咸丰的诺言,颇费踌躇。后来是一向被认为德胜于才的东太后想出来一个变通的办法,将王爵一化为四,分成侯、伯、子、男四个爵位。曾国藩封一等候爵,世袭罔替;曾国荃封一等伯爵。另外两个爵位,给了曾国荃的部将。此外立功出力的武将,共一百二十余员,亦皆从优奖叙。
流寓烟台的江南人,为数不少,得此喜讯,奔走相告,不在话下。但兴奋的情绪一平伏下来,却又不免犯愁,有的是抛不下已成的基业;有的是怕见那残破的家园;有的是携儿拖女,一笔回乡的盘缠,无法筹措;而像洪钧,则关心的是今年的乡试,不知能不能如期举行?
为了怕人笑他功名心热,洪钧的这份关切,深藏不露。唯有蔼如洞若观火。然而她也知道,如今跟他谈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与其徒乱人意,不如不提。
不久,来了一个好消息,本科江南乡试,决定在十一月间补行。但消息虽好,洪钧却更忧郁;蔼如知道,他是在为一笔赴江宁乡试的盘缠发愁。
有一天,洪钧回家,发觉马褂口袋中有张二百两银子的银票,不免又惊又喜,而更多的是困惑。马褂中怎么会有这一张银票?于是从这一天出门想起:先到衙门,并没有脱马褂;然后为一个朋友送行,更不会脱马褂;接着便是到了望海阁。是了!银票是蔼如放在里面的。
但也不见得!洪钧想起儿时在亲戚家见过的一件事,丫头偷了主母的一个戒指,家人大索之下,无可隐藏,悄悄塞在他人衣袋中,借以免祸。这张银票也是如此而来,亦未可知。究竟如何,唯有到了望海阁才能水落石出,于是洪钧仍旧穿上了马褂。
※ ※ ※他的去而复回,在蔼如意料之中,所不曾料到的是,他的第一句话:“你这里可曾发生窃案?”
“没有啊!”
“你倒检点一下看,是不是失落了什么东西,譬如首饰银票之类。”
这一说,蔼如有数了,“不用检点。”她很有把握地回答,“这里的人,手脚都很干净。”
“这样说来,”洪钧将银票掏了出来,“是你放在我马褂里的?”
蔼如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毫无表情地看着洪钧——要看清楚了他的态度,再作答复。
洪钧的脸上,至少没有不快的颜色;可也不是平静得深不可测,是一种微感为难与诧异,并多少混和着羞惭与感激的复杂表情。
表情虽复杂,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符合蔼如所期望的。这便使得她能放心大胆地说话了,“三爷,”她说,“也许我做得冒昧了一点。不过,我的一片苦心,你应该知道。说一句我识自己身份的话,我没有拿三爷当客人看。也希望三爷——”
她故意不再说下去,其实跟说出来一样。她不拿洪钧当“客人”看,当然希望洪钧也不拿她当“姑娘”看。“然则,”他问:“你拿我当什么看呢?”
这一问,直逼堂奥,颇难回答。但蔼如的机变也很快,“我拿三爷当至亲看。”她又加了一句:“三爷,我这样说,是不是过于高攀了?”
“高攀什么?你也是名臣之后。”
一提到这话,蔼如不由得向壁上的那幅“一笔虎”看了一眼;很快地,低下头去,但仍可以看得到,她面有凄然之色。
名臣之后,沦落青楼!以蔼如的品貌才情,偏有这样煊赫的家世,不但委屈了她,真可以说是造比弄人,有意折磨。洪钧突然激动不已,很想作一个惊人的诺言。可是,到底是读过书的人,想到“轻诺则寡信”之戒,不免自问,可能信守诺言?
不能!因为这个诺言,牵涉甚多,不是自己能够完全作主的。因此,他手持着那张银票,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了。
“收起来吧!”蔼如轻柔地用双手将他的手掌合拢,“如果不够,我还可以想办法。”
“够了,够了!”洪钧脱口回答说,话一出口,才发觉这是接受的表示。既然事已如此,也就不必假惺惺了,只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你娘可知道这件事?”
“跟你说实话,我跟我娘提过,老人家默许了的。”
“唉!”洪钧叹口其意若憾的气,“可叫我无可闪避了!只是,”他不胜感慨地朗吟着:“‘最难消受美人恩’。”
“言重,言重!”蔼如笑道:“我不是美人;更哪有资格施恩?”
“漂母一饭——”
“三爷你错了!”蔼如打断他的话,抢着说道:“漂母是看韩信穷途末路,可怜!我凭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我刚才说过,我不过是拿三爷当至亲,理当帮忙。如果你念念不忘千金之报,那倒是不了解我的心!将来你得意了,照数还我就是。”
“那当然。”
“好!一言为定,你算是借了我一笔钱。通有无是常事,三爷,你不必再说了!”蔼如问道,“只怕你还没有吃饭?”
“是的!回家就发现了这桩怪事,赶着来问个究竟,就顾不到吃饭了。”
“那,”蔼如想了一下,站起身来:“你带我去吃个小馆子好不好?”
洪钧欣然乐从,两人都打算着找一处清静的地方,浅斟低酌,细语深谈,好好共度一个黄昏。哪知事与愿违,望海阁忽然来了熟客,蔼如不能不出面应酬。而洪钧却又接到贾福的通知,说来自天津的。冶和轮船上,有他的一位同乡至好吴大澄在,希望他上船相晤。
这吴大澄字清卿,行二,弟兄三个,独数他杰出,好学不倦,于金石一道,很下过一番功夫。他比洪钧大三岁,在家乡时,洪钧一向叫他“二哥”,交谊亲如手足。所以接得这个消息,喜不自胜,匆创辞出望海阁,由贸福陪着,一直来到港口。
烟台并无码头,轮船无法靠岸,只泊在港湾中;人货上下,都用小舢板接驳,颇为费事,所以到得大船上,已经起更了。
他乡遇故,又当大劫之余,彼此都喜极而涕。叙到别后景况,洪钧少不得有所安慰——吴大澄是早就到了京里的,同治元年恩科、本年正科,两番北闱乡试,都未取中,至今仍跟洪钧一样,是名秀才。
“十一月里还有机会。”吴大澄很兴奋地答说:“今年有个数百年难遇的旷典。北闱下第,而本省补行乡试的,还可以赶回去应考,不以跨考论。礼部具奏请旨,两宫太后都答应了。所以我要赶回去。文卿,你呢?也该动身了吧?”
洪钧暗叫一声惭愧。他这话如果是在昨天问,还无以为答,此刻有张银票在身上,便不同了!“是的。”他很有把握地答说:“就在三、五天之内,有船就走。我也不写信了,拜托二哥,转告舍间,说我月底月初,可以到家。”
“好!我一到苏州就去禀告伯母。”
“江南的主考放了没有?”
“我出京的时候,还没有放。大概已有‘明发’了,不过,我们不知道。喔,”吴大澄突然想起,“倒是有件大事,你恐怕还不知道。两江换人了,曾侯移驻皖鄂交界,专责剿捻;李少荃暂署江督。”
“这倒是想不到的事。”洪钧感叹着说:“曾九帅告病,开浙江巡抚的缺;如今他老兄连两江总督的位子亦都保不住。曾家的盛衰变化,何其之速?”
“也不见得就是盛极而衰,朝廷对曾侯还是很看重的。”
接着,吴大澄便细谈当今人物,特别是同乡前辈,潘祖荫如何,翁同和如何。直到午夜,轮船大鸣汽笛,通知行将启锭,洪钧方始辞别下船。
这一夜睡得太迟,到第二天中午才为贾福唤醒,送上一封潘苇如的来信,说是接到“邸抄”,江南考官已经放了;另附一张单子,上写“正主考太仆寺正卿刘琨,字玉昆,号韫斋,云南景东厅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翰林;副主考翰林院编修平步青,浙江山阴人,同治元年壬戌进士。”
对于这两位主考的生平,洪钧一无所知,亦无心去打听。他所感到欣慰的是,潘苇如特地送这一封信,足见关切。回乡应试,不但请假必准,告贷川资,亦可如愿。
一转到这个念头,同时便想到失落的那封信;胸膜之间立刻就有一股突兀之气横亘着,很不舒服。“偏争口气!”他不自觉地自语,“不跟他开口。”
话虽如此,礼貌上仍旧要向潘苇如去道谢,顺便当面告假。潘苇如当然有一番勉励期许的话;他精于医道,送了洪钧一支人参,说在闱中构思,精神不济时,咬一口人参,细嚼缓咽,有培元固本、补中益气之功。最后又亲手送了一个封袋,是八两银子的“程仪”。
※ ※ ※从这天起,洪钧便不上衙门了,白天摒挡行装,料理未了杂务;夜来是同朋友,排日设宴饯行,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望海阁却是“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犹自点灯来”。
行期定在十月初六。前三天,蔼如就关照他,临行前夕,最好能辞谢应酬;如果不能,少喝些酒,到望海阁来喝第二顿。又说,这是她母亲的意思,不算饯行,聊当预贺。
因此,初五晚上,新关同人的公宴,洪钧托辞胃气痛,酒也不饮,菜也不吃,敷衍到终席,谢过主人,急急忙忙赶到望海阁。上楼一看,眼睛一亮,换了一堂簇新的平金红缎椅披,红烛烨烨之中,蔼如盛妆以待,红裙红袄,一片喜气。
洪钧看得呆了。他心目中的蔼如,一直是淡妆素服,天然风韵;谁知一改浓妆,更有一股夺人心魄,不可通视的冶艳色态。
“怎的?”蔼如倒有些发窘,羞涩地笑道:“倒像不认识我似地。”
“是啊!可真有点不认识了。你像个,像个— ”
“什么?我替你说了吧,像个新娘子是不是?”蔼如望一望自己的红裙说道:“关起门来做皇帝;没有外人,我也穿一穿红裙,过一过瘾!”
多少年来的习俗,唯有明媒正娶,鼓乐花轿抬进门的新娘子,才许穿红裙。洪钧懂她的话,却不能确定她话中的真意。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装作不懂,不置可否,就是件很煞风景的事。
这样想着,便不暇思索地答道。“你急什么?莫非将来就没有红裙穿了?”
蔼如笑笑,似乎不曾细想他的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