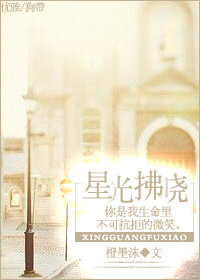拂晓刺杀-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紧的话见告于我?”
赵老大的一双金鱼限往上翻动,脸孔微微扬起:“何敢,今天遇上你,是你命大,更是老天爷要我这个贵人来助你逃过劫数;此番到‘大仙脚’左近来,我原是准备做一票生意,不料却先听到一个消息——何敢,你可是和‘八幡会’结下什么梁子?”
何敢舐着嘴唇道:
“你且先往下说。”
赵老大道:
“就在今天午时光景吧,我正好歇脚‘苟家集’一片茅店打尖,不意碰上‘八幡会’‘黑煞幡’所属的五名好手,这五人当中有两人原是素识,免不了寒暄几句,我问他们有何公平,他们的回话却吓了我一跳!”
何敢急切的问:
“怎么说?”
赵老大低声道:
“他们告诉我,要找你澄清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风闻你接了一趟生意,而这趟生意又是他们早先打过招呼,传示信物,要求同道必须拒绝的生意,好像关系着一个女人什么的,何敢,你是不是有这码子牵连?”
何敢坦然造:
“不错,我的确接了这么趟生意,那个女人叫金铃,似乎和‘八皤会’‘血灵幡’的官玉成有点纠葛,姓官的要杀她,她来找我护送到关外——”赵老大又瞪起金鱼眼,同时连连摇头:“何敢啊何敢,算起来你也是老江湖,眼皮子不谓不宽,心机不算不灵,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你难不好去招惹,却偏偏要和‘八幡会’打对台?你他娘‘一条钢鞭顶裤裆’,与‘八幡会’硬着卯上,岂会有你的便直占?你是糊涂了不是?!”
何敢叹了口气:
“人要脸树要皮,我总得争一口气,说得好听是不做那缩头五八,说得难听是势成骑虎,欲罢不能;赵老大,我也是背不过才应承下这档买卖的……”哼了一声,赵老大道:“脸亦好皮亦罢,都没有老命重要,何敢,一朝断了气,你就任是什么气也甭争了,这桩营生,你还是赶紧回了吧!”
何敢苦笑道:
“已经说妥敲定的事,又如何回绝人家?况且还收了前金,更护送了这么一段路程,赵老大,你替我想想,我朝后还得混下去呀……”赵老大默然片刻,突兀冒出一句话:“我妹子的事,你怎么说?”
何敢的表请马上痛苦起来,他朝朝艾艾的道:“令妹,嗯,赵老大,令妹莫非仍然待字闺中?”
赵老大的脸色变得不大好看了,他冷峻的道:“你这算什么驴话?三年以前,在你救了我妹子一命之后,她业已以身相许,一再表示过非你不嫁,如今你却问她出阁不曾?何敢,你是故意污蔑我妹子的名节,轻觑她的信诺?”
连连摆手,何敢急道:
“不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赵老大,我只是顺口问问——”赵老大仍然不悦的道:“自来是男求女、隔层山,女求男、隔层单,想我‘不回剑’赵大泰也是道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而北地‘赵氏剑门’更乃声威渲赫,我妹子赵小蓉素有‘断肠剑’之美誉,这种种般般,还压不过你小小的三寸名头?却是害我妹子对你百般屈求迁就,我‘赵氏剑门’上下无不对你巴结奉承,盼望的只是你能允诺这门婚事,做我赵家姑爷,可恨你他娘却拿跷端态,竟再三拒绝我妹子的一番深情厚意,何敢,你当你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居然将我妹子看成敝展不如?”
何敢又窘又冤,几乎就要指天盟誓:
“唉,唉,赵老大,你说起话来活脱放连珠炮,莫不成就不让别人有申辩的余地?令妹名高艺精,又是你‘赵氏剑门’三代以来唯一的掌珠,我何某人何才何能,得其垂青?我之不敢应允这门婚事,其一是自忖门户不当,高攀不上,再则我对令妹有过薄惠,施恩望报,岂是我辈为人之道?三则么,我他娘一个江湖浪荡,吃的是这行刀头饭,将来拿什么来保障令妹的终身幸福?赵老大,我不是不识抬举,实在是承受不起,自己业已混不出名堂,又何忍牵累令妹跟我遭难吃苦?”
重重一哼,赵大泰道:
“说得倒好——我问你,三年前我妹子中了那‘鸠雀花’的奇毒,是谁为她渡气运息?而且还是嘴对嘴的渡气运息?又是谁替她蒸浴排毒,以内力通脉行经?我妹子一个冰清玉白的黄花大闺女,被你一个素昧平生的臭男人在去除衣裳之后如此赤裸裸的摆弄,你,你叫她还能再嫁谁去?”
何敢面红耳赤的辩诉:
“那是要救她的命呀,常言道嫂溺援之以手,如何还能顾得了男女接受之规?再说,我本亦不愿逾越,都是那住在山坳子里的老郎中逼迫我这样做,他自己又瘦又干,搬动不了令妹,况且亦毫无内家修为,才把这桩倒霉的差使扣到我头上,我,我全是依那该死的老小子指点施为……”越大泰硬绷绷的道:“不必再说那些闲篇了,何敢,三年已经过去,你害得我妹子够惨,今天又碰上你,好歹你要还我一个公道!”
何敢尴尬的道:
“上一次,赵老大,在你找到我的时候,我不是讲得很清楚了么?刚才又一再向你解释我的苦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赵大泰的声音蓦地拔高:“好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我‘赵氏剑门’,与你不是亲家,就是冤家,姓何的,你要抛弃我妹子,便且先同我了断过再说!”
何敢退后一步,急促的道:
“赵老大,赵老大,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你这又是何苦……”拂晓刺杀……第五章血肉黄雀第五章血肉黄雀赵大泰圆浑的脑袋一昂,头顶上剑柄所缀的猩红穗子飘起,他恶狠狠的叫:“不必份熊装孬,姓何的人,人家忌讳你的那条骡鞭,我赵某人可不含糊,我他娘做不成你的大舅子,至少能换成个催命阎王!”
何敢正想有所表白,猛然觉得一股突如其来的炙热透升内腑,虽是一瞬即消,也令他心脏痉挛,全身抽搐,不由自主的晃动了几下。
方待翻脸出手的赵大泰是何等经验,见状之下大感诧异,他稍稍逼近,审视着何敢的面容,神情逐渐转为凝重:“何敢,你可是中了什么毒?”
何敢斜瞄一眼站在那边呆若木鸡般的姜盛,低声“嘘”了一声:“叫几条金线蜈蚣叮咬了几下,不算太严重……”赵大泰睑色一变,气急交加:“什么?你竟然被那种毒蛊伤着了?该死,这是要命的事,还说不算严重?解药呢?咱们赶快去拿解药救命呀!”
何敢点了点头,道:
“正请这位朋友带路,去找那持有解药之人。”
赵大秦那股焦虑样儿,就好像是他自己被毒虫叮咬了一样:“走走,咱们快走,这种事何等紧要,片刻也耽搁不得,亏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与我叙旧,该死,真该死!”
何敢一边挪步,边笑道:
“差点挨了你的剑,岂不比毒发而死更快?”
金鱼限又瞪凸出来,赵大泰怒道:
“你他娘少说风凉话,你以为我稀罕你?要不是为了我妹子,我早同你豁开了;小蓉也不知叫什么鬼迷了心,千挑万拣,单单看上你这个不成材的!”
姜盛又开始在前领路,却吃赵大泰一叠声催赶着,他搞不清楚赵大泰与何敢到底是种什么关系?一会亲亲热热,一会吵吵闹闹,但他却搞得清楚一点——不管人家是什么关系,却绝对没有他渔翁得利的机会就是!
一道土堤横拦在前,土堤后是一排三间砖瓦房,丈许高的堤面上植有防风林,密密郁郁的枝叶纠结参差,倒还相当隐蔽。
姜盛带头到了砖瓦房的门口,方待举手扣门,门已从里面开启,一个五短身材的仁兄冲着姜盛便嚷嚷:“你好歹算是回来了,这往返不到二十里地居然去了大半宿,大哥已不知问过多少次啦,小姜,你他奶奶是爬着走的哇?熊哥呢?大哥急著有话问他,还有,那个妞儿带回来没有?”
姜盛一脸苦相,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已被后头的赵大泰一把推进了屋,几乎和那五短身材撞成了一堆。
五短身材方始惊呼一声,赵大泰已跨进门里,大刺刺的四处搜视:“白不凡呢?快叫白不凡出来见我!”
那位五短身材一见赵大泰比他自己还要矮上半个头,又是这么一副其貌不扬的尊范,竟敢如此目中无人——大声叫嚣,立时便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你是打哪里钻出来的乌龟王八?黑天黑地撞到我们居处鸡毛子喊叫?白不凡,白不凡是你能挂在嘴上的?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赵大泰一双金鱼眼鼓起,却皮笑肉不动的道:“你,又是何人?”
五短身材一挺胸膛,十分有气概的道:
“好叫你得知,‘滚地虎’曹非就是你家老子——”“子”这个音韵尚在曹非的双唇齿缝间回荡,赵大泰已伸手一巴掌将他打了个大马爬,这一巴掌快如石火,根本无从躲起。曹非甚至连人家抬臂扬手的动作都没看清,但觉脸颊碎然火烫,人已趴在地下了。
赵大泰哧哧笑着:
“我就端打你这个不开眼的‘滚地虎’他娘,冲着我发狠”算你八字生倒了!”
门边的姜盛有心去帮伙计一把,却又委实不敢造次——在他背后,还双臂环胸,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何敢哩。
从地下一骨碌爬将起来,曹非捂着红肿的面颊,指着赵大泰跳脚叫骂:“好个三流窑子,你竟敢暗算你家曹爷?你今天是死定了,我要不将你剥皮分尸,就算是你“揍”出来的!”
赵大泰两条疏盾一扬,挪揄的道:
“我没有你这种窝囊儿子——就凭你这几手,连我孙子也能一脚险翻了你!”
怪叫一声,曹非往前便扑:
“看我活拆了你——”
这时,深垂的门帝一掀,白不凡人显声出:“曹非退下!”
前扑中的曹非扭腰卸肩,一个回旋走出三步,拉开嗓门大叫:“大哥,大哥,这不知从哪个鼠洞里钻出来的下三滥,竟然到咱门居处生事启端来啦,方才还抽冷子暗算于我,大哥——”浑身上下又是缠着白布条、又是涂抹着各色药膏,衣衫上还沾有斑斑血迹的白不凡,灰头土脸的委顿得不似个人样了,他挥挥手打断了曹非的话,眼睛瞅着赵大秦,一口童音里夹着沙哑:“阁下想是‘赵氏剑门’第三代大弟子‘不回剑’赵大秦?”
瞧着白不凡狼狈的模样,赵大泰嘴里不由“啧”了两声:“正是我赵某——白朋友,你好像发了点意外?”
白不凡已经发现站在门外的何敢了,他眼神极其冷硬的道:“艺不如人,活该要受这场教训;赵大泰,倒不曾听说你与何敢也是一条路上的,眼下你陪姓何的突兀到来,一定有事?”
赵大秦咧开了肥厚的两片嘴唇,仿佛有意展示他那一口凸凹不齐的黄板大牙:“找你呢,当然是有事,你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竿子捞不着,五鞭子打不着,若是无事,我老远巴巴昼夜登门做甚?只希望你能赏个薄面,将麻烦摆平,我担保何敢不会再找你索斤头……”白不凡的娃儿脸上浮现着一种诡异的老辣神形,他缓缓的道:“我得先知道是什么事,才能决定有没有商量余地。”
何敢一脚踏进房里,火爆的道:
“白不凡,你少他娘在那里拿跷,依得我的脾气,见面就剐人,还有这许多场面话可说?你使诈暗算于我,竟还敢端着人架子扮一个人样的人?!”
白不凡毫不动气,十分冷静的道:
“在江湖里混,原就是这么个名堂,孰是孰非,更是纠缠不清,我对付你,自有我的道理,八五八书房你用不着怨恨,便如同我吃了你恁大的亏,也没有什么好怨恨的一样!”
“呸”了一声,何敢怒气上冲:
“你吃亏?你吃亏全是自找,若非你歪点子动到我头上,怎么会招来这个后果?我这里一腔怨气还没有发泄,你倒振振有词的搬出春秋大义来啦?莫不成你暗算我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我应该闷着脑袋受割挨刮?”
赵大泰适时往中间一站,摆出和事佬的姿态:“好了好了,大家都不用争不用吵啦,事情既已发生,要紧的是如何善后,将问题解决方为当务之急,是非孰属,目前且不必追究——”转脸朝着白不凡,他又道:“我说白朋友,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你用你所饲养的那些个毒虫子螫咬了何敢,只好麻烦你再把解药拿出来救人,就此一事,然后咱们一拍两散,谁也不欠谁的……”白不凡先是沉默,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更且越笑声音越大,越笑表情越是得意。
赵大泰沉下脸道:
“你是娶了新媳妇啦?这么个高兴法?”
白不凡强忍住笑道:
“我是高兴,赵大泰,的确高兴,我原以为根本没有伤到何敢毫发,根本对他不曾造成丁点损害——而我却挨了一顿好打,这口窝囊气,憋得我几乎吐血,现在我知道了,我虽吃了亏,姓何的可也并不囫囵!”
对面的何敢冷冷一笑:
“你他娘阴着坑人,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赵大秦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