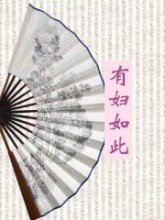岁月如此装X-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那朵牡丹花就这么开着开着然后谢了。
林佑生日那天,我在家打扫卫生。
穿着拖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我在灶台上反反复复地擦啊擦,上面的油渍怎么也去不掉。想了一刻钟之后,我打算步行去家乐福买瓶威猛先生。
走着走着,罗依然突然给我来电话,“张扬,你怎么没来?”
我力气不够,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你和林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深吸了口气说:“我去买瓶威猛先生。”
罗依然说:“话说明白,怎么了你俩?”
我说:“分手了。”
罗依然那边突然没声了,她好像把电话撂下来,背景很吵,好像有人在劝说少喝点,一会劝周子良,一会劝林佑,混乱不堪。
街上的车辆来来往往,路灯红黄绿变着颜色,路人提着菜行色匆匆地往家里走。
家乐福店庆在搞活动,外头聚了不少人。我挤进去,拿了两瓶威猛先生,再提了箱牛奶费力地挤出来。
走到小区楼下,电梯灯灭着,停电了。
我再拎着牛奶去找物业,物业小姐说:“楼下的告示都贴了一个多星期了,电路检修,你那一栋轮到晚上7点到11点停电。”
我说:“不是吧,我住23楼,你让我爬上去么?”
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那就到11点再上去吧,我这边要下班了。”
我就坐在小区里,手边搁了箱牛奶,一分钟一分钟数着时间过去。
天色已经暗得不像话。
一晚上没人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一条一条地翻名片夹,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打个电话过去聊几句。
这四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想。想想中学,想想大学,想想我做过的那些装X的事。
初中的时候流行复读机,那时候我走哪都带上那个硕大的复读机和一包磁带,插上耳机听听周杰伦的歌,觉得很牛X。
再后来开始看小说,什么《朝花夕拾》什么《雷雨》都好像不足以彰显牛X,一边看盗版的《流星雨》一边伤春悲秋才觉得自己段数太不一样了,太有文化了。
高中开始写日记,满篇都是明媚忧伤,文艺咏叹调地记录类似于“我的妈妈爱打麻将于是我是在困难中生活,我可能要离家出走去那遥远的地方。灰蓝灰蓝的天空下,飞过一群不知去往何处的乌鸦”的心情。
晚自习下课之后,和罗依然并排躺在操场上,忧伤地望着苍穹,心想那个大学它怎么就那么难考。
大学的时候找工作,看见别人拿的薪水眼红得泪流满面,最后还要扫一眼说“我最想过的生活是背个包,徒步环游世界,跟钱搭不上半点边儿”。
装着装着,我们就长大了。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些牛X的事,怎么看怎么傻X。
其实到现在我也经常装X,你们可能会说张扬你这人怎么活得这么不洒脱啊。
我要真能想明白这事,我早皈依佛门,普渡泱泱众生去了,还用得着在这感受装X未遂被人骂成傻X的快感吗?
八点半的时候,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她说:“张扬,你在上海过得开心吗?实在不行就回成都吧,我真后悔没再生一个,可以搁一个在身边。就这么一个闺女,还看不着摸不着,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怎么想怎么亏。”
我说:“妈妈,当初你不是怎么说的吧。你说不把我整去大城市,不足以给老张家光宗耀祖,对不起八辈列祖列宗啊。”
我妈说:“可我担心你啊。你小时候坐在我自行车后头,都能半道上掉下去在大马路中间哭。”
我安慰她说:“妈妈你放心吧,我在这边特别好。上海人民都是活雷锋,我那天把钱包掉公交车上,那个售票员还一路送货上门了。”
我妈说:“好就行,那个电视剧到时间了,回头和你说。”
我笑笑说:“赶紧的,别让我爸把电视抢了。”
挂了电话,你们看,我好像又装了一回。
快十点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林佑的电话。
我想接电话的时候,一声提示音之后,手机没电了。我有点无奈,只能把那箱牛奶拆开来,抬头对着月亮开始喝牛奶,喝完一包之后,我对着月亮说:“……张扬你别再把脸对着月亮了,月亮它会月蚀的。”
第二三章
来电之后,我提着牛奶上楼。
在房间里握着手机想了挺久,打算给林佑回个电话。
今天是他的生日,往前推十年的生日我们都是一块过的。突然不一起了,心里有点空荡荡的。
他的手机关机了。
我发了条短信说:生日快乐。
然后一整晚失眠,这条短信他没回。
第二天我去找高欣研究货源,我们要去找几家小厂,把东西印上会所的标志。关于会所的名字,高欣给了几个备选:亚历山大、奥斯顿和布兰得利。
我有点为难地说:“不如叫‘和平会馆’吧。你这些听上去怎么有点像做洋快餐的啊。”
高欣想了想说:“上海的会所酒吧无外乎两种,一种打着洋招牌,一种比较怀旧。你这个‘和平会馆’不错啊,有点十里洋场,金迷纸醉的调调。找个设计师搞个logo吧。”
自从那天高欣和陆华不欢而散之后,她就卖命地张罗一切和会所有关的事。好几回大晚上地找我和她讨论装修风格,我大老远地兜过去,她又一脸忧伤地和我说时间太晚,咱们洗洗睡吧。
我看她夜深人静的夜晚那么忧伤,实在不好意思发作。
终于在她空城计风雨无阻地唱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觉得高欣可能是寂寞了。
那天我俩坐在吧台旁,高欣说:“陆华和我结婚快十年了,但有些东西留不住,味道变了。”
我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在旁边陪她坐着。
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张扬,我们出去一趟吧,我想去江苏宜兴看看紫砂壶。”
我说:“行啊,这算出差是吧。路费饭费你报销吗?差补你给的吧?”
高欣又一脸忧伤地说:“时间太晚,咱们洗洗睡吧。”
晚上是谢君昊的生日会,我上门打算白吃白喝的时候,见着几个原来SB的同事。
一时间有点尴尬,只能凑过去和谢冉谈谈那些有名的作家,比如米洛哈伊达洛夫斯基、莱温斯基、公交车斯基、卡巴斯基、兔斯基等等等等。
谢冉挺有感慨:“谢君昊比我小一岁,你说这小子怎么转眼就长得这么不知不觉啊?”
她端了点喝的:“我去找他小谈一下,得赶紧把他的爱情观梳理正确。”
我回头见着原来的一个项目经理Mac,他笑着说:“张扬,你也来了。”,
我客套着说:“Mac,好久不见,怎么样,你们最近忙不忙?”
Mac说:“还行吧。”他耸了耸肩,有点遗憾地说:“老实说,你离职的事情太突然了。那时候我和Gavin一块在青岛出差,他刚看到邮件就给Hans打了电话,后来回了上海。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你做得很好。不过张扬,这不一定是件坏事,真的。”
我听他这么说,也舒了口气:“这事也过去一段了,我现在也还不错。”
Mac听完,突然挑眉低声开玩笑说:“我当初还以为是因为Gavin和你谈恋爱了,所以得支走一个,哈哈哈哈。”
“私底下说我坏话吧,张扬。”转过身去,谢君昊含笑站在那里。
我说:“师兄,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个定位么?”
谢君昊坦然地点点头说:“差不多吧。”
Mac走近去拍拍他的肩,说:“Gavin,我不打扰你俩打情骂俏。你这有什么喝的么?”
谢君昊说:“厨房冰箱里有酒。”
我递了瓶红酒给他,说:“我现在境地比较潦倒,体面的礼物实在拿不出手。我有个朋友开间酒吧,从她那顺了瓶酒过来。生日快乐。”
谢君昊笑了笑说:“你人来就好。”
在他家吃了顿晚饭,饭桌上说得开了,大家开始无穷无尽地扯淡。Mac喝了酒以后,那张胖脸有点红,他起哄说:“Gavin,张扬就在跟前,你趁着今天生日,有什么话要说赶紧说。我们都可以当听不见。”
谢君昊给Mac倒了杯酒说:“你这样子已经不行了吧,再喝两杯打的回去。”
Mac起来倒沙发里,哼了两句:“我今天就睡你沙发……不打搅你们吧……”
饭刚吃完,门铃响了。
谢君昊起身去开门,他的声音有点迟疑:“你怎么来了?”
接着我听见王晓雨的声音说:“表哥,生日快乐。我这几天刚好在上海开会,特意过来看看你。”
我下意识地回头,正巧碰上王晓雨的视线。她愣了愣说:“这么巧,张扬你也在。”
她放下外套,走近来低声问我:“我听说前段时间你把工作丢了啊。现在在哪呢?”
我笑了一声说:“你是想把我现在这个也搞没了?”
王晓雨脸黑了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工作丢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口气不好:“和你是没关系,你最牛X的不就是装么?你请继续,没人拦着你。”
王晓雨说:“张扬你犯不着把气撒我身上。是不是罗依然和林佑好了,你心里不舒坦了?我早和你说了,罗依然不是个省心的人。你才来上海半年吧,他们还不是好了。”
我提高了音量打断她说:“王晓雨你再说一句试试。”
她说:“今天我表哥生日,你这是想怎么的?翻旧帐?”
我忍了两分钟,提起包走过去对谢君昊说:“师兄,我有点事先走了。你们聊。”
谢冉在一旁叫住谢君昊:“你送张扬回去。”
我摆手说:“不用,他刚才喝了酒不能开车。”
谢冉寄予重望地拍了拍谢君昊的肩:“喝点小酒好办事,这要是被开罚单了,算我头上。”
谢君昊看了看我再看了看王晓雨,也拿起外套:“张扬你放心,我刚喝的都是苏打水。”
我坐在车里,打开车窗,晚风吹进来让人觉得清醒还有点冷。
谢君昊开了音乐,沉默了一会说:“心情不好?”
“还成。”
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张扬,你现在是不是过得很不开心?”
我怔了怔,转头看着车外的风景,一幢幢高楼大厦,很陌生:“没有啊。”
谢君昊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是么?我面试你的时候,你没现在这么黯淡。”
我说:“我在你手下的时候,天天陪你加班还要挨训。不黯淡一点怎么彰显师兄你的本事。”
他微微摇了摇头,笑着说:“张扬,你以为嘴上不说,我就看不出来么?”
我正打算澄清我生活不幸福的假象,突然一个不稳,谢君昊向左猛打方向盘,前面有辆车变道没有打方向灯,我们险些撞上去。
接着车尾被什么钝撞了一下,“哄”地一下向左边的隧道内墙直冲过去。
我坐在副驾座上,身体向前直接撞上车前饰。
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归西了。
“张扬,你怎么样?”谢君昊伸手过来扶住我的额头,拧着眉看着我。
我额角和右眼生生地疼,反应了几秒钟,得知我幸还之后,深吸了一口气说:“谢君昊,你怎么开车的啊?我差点小命没有了我。事到如今,我残存在这个世上容易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祖威武。”
谢君昊轻轻按了按我的右眼睑:“好像撞到眼睛了。”
我“嘶——”地抽了口气:“别按,疼。”
谢君昊沉声说:“在车里等着,晚一点我带你去医院。”
接着他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我看见谢君昊敲了敲前面那辆车的车窗,示意那司机下来。
他锁着眉心,松了松领口,对那司机说:“妈的,你怎么回事?!不知道变道要打方向灯么?!”
那个司机连连陪不是,上前递给他一根烟:“不好意思啊,刚才在打电话,没留神。哥们,真是不好意思啊。”
谢君昊皱了皱眉,没接他的烟:“你给我下回注意点。”
这是我第一次见谢君昊骂脏话,顿时感觉他身上的西方资本家气质消失殆尽,有一种“这个人他终于从高高在上的火星回到了地球”的亲切感。
两分钟之后,隧道里响起广播:“隧道内发生车祸,请后面车辆减速慢行,小心避让。”
接着我们就给一拖车拖走了。
现在我和谢君昊站在路边,我瞟了一眼他的那辆沃尔沃,撞得十分惨烈,惨烈到旁边有人路过,都要窃窃私语一句:啊,这车怎么撞成这样啊,里面的人肯定活不成了。
我一边捂着眼睛,一边心疼地说:“这能修好么?这要修好得多少钱啊?这车看上去不错啊,怎么这么不经撞呢?好好的一辆沃尔沃撞得跟一头栽进土里的拖拉机似的。不对,拖拉机要开隧道里比这个拉风多了。”
谢君昊试着发动了一下车子,还能走,他拿起电话报了个警,转头过来对我说:“等交警鉴定一下,把车开到汽修厂,保险公司会陪的。”
他再微微低头,看了看我的眼睛说:“有点肿了,得赶紧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