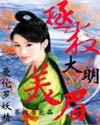大明财团-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我给我……”
这让没见过阵仗的报童吓得哭了起来,边哭边说道:“我……这里的二十份……已经卖完……”
“那什么地方还有?”
“我……不知道……”
正在乱糟糟之际,忽听的有人喊道:“这边也有……”
呼啦吵,众人又都顺着声音跑过去买报纸了,留下那报童不知所措。
“小哥,我看这报纸叫做《新阳旬报》,是否是十天出一版?”中年人见报童身边没人,就来到他身边问道。
“……是的,要十天后才有新的报纸出来。”
“那报纸上是否还会有《济公全传》?”
“我……我……不清楚。”
中年人有些怅然若失,要十天后才有新的报纸出来,还不一定有这个济公全传……
而在乡间,更是因为报纸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躁动,原因就在本版的头条上的那篇文章《秋收将至,知县大人叮嘱要做好秋收准备》。
别看标题很直白,让拿到报纸的乡绅嗤之以鼻,不过乡间有那些个识字的对此却是心思活动起来。
每年秋收,对朝廷和百姓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近些年风调雨顺,加上中原大地土地肥沃,百姓收成很好,少有出现强征暴敛的现象,但是因为收成好,中间倒是肥了本地的乡绅和胥吏。
太祖初年定下了上、中、下三等县,收税标准并不一致,但每个县,每年的赋税定额则是固定下来,后来大明中兴,或有调整,但依旧是为每个县设有定额。
而且沿袭了太祖的定制,年景不好或可少收,但不可多收,赋税超过定额还要受到责罚,这是朝廷为了防止官员为了业绩而对百姓加大剥削做出的限制。
作为现代人对此看来或许太过死板,但在这个时代也不失为一个为百姓着想的好方法。
但在收成好的年景,掌握着本县土地的乡绅们则可以损公肥私,收成好不止是租子要多交,县里分派下来的粮税也会让百姓多交出来。
只要不是太过,老百姓能有生活下去,加上乡绅和胥吏勾结,从中欺上瞒下,多收上来的赋税都进了这些人的腰包。
新阳县知县****书,乃是元庆七年的新科进士,在京城政务堂学习三年之后,外放到新阳县任知县。其人正值而立之年,雄心勃勃的想要做一番事业。但是来到地方,却感觉到束手束脚,处处受制。
知县俗称百里候,在以人治的社会里,知县的权利在其辖县可以说能无限延伸,哪怕他颁布一条法令说不许百姓放屁都可以!
不过这都是表面上的光环,真正能够完全掌控地方的知县在现在来说几乎没有,原因就在乡绅和胥吏相互之间牵连甚深,势力盘根错节,知县的命令都是通过他们才可传达全县。知县一任七年,而本地的势力却是扎根于此,所谓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说的就是这个。
正常的情况下,知县和本地官绅都能达到微妙的平衡,知县稳稳当当的做着县太爷即可,不需要操劳一般的“俗事”,有点类似朝廷中枢。
来到地方上,宋知县才晓得当今圣上为何总是会对朝廷政务指手画脚,当年他在京城时还曾非议过。
同他一样,当今皇帝李厚也是三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必不肯为朝臣所摆布,成一尊泥塑的庙像。
而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被人限制的滋味也让宋知县体会到了。
初来此地,宋知县不甘心受制,和本地势力有过交锋,但并未落的好处,甚至第一年的考评上,官声上还有些负面消息,落得个差评。
其家族着急派来一位富有经验的师爷过来鼎助,得其指点,宋知县暂时偃旗息鼓,按耐住心思,第二年的考评得了个上!
有作为时考评却只是个下,没作为时,考评却是上!原因就在于本地舆论尽操于乡绅之手。
宋知县却不甘心如此,却也没有再硬碰硬,而是耐心的等待机会,等来等去,却等来了陆骏!
第四十二章 新阳旬报(下)()
别看小小的一份报纸,但牵涉的东西很多。来自后世的陆骏知道,想要《新阳旬报》有所作为,得不到官府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是故,他那日和顾长君谈完,便拉着他一起去拜见新阳知县****书。
陆骏虽然在八丈河镇风生水起,但在整个新阳县依旧没啥名声,靠的是顾长君和顾家的名头才得以见到宋知县的。
进了县衙,通禀了姓名之后,陆骏就和****书说起了报纸,并且呈上去给他看。
宋知县翻看之后,对此不予置评,却不大看得起里面的市井方面的内容和通篇白话,却也没有为难。而且大明历来没有禁言的传统,朝廷是鼓励民间能多多为朝廷进言,登闻鼓可不止用来告御状的,所以就宋知县就同意了他们发行报纸一事。
随后聊天过程中,陆骏为了讨好宋知县说道:“不知老父母近期可有文章或是政令需要传达?或可放在这报纸之上。”老父母是秀才生员对本地知县的称谓,犹如陆骏称呼知府为老父台一般,加个“老”字以示尊敬,就行后世各种“总”流行一样。
宋知县愣了愣,随后说道:“放在报纸之上?这个嘛……”
他不由的沉思起来,这报纸一看就是俗物,士林不回对此感兴趣的,若是自己的文章放上去,同那些市井文章在一起无异于自取其辱,当即想要拒绝。
但是政令……政令或可放在上面,但又显得不太严肃。
在他沉思之际,陆骏说道:“这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父母若有政令,放在报纸上倒是能够让老百姓知晓,省得下面的胥吏欺上瞒下,到了下面会变味或是大打折扣……”
一直到后世陆骏生活的时代,咨询那么发达,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更别说这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
这番话正中宋知县的下怀,当即拍案说道:“正是如此!宝林、子良,如今秋收在即,本官正巧有道政令要下发,如此就放在报纸上如何?”
陆骏却摇头说道:“这样不妥,应当是老父母先走完公文的流程,我新阳旬报再把老父母的这份政令刊登出来为好……若是能配上老父母的解说则更好……老百姓或能识字,但多是不通公文,老父母能对此逐一解读,以白话刊登出来,则更能让百姓看的明白!”
宋知县稍一想也就明白了,点头说道:“子良所言甚是,是本官心急了。”
当下宋知县就喊来下人拿来文房四宝,手书一份政令,然后着师爷润色成为一份正是的公文,接着盖上大印下发到公房中。
主要内容不多,就是让老百姓做好秋收准备,税收要及时,粮税几何等等。
和历年来的公文差不多,但是经宋知县的解说,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引人注目的是粮税多少的问题,公文说是十五稅一,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十五分之一的粮食要交税,这是朝廷的定制,并无不妥。
却还有祖制在,也就是前文说道的赋税定额的问题。整个新阳县的赋税定额一直是在九万石的样子,而近些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正值清明盛世,加上新开的土地,整个新阳县的收成较国初定下的标准要提高三倍不止。
乡间收税是十五稅一来收的,赋税要收到三十万石左右!
而新阳县上交的赋税依旧只有九万石,其中二十一万的差额都被乡绅和胥吏吃掉了,当然,他宋知县也是占着大头的,这叫和光同尘!
宋知县所载的宋家乃是河北大族,并不缺银两,相比银子和官位、抱负,他很自然的选择了后者,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揭开了这中间的关系。
宋知县解说其中的奥妙,言道只要全县能上交九万石的赋税即可,每个乡镇按照田亩多少的比例进行分摊,而每个乡镇的赋税则同样按照百姓所占田亩的比例进行分摊即可。
报纸还很是体心的为大家把这个比例算出来,按照自家的田亩数,乘以这个比例即可得知今年秋收要交多少税了!
这还了得?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有些个甚至喜极而泣,而掌握着税收的乡绅则是咬牙切齿,直言这报纸乃是妖言惑众,让大家不要相信。
但是宋知县派出心腹之人坐镇在府衙门口,但凡有拿着报纸问文章真伪的,他都耐心的解释和回答。
赋税不止是对国家重要,对老百姓也很重要,根据报纸上所言,自家只要交往年三分之一的赋税即可,这差不多是全家人两个月的口粮!
对此谁敢不认真对待?自打报纸传开,一下子就传遍乡里,老百姓凑钱也要买上一份报纸,只为了拿到城里去问一下这件事的真伪。
很快,原有的两千份报纸卖脱销,连着加印三千份才算告一段落。
但随着秋收的来到,全县各处每日都有械斗消息传来。
乡民们要少交税,但地主乡绅却不同意,两方各执一词,一方以宋知县所言为据,一方则以国朝律例为凭,由此矛盾开始越来越有所升级。
宋知县感觉到了各地的暗潮涌动,就招来陆骏问道:“子良,乡绅地主反对之声甚重,县衙里的这帮胥吏更是阳奉阴违,如今却为之奈何?”
陆骏听到了宋知县把情况说明,一时间也是头大。水至清则无鱼,这一下子把那帮人的奶酪不止是动了,而且是直接扔掉,半点渣渣都没留,没人反对才怪哩!
见陆骏沉默不语,宋知县说道:“唉,也是本官太过心急,思虑不周……不止是乡绅得罪狠了,连县衙这帮胥吏也都完全不听我的命令……如今只能求助于你。”
别看宋知县说的可怜,但陆骏见他并无惊慌,想来已经心有定计,或是不满意,或是想要问问可有更好的方法。
“老父母不用着急……这等利民之大事,放在何处也不会短了理,拿到御前只怕圣上也会赞一声爱民如子。”陆骏先夸赞道。
“子良不用为我带高帽,如今乡里之间,这百姓和乡绅关系是愈演愈烈,弄不好就要出乱子……如今这关该如何度过?”宋知县摆了摆手说道,却也满意陆骏所言。
闹大了才好,闹大了才能让朝廷关注。如陆骏所言,他这等利民之举,到哪里都站得稳,纵然有些人对此不满,但也不回明面反对。
这民心所向,就是大势,且堂堂正正!
但是闹大了,对宋知县或是个不小的污点,哪怕因此名满天下,但朝廷对他的使用上却是要小心翼翼了!
宋知县虽有法子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思来想去,都不能妥善处理,总会留下些后患,还是其师爷说道:“某观那陆骏陆子良胸藏锦绣,多奇志,富有韬略,或可招他前来相问。”
“想不到黄先生对其评价这么高。”宋知县狐疑的看了眼这位黄师爷。
第四十三章 求解(上)()
黄师爷就是家族派给他的那位师爷,帮他打理关系,主持事物,能力非凡,对其多有倚重。
能得黄师爷这么高的评价,让宋知县很是吃惊。那日陆骏同顾长君一道前来,虽交谈过,政令上报的主意也是陆骏出的,但是宋知县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一则陆骏年纪尚轻,二来也没什么名气,若不是同顾长君一道来,他根本不会见陆骏。
“或许大人对其不怎么关注。”黄师爷笑了笑说道:“自打报纸闹出来这好大风波,我就遣人去调查了陆骏一番,这一调查可不得了!”
“说说看。”
“陆骏其人,乃是县北境八丈河镇人氏,元庆十年中的秀才,之后却弃考从商,帮助其父打理生意……今年四月时,钱庄遭人陷害……”
黄师爷把陆骏的事迹说了一通,接着说道:“有两点可看出其人不简单:钱庄危机那次,能够从府衙借来银两,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同时也让人对他的背景琢磨不透。但我查过,在此之前他和府衙并无联系,由此事之后才和府衙搭上关系,为此还在府城开了间小分号,专门用来在府城打点关系。”
“一个在府城没有半分关系的人,竟然从府衙借来银两,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都表明他为人不简单。”
“还有个传闻,说当初因为银两缺口太多,陆骏为了借银,拿婚约和其有着娃娃亲的杨家换来了白银三千两。杨家一直看他不上,杨夫人想悔婚的心思在杨家也是路人皆知……最近和府城的刘家结了亲,大人还去吃了杯酒呢。”黄师爷有些拿不准道:“不过不知这传闻是真是假,若是真的,可看出此子的心智着实不凡,却也有些……凉薄!”
“想来不会是真的。”宋知县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