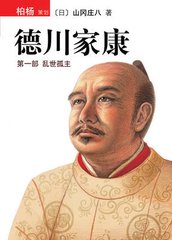德川家康-第3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岛津大人究竟为何如此气愤?难道他真的有恃无恐?”
宗传并不正面回答,岔开了话题道:“先生要多劝关白莫贪恋女色啊!不然,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事来。那些潜在的威胁,真让人担心。”
“哦?”蕉庵蹙眉坐下,“关白误估了形势,恐怕必有一败。可能因我们对他认识有偏颇或估计不足,他竟转不过弯来。”
“人啊,毕竟做了关白,性子有些变了。”宗传道,蕉庵举手止住他,道:“不能这么说,否则不就是说我和宗易……不,是与现在日本第一茶人——利休居士的训示相违背了啊。”
“实际上,去年正月特地把宗湛先生从博多叫来和关白见面,就是我们着手安排的。”
“您的意思……”蕉庵沉吟。
“关白大人给岛津一封信。”
“内容和你我听说的不一样?”
“是,他照例又夸大其词,说天下大部已经统一,便想劝岛津投降。”
“唔!这很糟。”蕉庵叹道。
“不错。”宗传再度搔搔鬓角,“所以,当神谷宗湛先生再把利休居士和幽斋先生的信函交给岛津义久时,岛津嗤之以鼻,拒收。”
“哦?糟!”
“大人应该清楚,除了岛津,北边尚有北条和伊达。他也应记得自己在德川之事上怎样费尽周折。那信函实是有欠考虑。”
蕉庵苦笑:“那么,利休居士知道此事了吗?”
“知道,在安艺的二十日市相遇时,我向他和盘托出了。”
“居士怎么说?”
“他一脸苦涩。可是,岛津大人也可有些体会了,关白大人的信函固然傲慢,可是岛津竟让关白亲征九州,这也太莽撞了。”
此时木实端茶进来,二人止了话。木实道:“洗澡水已备好了。”
“是,这道菜是最好的,待会儿我要好好品尝。”蕉庵递眼色让木实下去,又对宗传道,“那么,此战规模非同小可了?宗湛先生怎么看?”
“他说,这是九州的‘小牧之战’。”
“九州的‘小牧之战’?”
“是。他说,他从一开始就错了,本不该听命于秀吉、义久等人。然而这不过是对大势估计不准。可是,秀吉率领如此庞大的队伍,即使岛津明知必定失败,也不可能轻易臣服。因此,对关白大人也是一次有力的磨炼。确如宗湛先生所说,是九州的‘小牧之战’。”
蕉庵一直凝视空中,无言。所谓战争,不只为了利益,还涉及志向、名声等,甚是复杂。就凭岛津义久的实力,实不足与秀吉抗衡。此次战争对义久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大大阻碍了堺港人与海外的交易。
因此,堺港人悄悄把神谷宗湛从博多叫来:于去年正月初三出席大坂城内的茶会,把他介绍给秀吉,目的是阻止战事。众人商议,决定先让岛津氏老臣伊集院忠栋拜利休为师,学习茶道,拜细川幽斋为师,学习和歌,使他们起到沟通双方的作用。当然他们未能阻止秀吉动兵。
堺港人致力于把应仁之乱以来将一切诉诸武力的恶习,转化为以理智来解决纷争。理性才能带来天下太平。也可以说,此举是堺港人的尝试。丰臣和德川的矛盾解决,便是得益于他们的各种努力。岛津氏的问题也当这么解决。他们终于使得秀吉延期到三月才出征,然而岛津氏却无积极反应。他们急急派宗传去九州探询实情。在此期间,秀吉已迫不及待,终于决定南征。
如今根据宗传的说法,岛津义久乃因秀吉的信函而产生了误会,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过去,利休居士几乎一直跟随秀吉,这一次也在其身旁,却仍无法阻止这场战事——堺港人的实力,还不足以主宰时局。
蕉庵遗憾之余,焦躁难耐。利休居士更是咬牙切齿,因此他碰到宗传,也无话可说。他们已经举起“茶道”这面新的旗帜,企图用这种强大的无形力量取代武力。
事情并非毫无成功可能。堺港人劝秀吉把黄金茶室搬到小御所,依据敕命,赐宗易利休居士的名号,为天下大名茶道之师。除了毛利、小早川、吉川一族,前田利家、细川忠兴、蒲生氏乡、秀长,连大政所都成了利休的弟子。但这一次却失败了。这次的筹划人不是别人,正是纳屋蕉庵,故蕉庵尤为遗憾。
“蕉庵先生,要不要再做些什么?”宗传担心地注视着蕉庵。蕉庵一面点头,一面苦笑,对宗传道:“不可丧气,事已至此,要再麻烦你到博多走一趟。”
“别说一次,十次都可以。先生有何良策?”
“无甚良策。我只是心中不安,利休居士会否因此事而心中难平,与关白大人发生冲突?”
“哦,不无可能。”
“你知宗易先生个性要强,连关白也不会谦让。但若关白遇事,他亦不会袖手旁观。”
“有此可能。”
“故,你能否再走博多一趟,把我的想法告诉居士?”蕉庵道。
“先生是想……”
“定要避免残酷的血战。关白非同常人,他可耐心等待岛津醒悟。定要不厌其烦地向居士说明。”
“避免残酷的血战……”
“对!所以,对关白也定要灌输些新的想法。你说他贪恋女人,可是他并非那样的人。因此,设法全力阻止战事才是正途。”蕉庵目光四处游移,道,“岛津降服只是早晚之事,有必胜的把握,故不必操之过急。既然特意陪关白到九州,就把好事做到底,以流芳百世。请这样告诉居士。”
“流芳百世?”
“是。既然专程到了那里,就把那块土地打造成为日本的新基地,再回来。”
“哦。如此看来,关白大人定会拍手叫好。”
“定要让居士尽力,不可让九州陷入战乱。天子子民自相残杀,终是耻辱。仔细考虑生存之道,才不愧为史上无二之关白。故,向他进言,把彼处变为第二个堺港!”
“第二个堺港?”
“便是博多啊!宗湛先生和岛屋先生在那里大兴茶道,让关白自己划分版图。这么一来定会有趣,一定可以避免战事。”
宗传拍拍大腿,起身道:“好!好计好计!不如此,岛津氏与关白大人僵持不下,必有一战,那样一来,后果不堪设想。”
蕉庵不理他,继续道:“这种说法是开导居士的妙方。你告诉居士,特地以天下第一茶道名家身份去九州,就要把那里的名人都收为弟子,方能回来。明白吗?把大友先生、岛津先生都收为弟子,否则堺港人岂有台阶可下?”
“唔!不愧是蕉庵先生。”宗传佩服不已。这确实是妙计。巧妙地利用秀吉和利休的性情,然而也是为了岛津、为了日本,尤其是考虑了堺港人,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善政”。“宗传,另,你告诉居士,说我请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关白起争执。只要我蕉庵活着,就不会让居士在关白处受丝毫委屈。大家要同心合力,密切配合。请不断叮嘱他。”
“遵命!不过,蕉庵先生,居士和关白真有可能争执起来吗?”
“很有可能!”蕉庵这才收回目光,看着宗传,“虽然双方互相了解,互相敬重,但他们性情都很急躁。”
“一对好胜之人!”
“而且,关白不明居士的风雅之深,居士也不明关白的器量之广。由他们不时产生分歧,就可得知。例如,关于照居士意见,令古田织部烧出的茶碗的颜色……”
“茶碗的颜色?”
“是。居士说黑色典雅庄重,能够显出古风之威严,而关白却外行了,他喜欢红色。”
“关白本就喜爱黄金茶室之类啊。”宗传道。
“黄金本身虽华贵,可是执著于黄金的人,心中却不免卑俗。说红色乃杂芜之色,关白必不以为然。”
“的确如此。”
“但居士却非要关白明白。而关白一旦认定,无论谁说,都会断然拒绝!”
“比如红和黑?”
“是啊!”蕉庵长叹道,“这可能便是人之宿命,可我却想改变这宿命。但居士若和关白争吵,我便无能为力了。”
“嗯下心服口服!”
“因此,希望你办好此事。何况你又敬重神谷宗湛先生。为了给关白、居士各送一副良药,只好由你再赴博多一程。当他们心情畅快时,就让他们知,岛津大人也是天下不可多得的贤能啊!”蕉庵说到此,方开怀大笑。
宗传好奇地望着蕉庵。他把在安艺的二十日市碰到的木偶般的秀吉,与一心想控制秀吉、隐居于市井的蕉庵一比,就深深觉得世间之大无奇不有。方今天下武将,都汲汲营营只欲靠近秀吉;另外一类人,则绞尽脑汁与他对抗,以求存活。在后者眼里,秀吉强大如中天之日。
蕉庵却不把秀吉放在眼中,认为秀吉不过是乱世需要的守备大将。不只是对秀吉,从信长干涉堺港开始,蕉庵便常常出语惊人。起初,他背地里叫信长的奉行为“织田伙计”。但他主张为了日本的未来,要善待“织田伙计”。同时,他又把宗及、宗易、宗之等陆续荐到信长的茶室。而当信长在本能寺归天之后,蕉庵很快把大旗交给了秀吉。
“光秀不过一介老朽,此后要多关注秀吉。”他巧妙地通过投票的方式,察知堺港人的真意,然后全力支持秀吉。不用说,信长原来的茶友和后来依附的人,便纷纷进入秀吉的茶室。除了宗易之子绍安、宗久之子宗熏等人,还有药房的小西行长、刀剑师曾吕利新左卫门,以及宗安、宗传,从五山信徒到公卿,都投入蕉庵的门下,已然成了堺港人的地下朝廷。
可是,此次在岛津和秀吉之间,他的斡旋却没成功。堺港人的想法是尽快让两方放弃对峙,开放博多、平户、长崎等港口,以那里为基地,迅速向南发展。这个计划原本不错。据他们所知,西洋诸国已先后出入南方诸岛,若不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坐失良机。
“怎样?先生的心情似乎好多了。”宗传看蕉庵放松下来,“我要先吃些东西,再洗个澡。”
“啊!是我疏忽了。木实!木实!把饭菜呈上来。”
在蕉庵大声叫喊时,却忽地又来了一个人,嚷道:“趁饭菜还没上,曾吕利来了,也来陪你们用饭吧。”
曾吕利新左卫门边说笑边走了进来,和对待秀吉完全不同,他郑重其事向蕉庵施礼,“我有三言两语要说给先生。首先,我也去赏花了……”
“请坐!我正在和宗传谈他再去博多一事。”蕉庵道。他在曾吕利面前,远比对宗传和气得多,一副十足的长者模样。“关白大人近况如何?”
“按计划,关白大人正乘船在宫岛痛痛快快游玩。东边却有动静。”
“东边……是德川大人?”
“不,再往东。”
“便是小田原的北条?”
“不错!本阿弥光二先生之子光悦去了小田原。”
“哦。”
“看来,这可能是德川大人的意思。可是,据他回来说,那里似免不了一战。”曾吕利说着,紧张地直视着蕉庵,“听说最近有人来堺港购买枪炮。”
“哦?若是北条大人,他怎会这样不明天下大势?”
“是。原因便在他与德川大人是亲家。”
“北条以为德川大人会站到他一边?”
“像是。本阿弥先生便是这般推测。”
“那么,德川大人呢?”
“当然毫无疑问。”曾吕利重重点着头,他可能想说,对德川尽可放心,因为德川是站在秀吉一边的。
在木实的指挥下,两名侍女端来了三份膳食,还送上酒壶、酒杯。
“来!请饮酒。从宗传先生开始。”木实先替宗传斟酒,又转向蕉庵道,“隆达刚才来说要给您弹三弦,唱小曲,女儿告诉他,您有客人,要他稍等。”
“隆达?他是来给我唱他拿手的小调的,先给新左斟酒。”
“是!失礼了!请,曾吕利先生。”木实一面给新左卫门斟酒,一面道,“父亲,隆达说,万代屋宗全先生好像病得不轻啊!”
“万代屋病重?”
“是。阿吟小姐太可怜了,万代屋先生如有不测,孩子们都还那么小……”
蕉庵不听女儿念叨,道:“新左,绝不可把枪炮卖给北条和伊达啊!”他声音很低,语气却甚是严厉。曾吕利似大吃一惊,把杯子自唇边移开,望着蕉庵。
蕉庵心平气和,转向木实道:“万代屋病重?”
“是,春天过后就咳嗽不止,有时还痰中带血。”
“阿吟会甘心做遗孀吗?”蕉庵沉吟着,“新左,为了北条一门,要密切监视去往小田原的船。”接着才把视线转到女儿木实身上,叹道:“那姑娘可能真为关白而生。”
“唉,这种事,阿吟应不会答应。”木实道。
“新左,不可操之过急。虽不可心急,但亦有必要使关白大人知晓,时势已然变化。”蕉庵道。
“先生说得是。
“或许不只是茶道可以利用,狂言剧、三弦也不错,还有大鼓、胡琴、和歌……”蕉庵又道。
“对了!”曾吕利像突然想超了什么,“关白摘了一朵有趣的花。”
“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