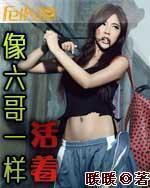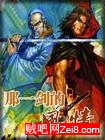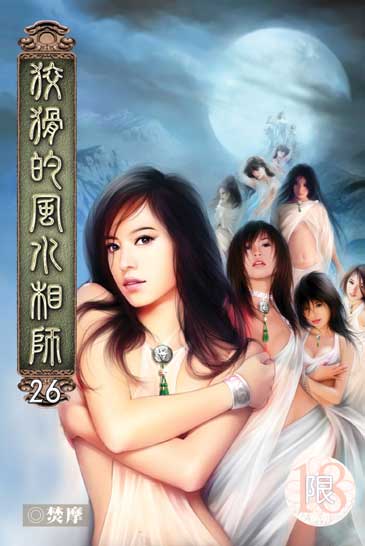一样的风-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蠊粒沂袄确黄叽Φ氖κ舨慷酉蛱旖蚴锌柯#媸碧虻鞫A晃桓笔Τざ贾朗账醣Γ鹑泛么蛉说牡览恚恢笔彼握茉氲焦挥校�
但掌握着华北包括平津命运的“小委员长”宋哲元,执行的是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只是想和日本鬼子搞妥协,保住他的“地盘”。
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20里内驻扎,这就是当时半殖民地的现状。因此,天津仅有装备简陋的保安总队,下辖3个中队和武装警察共1500人。卢沟桥事件后,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驻天津西南的马厂一带今河北省青县,属沧州市管辖,只有两个步兵团和—个警卫连,和几门小口径平射炮以及18挺高射机枪这样一些装备。
27日,李文田接到二十九军部发出的“自卫守土”命令,决心立即抗战。
28日,李文田得知日军已在平津及华北发动全面进攻,又得到军部命令:“固守津市,即行抵抗”。但没有任何支援,如果这时宋哲元能想到他熟知的孙子兵法中的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到二个团的区区兵力支援天津,起到的效果,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在天津广大官兵强烈抗日要求,和中共地下工作的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旅长何基沣(就是近代电影《佩剑将军》的原型)督促下,于当日晚7时,在他前几日整天踱步的会客室里,召开了紧急军政头脑会议。
会议决定乘鬼子攻击的重点放在北平,驻天津兵力空虚,分几路打击驻天津的鬼子。重点是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司令部和东局子机场。我军兵力5000余,鬼子兵力5000余,兵力之比约为1:1。
7月29日凌晨1时,各部队按照指定任务,分四路同时向驻津日军发动攻击。由于突然袭击,初战进展较为顺利,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鬼子占的地方。
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刻,北平方向偶尔的枪炮声像是点缀。
这一路负责攻打东局子机场的朱春芳团第一营与保安二中队的战士,按照要求每人准备—小壶汽油和一盒火柴,飞速奔向东局子机场。为了抢时间特地选派两名排长跑在部队最前面。当接近机场门口时,他们为了不惊醒里面的鬼子,先用大刀,咔嚓几下,砍死了两名日本哨兵,又见从机场里开来一辆汽车,随即被我方击毁。
凌晨2时,参战大部队赶到,全体一同冲向机场停机坪。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驾驶员都睡在飞机身下,听见枪声立即惊起,爬上飞机进行发动企图紧急起飞。中国战士扑向机群,泼上汽油点燃。七月底正是天气炎热吃西瓜的季节,加上跑步前往,战士身带的火柴被汗水浸湿划不着火,仅有七、八架日机起火。战士们便从已点燃的飞机上引过火种继续点燃其他飞机,或用手榴弹炸毁日机。日军见状立即进行疯狂扫射,中国军队安排兵力顽强抵御,但仍有12架日机起飞。有10余架日机被烧或炸毁,机场内烟火冲天、弹声隆隆。有10余架鬼子的飞机被毁啊,虽然和高志航率领的飞行员们击落鬼子的飞机战法不同,但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也是很不错的战果了。
3时许,中国军队攻进日本航空兵团司令部,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包括航空兵正在使用的电报密码。中国军队将日军压制在机场办公楼和营房工事里,占据了飞机场。天亮后毫无遮掩的中国军队被暴露,加上飞起来的12架日机连连向中国军队疯狂反扑,龟缩在办公楼上的日军居高临下配合扫射,中国军队伤亡很大。
另一路进攻驻海光寺鬼子司令部的部队,虽未能冲进鬼子的巢穴中去,但包围了海光寺,同样给鬼子给与较大杀伤。
日本驻津总领事掘内干城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参事森岛守人发电报:“从29日午夜即凌晨12时左右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危急的状态”。
这时如果再有一、二个团的有生力量拿下鬼子司令部,平津的战局可能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
但天津的胜利,只持续了短短的半天,15个小时。到29日下午二时许,大沽口的援军遭鬼子舰炮的攻击,没能及时赶到天津市区作战位置。同时北平方向南苑激战已近尾声,佟、赵两位将军已战死,鬼子分兵来救天津了。
李文田等几位头领商量决定撤出天津。
中国军队撤出天津过程中,少数保安队员仍坚守战斗阵地,同日军继续进行战斗。30日中午,日军发现在某厂一座20多米高的八角水塔上仍有中国保安队员在抵抗,便下令施放毒气。4名保安队员虽陷入重围,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从水楼塔上走出来,虽然中了毒气,脚步踉跄,他们仍拼尽全身的力气,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刺死日军6人。这些战士虽全部牺牲了,但人们会把他们当做真正的民族英雄来记得。
随着华北两大城市的陷落,平津作战就这样基本结束了,和抗战初期作战一样,是这样的被动和无序,对即将沦陷区域军民的撤退、物质的转移,毫无帮助,只表现了中国普通士兵的英勇,反忖出腐败当局的虚弱。
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29军撤出北平是灰溜溜的,而撤出天津是昂着头走的。历史学家称中国29军及地方部队在天津的短暂得胜,是平津作战中少有的较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取得的作战战果却很好。
如果说天津中国军队的反击能得到其他部队强有力的支援,在已经包围住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前提下,来个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常用的围点打援的战术,那将取得多大的战果?
同样,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能有29军这样的人员和装备,有包括华北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这样的活动区域,来和鬼子作战,不知能消灭多少鬼子?牵制多少鬼子的有生力量?
但历史没有如果!
第十五章两位上将()
(一)。
此时,延安也日夜关注着华北局势,1937年7月8日和7月23日,中共中央两次发表宣言,指出“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放弃任何妥协立即实行抗战,并致电宋哲元和蒋介石要求共同抗日。
(二)。
1935年,根据《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还有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宪兵三团,蓝衣社等特务机关被迫从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撤退。由原来中原大战后残存的西北军各部组成的29军,进驻两市两省。29军长宋哲元还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华北一方诸侯。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为了躲避,宋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于1937年2月底离开回老家,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
1937年7月7日在宛平正式打响后,而身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一直在是战是和中徘徊。
在南京政府和29军的部下的一再催促下,7月12日,宋从山东老家回到天津;他不曾料到29军副军长秦德纯等人已与日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宋哲元轻信秦等说日本决心把此次事件作为“地方化”、“就地解决”的“不扩方针”,于12日发表了力主“和平”解决的看法和主张,竟承认了秦德纯等所签订的所谓停战三项协定。
7月19日,宋哲元由天津返北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等。
当他后来发现日本鬼子増兵,并已三面包围了北平时,他才如梦方醒。7月27日才把他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师派上去,28日日军就全面发动进攻,显然为时已晚。
还未开打,29军在判断战场形势和排兵布阵上就先输了两阵。虽然有佟麟阁、赵登禹和李文田率领的前线将士的英勇无畏,但29军在整个华北的失败已在所难免!
(三)。
从7月7日的卢沟桥,到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表明,它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所谓上层的共同意志,绝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是日本长期以来侵华野心的最终全面实施,也绝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中国已经丧失了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北等一系列领土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还霸占了中国剩余领土内一系列军事、经济主权,更甚而要侵占华北,中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不得不还手的最后地步了。日本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退让,渐进式的蚕食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行不通了。为此,日本急不可耐地抛弃了渐进式蚕食的方法,为了实现预定的大陆政策,对中国开始全面出击,企图根本上灭亡中国。然而,侵略者总要给自己粉饰一下,说什么是由于中国的“反日”行为才造成了日本的被迫反应——简直是一派胡言,潜台词无非是“中国应该顺从地接受日本的统治、占领和奴役”。
而中国当时的南京政府呢,虽然蒋好似比宋哲元等较早看出了日本的野心,但命令总是模棱两可,
(四)。
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毛主席也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但这除了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以外,并不能改变平津这两座华北最大城市陷落的实际,又有多少中国人一夜之间成了亡国奴?
(五)。
从1874年侵略台湾起,日本近代史上发动的14次对外侵略战争中,10次针对中国。挑衅的次数,多的更是无法统计。日军的铁蹄从中国的东三省踏至内陆。
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580万吨,是中国的145倍。
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卢沟桥的枪声好像看起来偶然,29军的失败,好像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但当时国力孱弱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历史的必然。
第十六章必须有人接()
(一)。
1937年8月5日,南京
8月南京的天气,人们常用火炉来形容,其实应该要用蒸锅来形容更为妥帖。
南苑惨败,北平、天津已丢失,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虽然南京——当时的首都,还未见战火,但除了傻子,大概都知道,日本鬼子的下一方向,肯定是民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了,当时称京沪一线。中山陵依然巍峨,中山大道在当时是那样的宽阔,数十里的秦淮河依旧繁华,不知那些歌女是否又在唱着后庭花?大官大员们是否还在纸醉金迷中消磨着时光?但不少战后的记述都说当时的首都南京是汤浇蚁穴般的场景。火热的天气掩不住即将到来的萧杀。
胡适和陶希圣乘坐的汽车,离国民政府(后来的总统府)好远就被第一道岗哨拦了下来,一律必须下车检查。陶希圣一脸不高心,因为陶希圣掏出了侍从室的派司,还认真核对后,才得以通行。不像以前,往往是哨兵刚看见这种蓝布面的,印着青天白日徽的派司,里面的内容一般都不看就挥手放行了。胡适看着宪兵们一丝不苟的着装,以及胸前挎着的美制冲锋枪上闪烁的烤蓝,反而觉得心里有一点宽慰。再想想一路上眼见高大建筑上明显增加了防空哨,他心想,如果当时全国的武装部队都有这样的素质和纪律,何愁打赢不了小日本啊!
汽车绕过有沙包、铁丝网的掩体,到了第三道岗,即大门前的岗,陶希圣的侍从室的派司也没用了。必须政府大楼里面有人出来接,才能进到大楼里面去。陶希圣通报了所找人的部门,岗哨打了电话。不一会,出来一位年轻人,穿薄中山装,左胸前佩着青白的徽章,并别着钢笔,一身干练的样子,一看就是个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他见到胡,陶二人,恭敬谦和地用带着浙江口音的话语说:“陈主任有要事外出,关照过了,有事请进去讲。”别小看这需要里面的人接,无形当中等于又增加了两道岗哨。
(二)。
穿过长长的走廊,主客三人来到会客室坐下。会客室的后面就是国民政府文胆陈布雷的办公室,陈布雷的办公室对面,就是蒋委员长的办公室,这几间房间就构成了当时民国最高级别的办公场所。
这时,有穿军服的侍从端上茶,轻轻关上了门出去。年轻人对胡、陶二位说:“陈主任有事,关照我接待你们,有事请讲。”说着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