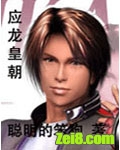大顺皇朝-第1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全垨此刻,才算有了旧日的一丝风采,镇定自若地笑道:“若将军信不过我,我把训练之权,还给将军便是。”
一听朱全垨想撂担子,陈方运连忙赔笑道:“朱大哥勿恼,我这不是担忧将士们的性命嘛!既然朱大哥说没事,那肯定是没事的。”
听了这话,朱全垨在心中暗暗说了一句:“知道是这样,你还不闭嘴?”这句话当然不敢说出去,朱全垨没有理会陈方运,而是静静地观测着水中的情况。
陈方运讨了个没趣,过了一会,悄悄地离开了岸边,自行去偷懒了。倒是朱全垨尽忠职守,直到禁军没了力气,才宣布停止训练。观测了一遍训练成果,发现第一日,喝饱了水的禁军,不过五分一强而已。而粗通水性的已有半成之多。
朱全垨不由地叹道:“禁军乃天下精锐,先前不信,现在倒是信了。”
要知道,他拉起的那千余人,能在这么短时间粗通水性的,也不过三十余个天赋较好的。和禁军一比,那真是天壤之别啊!(。)
ps: 看着历史战力榜如火如荼,心中很想参加,奈何订阅差得太多了。要是能参加的话,我把存稿全都缴纳了……
第三百二十六章:关学兴起的前奏()
梁山水泊岸边,朱全垨在全力以赴,训练着大顺禁军。而这边厢,卢胖子给他写的奏疏,总算是通过飞马急报,送到了陆承启手中。别怪这年代的办事效率慢,而是那官道,经过黄河一次次决口,已然成了黄泥塘。要想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京城,非得绕路不可。这般一来,花费的时日便长了。
而卢尘洹又明确告诉飞马急报,这并不是紧急军情,可以悠着点。卢胖子这不是怕飞马急报累着,而是心疼那些驿马,被这么一次次摧残,没有个把月的恢复,喂养精饲料,肯定是废了。卢胖子爱马如命,又怎么会看着这些好马,因为传递一个不重要的奏报,而消耗马力呢?
卢尘洹当然不知道,就是因为他的一时兴起,却差点毁了朱全垨的前程。陆承启是什么人?重生而来的人士啊,他当然知道人才是最重要的。要是因此毁了一个懂得水战的人才,陆承启不把卢胖子剥皮剔骨才能消心头之恨啊?
原来,这飞马急报以为这不过是寻常的奏疏,当然也是受了卢胖子的误导。当他把奏疏按常规递给内阁,便自个回去潇洒了。要不是今日当值的是很负责任的内阁首辅徐崇光,恐怕这折子要再等得个把月才能重见天日,再票拟递给陆承启,继而重新下旨到东平府中的禁军,没有两个来月根本不可能。
徐崇光这举动,间接救了卢胖子一把,恐怕连徐崇光自己都不知道。而见到徐崇光按例递回票拟的折子。陆承启却有些疲倦了。他并非一个机器。即便设立了内阁。每日的工作量,还是超出了八个小时,而且从无休息,周末正常上班。要是在后世,陆承启早就去申请劳动仲裁了。可这皇位坐得,痛并快乐着,闲暇之时,便苦中作乐好了。有什么大不了?
让陆承启头疼的,是近来自《大顺民报》刊登国子监辩道一事以来,各大士人所办的报刊,便集中火力,猛烈地抨击起张载,以及他的关学来。特别是《大顺民报》把关学主旨的那四句话写上去之后,更是让那些无所事事的举人,骂得狗血淋头。再加上陆承启下旨,赐张载同进士出身,封为秘书省编修。更是让诸多屡考不中的秀才举人们羡慕嫉妒恨,差点红了眼。
《大顺民报》一出来。那《时政报》便撰文骂道:“此匹夫,胆大欺君,宣扬歪理邪说。至圣先贤,又何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四句话?无稽之谈,实属误导世人!若圣上不将此僚收监关押,任由其妖言惑众,则天下非大乱不可!
悲夫,我大顺开创科举以来,每每尊崇孔圣人。却不闻其余诸子,非太祖不识邪?非也,皆因儒术乃治国精要,人君者,不遵天意,自取灭亡之道。前有暴秦之车,我朝绝不能重蹈覆辙……”
陆承启看完最新一期的《书社报》之后,不得不佩服那些读书人,为了捍卫儒家正统地位,也是花尽了心思。张载的关学以《易经》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这让一些既得利益的官员,似乎嗅到了一丝不安。而看到小皇帝又这般看重关学,便动了心思,要彻底抹黑关学。他们请人代笔,断章取义,极力抹黑关学,希望小皇帝能看到,能及时的迷途知返。那样的话,他们的利益便会保住了。至于牵头之人,陆承启不用问都知道,定然是那些高官。他们生怕自己的后进者少了,分不到权柄,才如此抹黑关学。
但陆承启是什么人?岂能被这等小伎俩打倒?陆承启最大的舆论武器,便是报纸。以《大顺民报》的影响力,洗白关学岂不是手到擒来?
不过,陆承启并不打算这么做,而是默默地计划着,如何在下一次科举中,以关学为骨,孔、孟为体,结合算学,取得真正的人才。
要是天下士子都知晓了,关学是下一科科举必考,他们还会不去钻研吗?上有所好,下必投之的道理,陆承启早就明了于心。
《时政报》见《大顺民报》等报刊都沉默了,不是转而报道其他事情,便是避而不谈。这令得《时政报》愈发地得寸进尺,几乎都说道,要是小皇帝不回归正轨,大顺就要灭亡一样。
陆承启看着他们的疯狂,冷笑不已。若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时政报》越是疯狂,就代表日后跌得更惨。
这不,陆承启都让张载拿出一整套试题来了,借口说是考较一番自个。张载自然乐得陆承启好学,不遗余力地编了一套试题。还真别说,陆承启做完之后,交由张载批改。张载改完之后,再次递回给他。这一来二去,便有了标准答案。陆承启这一招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有谁知晓?
虽然这套题不算太难,但主要观点,在于亚圣孟子的言论,这一旦变成科考题目,肯定会难倒不少不看《孟子》一书的举子。再到后面,考究的是简单的《周易》,这是一个辩论统一的题目,非得有着深厚的《周易》功底,才能对答如流。没看过的人,自然是两眼一抹瞎了了。
陆承启拿着这完整的试题后,心中奸笑:“看看你们的伎俩厉害,还是我这一手阳谋够力!”
这个时空,因统治者畏惧《孟子》的一书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孟子》批为异端邪说,这使得《孟子》在问世以来,虽被民间大儒认可,却不受当朝待见。要是陆承启真的打算考《孟子》的话,恐怕能符合他心意的士子,一万人中都没有半个。
这要怎么调低试卷难度,便成了陆承启头疼的问题。既能保证所取之士全是人才,又能保证关学的兴起。这个时空,自周敦颐的“理学”未曾兴起,倒是省了受那极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所毒害。
正当陆承启头疼的时候,却接到卢胖子的奏疏,只好放下了那沓试题,摊开了奏疏看将起来。当看到有水贼头目来投,询问是否接受的时候,陆承启立时便做了决定,批红道:“当即封朱全垨为禁军教习,若日后破了梁山水贼,再论功行赏。”
写完之后,陆承启觉得很是奇怪,这应当是飞马急报几百里加急奏疏啊,为何看卢胖子写的日期,竟然是二十多日前写下的?而且由徐崇光递进来,更是奇怪了。难道这中间有什么误会不成?
陆承启想不通,也不想细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管是徐崇光的失职,还是卢胖子的失职,都是小事一桩罢了。因此寒了两人的心,有点划不来。
陆承启想到这,便唤来了小黄门,让他当面漆好火漆,装入木匣子之后,送到飞马急报那里。可怜那飞马急报还没坐热椅子,便再次被遣返了东平府。怀揣着这沉甸甸的木匣子,飞马急报也是有些后怕,心道:“卢指挥误我,若不是陛下宽宏大量,我非得吃军棍不可……”心有余悸之下,匆匆忙告诉他浑家一声,又跑去长安驿站,准备出发了……(。)
第三百二十七章:进入梓州路()
话说苏轼和秦明等一干人,自京兆府,经凤翔府乘船直下,途经利州、巴州,最终乘马车到达梓州。一路上,巴陵胜状,以及川地风情,都尽收眼底。
苏轼乃眉州人士,中状元以来,除了跨马游街之外,便没有回过家乡。这次来到梓州,已然靠近成都府。成都府路再有百多里路,便回到了眉州。过家门而不入,几乎都可以说是衣锦夜行了。
秦明等皇家军校学员,见苏轼对梓州风貌都熟稔于心,还用方言和周围之人交谈起来,无不惊奇,问之,苏轼才说道:“成都府路与梓州路,人文相差不远。同饮一江水,自古便是儒士辈出之地。《诗经》有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其重孝悌至此也。子瞻乃成都府路眉州人,自是明白此地风情。”
秦明苦笑道:“苏大才子,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一群大老粗,哪里听得懂这些什么经什么书!”
苏轼也有些好笑道:“你们不都是识字的吗?前朝大诗人柳宗元,还写过‘乡禽何事亦来此,今我生心忆桑梓’哩!”
秦明压低了声音说道:“都是托了陛下的福,我等才算勉强学得几百个字。要是之前,那些字,它认得我,我可认不得它!”
苏轼大笑,可笑声中暗藏着悲伤。路过梓州,想起柳宗元的那首《闻黄鹂》一诗,他便想到了已然身故的生母程氏,一时间情绪流露。秦明等人见一路上颇多话的苏轼。进入了梓州之后。便沉默寡言起来。除了例行公事的问话之外。都是闷头赶路。弄得秦明他们好生不适应,还道苏轼是心情不好。
这日,到达梓州城中之时,已然时近黄昏。一行人寻了间客栈,就此落脚。其实苏轼乃是第一次办案,如何入手都毫无头绪。这一晚,苏轼辗转反侧之下,无奈起身。推开窗户,正想赏月之时,却不料天色阴暗,满天无星,更别说月亮了。
不多时,果真下起雨来。雨点敲打在瓦片上,在静谧的天地间,似乎奏出了一番独特的韵味。
看着不远处的涪江水,苏轼灵感来了,顺口吟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人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江似月水如天。”
望江如月是什么意思?正是因为苏轼此时住的房间。就此望去,涪江水如同一弯明月。最后那句,望江似月水如天,如果是按照正史上,苏轼会在此时九年后,在杭州望湖楼作下,原句应为“望湖楼下水如天”,可原句的意境却不如此时这“望江似月水如天”了。毕竟西湖只是一个没有活水的湖,而涪江却是梓州百姓的生命源泉。或许西湖的婉约,与历代文人骚客的描写,使它具备了“断桥残雪”般的意境。可苏轼的文风向来大开大阖,描写西湖还不如描写这浩浩荡荡的涪江水呢!
这话音刚落,却听得门外有人轻声喝道:“好诗,好诗!”
苏轼一听这声音,便知道是秦明了。他关上了窗户,才慢慢地开了房门,一看,果不其然,门外正是秦明。苏轼很是讶异:“秦大郎,怎么你还不睡?”
秦明做了个噤声的姿势,然后闪身进了苏轼的房间里面,轻轻关上房门之后,才以只有他们两人听得到的声音说道:“苏大才子,我刚刚从小二那里,套来一些消息,也不知有没有用,便来和你一同参详。”
苏颂一愣,他倒是不知道,查案还能这么查,也压低了声音,说道:“请说,子瞻洗耳恭听。”
秦明笑了笑,说道:“这原本是监察司那些人的套路,我不过借用罢了。刚刚我花了百文钱,便从客栈小二那里得知,前不久,在他们这里,有两个凶恶的大汉,带了四五个孩童,皆为男童,前来投宿。按理来说,若是夫妻二人带着孩童出游,这又不算得什么。但带着孩童的,是两个大汉,还因为小二怠慢,而踹了他一脚。于是,小二便铭记在心。他们是驾驶马车而来,那些孩童,似乎都在沉睡一样,被两个大汉轮流抱入客房之中。那小二记恨在心,曾偷看他们如何对待那些孩童,嘿嘿,苏大才子,你永远不会想到,人心是多坏!”
苏轼听得他这么一说,忍不住吞了吞唾沫,声调都变了:“那大汉,是怎么对待这些孩童的?”
秦明恨声说道:“这两个大汉,都是会武之辈,概是怕那些孩童走脱,竟使出分筋错骨的手法,卸开了他们的膝关节!”
苏轼闻言,怒道:“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