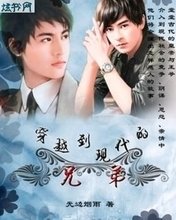拿破仑时代-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4 年秋,阿登纳回到波恩。当他从瓦恩机场走下飞机时,受到基督教
民主联盟要人们的欢迎。他容光焕发,皮肤晒得红红的,显然卡德纳比亚的
阳光使他重新焕发了精神。新闻记者们团团围住了他,在镁光灯此起彼伏地
闪烁、聚光灯炫目地对准他时,他又找回了昔日的感觉。他畅谈了自己回忆
录写作的进展情况,非常自信地表示他将以旺盛的精力和斗志重新投入波恩
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中。
转瞬之间,那令人难忘的卡德纳比亚又被置诸脑后了。他焕发出昔日雄
风,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
阿登纳回来后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举行预算辩论、基
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会议、与国内外政治家的会谈。。
回到波恩的第二天,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
鲁晓夫被人赶下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西方各国,事先没有一点征兆。——
“俄国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阿登纳评论道,“一切都是那么捉摸不
定!既然他们能用这种手法干出推翻赫鲁晓夫这样的事情来,那么一切的一
切又会如何发展,还有什么主意打不出来呢?”他越发感到他对俄国认识的
正确性,这件事再度成为他向联盟党和德国人阐述对苏强硬政策的最好注
释。
阿登纳对西方国家中有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感到无法理解。柏林墙一再
有人被枪杀都已经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现在竟然去为赫鲁晓夫一掬同情泪,
简直滑稽、荒谬。他说:“一想到去年(1963 年),我今天还要发火!西方
简直没领会到俄国粮食危机所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直不了解!1963 年夏
秋两季,这个人不是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吗?西方本该换取俄国人同意
实行真正有监督的裁军并结束柏林的烦恼,可他们退缩了,一个多么好的良
机失去了!”显然,说归说,起的作用已经很小了,接替他的艾哈德正在积
极修复同美国的关系,他可不愿因为阿登纳而得罪了美国人。
对俄国人的警惕和与法国人的友好,仍然是阿登纳时时告诫基督教民主
联盟党内的重要问题。同时,他也不忘记随时为他的党和他的主张作最有效
的宣传。他与新闻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对艾哈德的不满仍然在继续。1964 年7 月,戴高乐将军访问波恩,受
到艾哈德政府的冷遇。阿登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艾哈德不仅冷落了他的朋
友,而且完全偏离了他所确定的法德友好的路线。1964 年10 月,《星期日
图片报》为即将到来的联邦议院选举采访了阿登纳。他借此大发一通。第二
天,一篇大字标题为《艾哈德对此无能为力》的报道,引起了基督教民主联
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内部一场哗然大波。
记者采访是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北莱茵——威斯特伐伦、莱茵兰——法
尔茨、萨尔等地方选举中失利揭开话题的。
记者问:地方选举以后,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现了紧张
气氛。请问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股逆风从何而来?基督教
民主联盟能刹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挺进吗?”
阿登纳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升的趋势,表明了对联邦政府
工作的不满,也是对联邦政府中执政党工作的不满。如果我说情
况不是这样,那显然是愚蠢的,。。您想想历史上的几次反复吧!
根据我的经验:德国人民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领导,如若不
然,他们就感到不满。我对竟选颇有经验。德国人民宁愿喜欢强
硬的明朗态度,而不喜欢软弱的不明朗态度。。如果本届联邦政
府和联合执政党真能果断、灵活和坚定地进行工作,同时能作出
成绩来,那么,两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前景并不会坏,这些确实
是先决条件。
记者问:那您是否在考虑什么具体的事情?
阿登纳一笑:我考虑的事情多着哪!
记者追问:是考虑外交政策,欧洲经济共同体吗?
阿登纳道:我在考虑整个社会领域,这方面一直占很大的份
量。但我也考虑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认为,外交形势方面,特别是对联邦共和国来说,还从来
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局面:在苏俄,竟能秘密准备并搞出像推
翻赫鲁晓夫这种更班换马的事来,而对此竟没有一个国家的大
使,没有一个情报机关,没有一个记者事先能得到点滴消息,这
确实反映了一种危险性,如果再考虑到俄国拥有核武器的话,足
以使人不寒而栗。同时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怎么样呢?
英国人、戴高乐对此将持何种态度呢?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记者插问: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是吗?
阿登纳语气坚定地肯定:永远保持警惕!
记者转而又问:您对戴高乐总统很尊敬,但他为什么会制造
这么多的麻烦呢?现在他跳了出来,和俄国人签订贸易协定,对
莫斯科如此曲意逢迎。戴高乐不是以抵制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
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威胁吗?
阿登纳答道:我认为戴高乐的这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今
年7 月他在波恩受到联邦政府冷遇有关。像戴高乐这样一个人
物,不论是从他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来考虑,还是从他的全部性
格方面来看——对他的性格我有所了解,显然都是不能容忍这一
点的。
记者问:其中也有个人的恼怒起作用吗?
阿登纳说:您对戴高乐不能这么讲,再说,他和德国结下了
友谊,而这是其他法国人所没法办到的。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
法国的利益,并不是对我们有特别的好感。好感在外交政策中是
不存在的,而是本国的利益,即法国的利益起着作用,因为欧洲
的局势由于苏俄的侵入已经完全改变了,而这两个国家又是邻
国。现在戴高乐突然感到德国经常找麻烦,这点我是根本不理解
的。
记者问:您相信戴高乐会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吗?是否可能出
现巴黎——莫斯科轴心?
阿登纳回答:对,肯定的。但这与戴高乐毫无关系。戴高乐
也不会长生不老,在法国,共产党是所有政党中最强大的,而且
也是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党。
记者试探地问: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趁戴高乐还健在的时
候,尽量争取时间,是吗?
阿登纳肯定答道:是啊,我们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好趁戴高
乐还健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得到巩固。这对我们确实是
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德国多项外交政策必须着眼于此。
可以想象阿登纳的这次公开谈话得罪了新总理艾哈德,也得罪了联邦政
府里所有的人。阿登纳捍卫了他自己的观点,也热情维护了他的朋友。对这
个拥有崇高声誉与地位的老头,无论是新总理艾哈德,还是基督教联盟党都
是无可奈何。
不过,形势发展证明阿登纳有关艾哈德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的预言完全正确。艾哈德的胜利多因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的权威也仅
因于选民的拥戴,一旦真正执掌大权,他外交上犹豫不决、政治上优柔寡断
的个性很快暴露出来。艾哈德在争取本党支持、协调各种矛盾、驾驭各种困
难形势等方面的能力远不如阿登纳,他不仅没能摆脱阿登纳时期内政外交的
困境,反而使各种矛盾大大激化。他面向大西洋的修复政策同样未能适应形
势的发展变化,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威信越降越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
主党的声望却不断在上升。
1964 年11 月,长期重病的前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去世了。
这对阿登纳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伤,他失去了一
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
勃伦塔诺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
“我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
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
到1965 年初,他去了法国,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
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这次去法国,报界
评论说他在法国“红得发紫”。在这种恭维客套之辞中,他感受到法国人的
极大诚意,并为此十分愉快。
1965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在几天前圣诞节的
讲话中,阿登纳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世界形势的极大忧虑,况且人到这个年龄
对本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好像是做展览,他希望不搞大型庆祝。
生日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范围内对他的祝贺。在他心里有更
多的事还等着他去操心。1965 年对他来说充满了问号:联邦议院还面临着选
举,基民盟形势岌岌可危;英国工党政府又上了台,谁知道他们会对东方有
什么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换了新人马,去向未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它
又会有什么更深刻的影响?刚刚赢得竞选的约翰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
不得而知。。他最关心的北约改组和欧洲联合问题更是前途未卜。
1 月24 日,从伦敦传来了丘吉尔的噩耗。又少了一个同路人,阿登纳的
心情再度沮丧。曾与他一起搞政治的人越来越少,圈子也越来越小了,世界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从旧有的逻辑出发,阿登纳认为政治局势与其说
在继续发展,不如说在不断恶化。
他仍然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联邦德国同法国和美国的关系。自从艾哈德和
戴高乐总统再度会晤之后,德法关系看来已经摆脱了夏季以来的冰冻状态,
出现了某些好转。虽然对法关系有了些希望,但同美国的关系却一点也不容
乐观。这些年来,阿登纳利用一切谈话的机会向他大洋彼岸的政治伙伴们灌
输:美国的命运同欧洲的命运休戚相关,欧洲应是美国外交的决定性重点,
是美国利益真正的所在。但是,这一基本事实是否也为华府官员们所看到呢?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过去之后,白宫的新主人虽然继续着这一路线,
但从柏林危机、北约改组这一系列事件中,让人不能不感到欧洲的重要性在
华府的心目中已经丧失。难道欧洲已经安然无恙,再也不会有来自苏联的危
险了吗?阿登纳决不相信这一点。他希望美国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2 月5 日,阿登纳在波恩联邦参议院侧屋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纽约时报》
的发行人C·L·苏兹贝格。阿登纳认识他已多年了,苏兹贝格对美国舆论有
重大影响。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
1965 年2 月10 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
当问起八十九岁的康纳德·阿登纳,谁是他赏识的最重要的
人物时,这位前总统拿起他写字台上一张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的签名照说:”就是这一位,他头脑精明,有预见,并且遵守诺
言。”
阿登纳悲观地认为,当前在华盛顿找不到一个这样有才能的
人。他认为,美国热衷于东南亚,忘记了更为基本的欧洲,而他
却在为欧洲的前途担忧。他说,“欧洲大陆是美国的弱点所在。
如果美国失去了它,俄国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也不能摆脱这种疑虑,即华盛顿同
莫斯科为了维持现状而有着默契。他相信,这是美国决定不发展
中程导弹的原因,而阿登纳把这种中程导弹看成是对付苏联炮兵
的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
此外,阿登纳还在想,戴高乐一旦退出政治舞台,则法国和
意大利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就将取得政权。到那时,他
预料西德抵抗苏联的意志就会涣散。
阿登纳相信欧洲今天在军事上是没有防御力量的,而明天在
政治上也将没有防御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正处于1945
年以来的最危急的时期,而你们的国家,西方最大的国家,却无
所事事,不肯正视这种危险。”
阿登纳宣称,他同肯尼迪总统曾就美国发展机动中程导弹和
把它们设置在欧洲以抵销俄国在这种武器上的优势一事达成过协
议。尽管如此,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均未履行这一协议。
阿登纳说,这就使人怀疑,并促使德国去依靠法国给予迅速
的、尽管是微小的核援助的保证,以抵抗苏联的任何进攻。波恩
和巴黎都不幻想它们能单独对抗俄国的力量,但是它们相信,它
们能迫使美国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干预。
在政治方面,阿登纳确信,俄国人正在等待他们能够取得欧
洲的时机。阿登纳抱怨说,西方民主国家接二连三地向它们的追
求赢利的商人让步,因而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