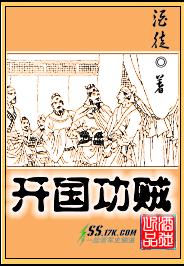开国战将-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不愿谈了;有的甚至警觉地问:“写谁不行,为什么要写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尤太忠将军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他听说笔者要写王近山,一反过去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的惯例,热情地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这一年里笔者曾多次联系采访,均被他一口回绝)。他不但接受了,而且破例把笔者安排在他的书房里与他单独谈。据将军夫人王雪晨后来告诉我,尤太忠一般都在宽大的会客厅接待来访者,很少在书房里接待客人。
笔者清楚地记得,他谈王近山打仗时兴致勃勃,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谈王近山遭受的挫折时心情沉重,充满了深深的惋惜情感;谈到他新中国成立后和“文革”中的境遇时,有一种欲拔刀相助而难酬其愿的悲怆气概。
在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一书中,有尤太忠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尤太忠写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与王近山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一起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同志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我们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从王近山这位老首长、老上级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经验。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曾经在战争岁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结发夫人离婚。他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职,并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下放到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那一天,尤太忠将军向笔者讲了许多王近山将军打仗的故事。后来,笔者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人物素描《“疯子”王近山》,发表在1993年《世界军事》第3期上,发表时标题变为“猛将王近山”,应该说,这是第一篇公开为王近山正名的文章。
从尤太忠谈话的表情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老上级”十分敬重,这种敬重并没有因为王近山将军的落难而发生丝毫变化。岁月动『乱』,人事沉浮,没有使尤太忠将军放弃对一个人的真正情感。
1969年7月,王近山复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的复出,当时在军界上层是一件轰动的新闻,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王近山的复出是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建议的。其实,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将军是促使王近山将军复出的主要推手。
这是尤太忠将军不经意谈到的一件内幕。尤太忠将军虽然是一员战将,但又有独特的政治嗅觉。王近山被处分后,他始终关心着这位老领导。
尤太忠将军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期间与许世友散步。
尤太忠说:“王近山的问题处理得太重了。一个老红军当个农场场长,叫人家怎么过啊?”
许世友:“那就叫他回来!”
尤太忠:“许司令,王近山这一级干部回来,要中央同意啊!”
许世友:“你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我有什么办法?”
许世友:“你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许司令,现在不是要准备打仗吗?”
许世友:“哦。”
正是尤太忠将军对许世友的提醒,带来了王近山将军复出的重要转机。
闻鼙鼓而思良将。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上,许世友主动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王近山很能打,处理太重了,能不能让他出来带兵?”『毛』泽东问:“王近山我知道,你们哪个军区要啊?”许世友立即说:“我们要!”尤太忠将军说,这样又把另一位犯了错误的老中将周志坚也一起解放了。
1969年7月某日深夜1时,南京火车站,一对身穿褪『色』破军装的夫『妇』从郑州开来的硬座车厢里走出。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旅行袋,女的用手拉着个三岁的小孩子,手上还拎着两个网兜,里面装着玉米、山芋、地瓜等杂粮。他们就是王近山一家。王近山夫『妇』一下火车,便对眼前的情景愣住了:三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王近山一家接风洗尘。
那是一幅令人酸楚而又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在《猛将王近山》一稿中写的这一段,就是尤太忠将军亲口对我说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王近山将军永生难忘的一幕。而当尤太忠将军向我叙述这件事时,却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常。他说:那天我到南京开会,住ab大楼(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晚饭后散步,遇到军区司令部的管理局长,他原来是我们27军的干部。
我问他:“干啥?”
他说:“许司令指示接一个老首长。”
我问:“老首长叫什么?”
他说:“叫王近山。”
我马上就对他说:“几点钟到?我也去接。”
他说:“从郑州开到南京的火车,1点钟到。军长太晚了吧,明天你还要开会。”
我说:“你别管,我去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当时他很兴奋,立即给几位王近山的老部下打了电话,问他们去不去接站,但态度都不明朗,有的说你去我就去,有的问去接站好不好?尤太忠怒道,“你们不敢去,我自个儿去!”
对尤太忠将军来说,为老领导复出提建议,老领导复出后去接站,这都是一位老部下应该做的事,是一个人无须考虑无须犹豫的正常行为。他说,老领导落难时不敢说话,落难的老领导到你家门口不出迎,那还是不是人?
尤太忠将军接着说:“到了半夜,吴仕宏来了,肖永银也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去火车站接。看到老首长这个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指着他带的那些农产品说:‘你带这些干啥?’他说:‘自己种的,你们城里人吃不到啊!’”
回到ab大楼,尤太忠将军立即叫管理局长炒了几个菜,给王近山夫『妇』吃。
尤太忠和夫人王雪晨一直陪伴在左右。
我曾多次参加将军们的聚会,老将军们在一起的话题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是“生老病死”“吃喝玩乐”;是“某某人如何了”“某某人应该如何,而不应该如何”“某某人做得在理,而某某人太不像话”
等。他们评判事物的准绳不一定是政治,而更多是出于人情和良知。
“一个跟党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这样处理是太重了,‘文化大革命’冲击老干部就更不应该了。”尤太忠将军讲到这里,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显出沉痛的表情,眉宇中间的两条竖纹陷得更深,那条肉瘤更突出了。
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笔者第二次采访尤太忠将军是1996年4月13日上午。三年多不见,将军得了一场大病,老了很多,脸上肌肉明显松弛了,神情有点疲惫。已过阳春的天气开始转暖,但他还穿着深绿『色』『毛』料军制服,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这次采访,笔者才清楚地看到,将军为什么始终拧着眉头——原来那是两道明显的竖纹,深深竖纹间是一长条略微凸起的肌肉。正是这展不开的眉头,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京剧武生相的效果。
“首长,想请你谈谈长征……”那时笔者在广州军区战士报社任副社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决定为尤太忠将军做一个专访。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忆昔抚今,将军说,“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9团5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17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战士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呀!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笔者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尤太忠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于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60年了,那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藏民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第30章 尤太忠:战将的风骨(2)()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钳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4军、9军、30军、31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八万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
他曾经对笔者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吧,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一位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