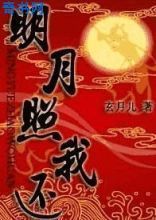我还没摁住她-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简介:重活一世的纨绔小娘们儿付玉,在拥有强大后台下的内心独白:这一世,人家只想做一个安静的萌妹子,那些小贱人小婊砸,都滚远些好么?只想做一只萌哒哒的小米虫,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不要烦她好么?不过…前世温柔多情的夫君,今世怎的变成了高冷腹黑的面瘫脸?!哎哟,小夫君,皮痒的等着被调教?三好妻奴的大红招牌在向你招手嘞!
://157692
一个梁子()
我还没摁住她
文/星球酥
…
序:一个梁子
—
初春暴雨,四月的天被捅漏了,天暗得犹如个锅底。
三十年高龄的校舍在梅子黄时雨中漫着股霉味儿,简直不能住人。
312宿舍里,许星洲捧着笔电靠在窗边,望着窗帘上灰绿的霉菌发呆。
她看着那块霉菌,至少看了十分钟,最终下了这是蓝精灵的脚印的结论——一定是蓝精灵陷害了窗帘。然后许星洲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把笔电一合,站了起来。
程雁悠闲地翻了一页书问:“下午三点钟,学生会要开会是不是?”
许星洲揉了揉眼睛道:“是,会长换届了,得去看看。”
“新会长是谁啊?”程雁问:“我觉得你还是别在学生会折腾了,整天这么多活动,忙得过来吗。”
“我本来就不怎么去啦”许星洲笑眯眯地伸了个懒腰:“我觉得学生会蛮好哦,还可以混活动分。总之是不可能辞职,别的社团吧又不想去,只能在学生会混吃等死了这个样子。”
她说着往身上披了件红和风开衫,又将长发松松一扎,露出一段白皙削瘦的脖颈。她一段脖颈白得像玉,长发黑得如墨。
许星洲生得一身无关风月的美感,干净又明利,犹如江水与桃花,笑起来格外的好看。
“而且,”许星洲洋洋得意地补充:“而且我们谭部长辣么可爱,我当然要和她黏一生一世了!”
——好看,也仅限于不说话的时候。
许星洲实在是太浪了,程雁死死忍住了吐槽的欲望。
…
下午两点半,阜江校区天光晦涩。
春雨噼里啪啦,砸得行人连头都不敢抬。来来往往的学生有的刚刚下课,还抱着本厚厚的大学英语。
许星洲在那倾盆的暴雨中撑着伞,拿着手机导航,自己哼着歌儿学生会走。
她唱歌非常五音不全,哼着调儿跑到天上去的儿歌,走路的步伐轻快得像在跳芭蕾,并且和每个迎面走来的素不相识的人微笑致意。
有个小学妹耳根都有些发红地问:“学、学姐,我认识你吗?”
许星洲浪到飞起,笑眯眯答道:“我们今天就认识了,我是法学院大二的许姐姐。”
新闻学院的许星洲屁话连篇,笑容又春风化雨,小学妹登时脸红到了耳根,不敢和许星洲对视,连忙跑了。
学生会中,许星洲平时负责在部里混吃等死,爱好是黏着他们部的萌妹部长,兴趣是调戏小姑娘。
就这么个混吃等死的人,除了宣传部那几个熟面孔,其他的人她一概不认识。
——包括新上任的学生会主席。
斜风骤雨天地间,远山如黛。
檐外长雨不止,乔木在雨中抖落一地黄叶。许星洲走进上世纪日本人建的理教后将伞一旋,抖落了伞上的水。
这所学校处处都是岁月的痕迹,犹如岁月和风骨凝出的碑。
新学生会主席即将上任,来来往往来开会的社员不少,许星洲顺着风,也听了一耳朵的八卦
“这次新上任的主席是外联部的?我好像都没怎么见过他”
“外联部部长,性别男,数学学院大三。最可怕的是我听说他绩点是满的,去年差点包揽他们院的所有奖学金”
“卧槽居然是数科院的gpa4。0?还干学生会,他简直什么都没落下吧”
许星洲听到这里,登时,对这位主席肃然起敬
整个f大,但凡上过高数的人,都对数科院的变态程度有着清楚的认知。
许星洲高考数学考了143,已经分数颇高,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蠢货,但即使如此上学期修数院开的线代a都差点脱了层皮——她对着他们学院的试卷时甚至怀疑自己智商有缺陷。更有小道消息说数院的专业课挂科率高达40%,每个学生都惨得很。
这里却有个绩点4。0的。
他头上还有头发吗许星洲颇有点苦哈哈地想着,钻进了教学楼。
…
下午两点五十五,理教五楼,许星洲把自己的小花伞往会议室门口一扔。
走廊来来往往全都是来开会的。这次会议事关换届,颇为重要,副部以上职位都要到场:他们要和新学生会主席见一面,以防哪天走在街上还不认识对方。
会议室里,他们的萌妹部长谭瑞瑞早就到了,一见到许星洲就笑道:“星洲,这里!”
谭瑞瑞应是已到了一段时间,连位置都占好了。她个子一米五五,是个典型的上海萌妹,笑起来两颗小虎牙,特别的甜。
许星洲跑过去坐下,谭瑞瑞笑眯眯地对周围人介绍: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节假日从来找不到人的许星洲许副部。”
许星洲点点头,冲着那个人笑得眼睛弯弯,像小月牙儿。
那人瞬间脸就红了。
“许副部一到节假日,不是跑到那里玩就是跑到这里玩”谭瑞瑞小声说:“可潇洒了,我是真的羡慕她,我就不行”
这厢谭瑞瑞还没说完,前主席李宏彬便推门而入。
谭瑞瑞竖起手指,嘘了一声,示意安静开会。
前主席一拍桌子,喊道:“安静——安静!别闹了!赶紧开完赶紧走!”
赶紧开完赶紧走许星洲一手撑着腮帮,发起了呆。
话说以前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刚当上主席的外联部部长
听说他是学数学的,到底秃没秃呢?如果他是秃头的话千万要忍住,万不能笑场如果留下坏印象就完蛋了,怕是要被针对一整年
许星洲胡思乱想道。
“秦渡——”一个人大喊。
李宏彬对门外喊道:“——进来吧,和大家问个好!”
秦渡?这是什么名字?怎么莫名的预感有点不太对许星洲疑惑地挠了挠头,探头往门口看去。
——接着,会议室的前门吱呀一声响,那个神秘的新主席走了进来。
…
走进来的那个青年人个子足有一米八五,套着件飞行员夹克,肩宽腿长,浑身上下透着股硬朗嚣张的味儿。他周身充满侵略的张力,犹如一头危险而俊秀的猎豹。
但那种气息只一瞬,下一秒他收敛了气息,那种危险气息登时荡然无存。
“大家好,”那青年扫了一眼会议室,平平草草地道:“我是前外联部的部长,数科院大三的秦渡。”
谭瑞瑞看了他很久,赞叹道:“真他妈的,我还是觉得他帅。”
“他和我见过的理工男完全不一样”谭瑞瑞小声对许星洲的方向八卦道:“理工男哪有这种衣品,听说成绩也相当牛逼”
然后秦渡转身在黑板上写了行手机号和名字,示意那是他的联系方式,有什么事可以用手机号找到他。
谭瑞瑞趁机倾身,小小声地问:“这么优秀的学长,你有没有春心萌动咦?”
许星洲人呢?位置上空空荡荡,人怎么没了?
谭瑞瑞低头一看,许星洲头上顶了张报纸,装作自己是一只蘑菇,正拼命地往圆桌下躲
谭瑞瑞:“”
谭瑞瑞定了定神,温柔地询问:“星洲,你怎么了?”
许星洲往谭瑞瑞怀里躲,拼命装蘑菇,哽咽不已:“救、救命怎么”
谭瑞瑞:“?”
接着,许星洲绝望哀嚎:
“怎么会是这个人啊!”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两周前讲起。
第一章()
第一章
…
两周前。
三月玉兰怒放,春夜笼罩大地,白日下了场雨,风里都带着清朗水气。
那个周的周二,许星洲打听到附近新开了家很嗨的、十分有趣的酒吧。
它特别就特别在它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禁酒令时期的风格,连门口都不太好找——外头是个长得平平淡淡的副食店,还晒了些腊肉,甚至还有个守门的。装作是个副食店的样子,可里头却是个嗨得很的pub。
许星洲一听就觉得好玩,就在一个冷雨纷纷的夜里偷偷溜出了宿舍,特地喷了点香水,还拖着程雁一起——美其名曰给程雁买单,让她顺便体验一下资产阶级腐败的生活。
许星洲的人生信条就是“生而为人即是自由”,其次是“死前一定要体验一切”——她的座右铭是活到八十就要年轻到八十。
去个个把酒吧,在她这连事儿都不算。
酒吧门口‘1929’的牌子在夜风里晃晃荡荡,天刚下了场雨,石板路上映着灯红酒绿、水光山色。
那酒吧十分好玩,且富有年代感,照明还用了上世纪流行的霓虹灯管。它为了掩盖自己是个酒吧的事实甚至还在店里挂了一堆香肠,许星洲捏了下,里头灌的是货真价实的火腿。
“副食店”柜台后一扇绿漆破木门,长得犹如储藏室,十分欲盖弥彰。
程雁站在门前十分扭捏:“我不想进去”
许星洲怒道:“你就这么没有出息吗程雁,你都快二十了!连个夜店都不敢进!你是因为害怕你妈吗!”
程雁:“我妈确实很可怕好吧!”
许星洲不再听程雁扭麻花儿,硬是将比她高五公分的程雁拖进了小破门。
…
那扇破门里仿佛另一个世界,里头灯光昏暗绚丽,音乐震耳欲聋。紫蓝霓虹灯光下,年轻英俊的调酒师西装革履,捏着调酒杯一晃,将琥珀色液体倒进玻璃杯。
程雁终于摆出最后的底线:“我今晚不喝酒。”
许星洲甚是不解:“嗯?你来这里不喝酒干嘛?”
程雁说:“——万一断片了不好办。咱俩得有一个人清醒着,起码能收拾乱摊子。我觉得你是打算喝两盅的,所以只能我滴酒不沾了。”
许星洲眼睛一弯,笑了起来,快乐地道:“雁雁,你真好。”
他们所在的这个俱乐部灯光光怪陆离,她的笑容却犹如灿烂自由的火焰,令人心里咯噔一响。
程雁腹诽一句又跟我卖弄风情,陪她坐在了吧台边上。
程雁要了杯没酒精的柠茶,许星洲则捧着杯火辣的伏特加。程雁打量了一下那个酒瓶子上赫然在列的‘酒精含量48。2%’——几乎是捧着一杯红星二锅头。
程雁:“你酒量可还行?”
许星洲漫不经心地说:“那是,老子酒量可好了,去年冬天去俄罗斯冰川漂流,在船上就喝——喝这个。”
许星洲又痛饮一口,毅然道:“我一个人就能——能吹一瓶!”
程雁:“真的?”
许星洲怒道:“废话!”
那杯伏特加许星洲喝了两口,就打死都不肯再喝,毕竟那玩意实在是辣得人浑身发慌。于是许星洲把杯子往旁边推了推,靠在吧台边一个人发怔。
程雁在旁边打了个哈欠,说:“这种会所也蛮无聊的。”
许星洲盯着酒杯没说话,沉默得像一座碑。
程雁知道她有时候会滚进自己世界里呆着,就打了个哈欠,将自己那杯柠茶喝了底儿净,到外面站着吹风去了。
紫色霓虹灯光晃晃悠悠,像是碎裂的天穹。
许星洲坐在灯下,茫然地望着一个方向,不知在想什么。
片刻后,调酒师将冒着气泡的玻璃杯往许星洲面前一推。
调酒师礼貌地道:“一位先生给您点的。”
许星洲低下头看那杯饮料,是一杯柠檬和薄荷调就的莫吉托。她又顺着调酒师的眼光看过去,吧台外闹腾着、乌乌泱泱的一群人,角落里有个颇高的、男模般腿长的身影,大概就是调酒师嘴里的那个冤大头。
许星洲的视线灯红酒绿,模模糊糊,一切都犹如妖魔鬼怪——她使劲揉揉发疼的眉心,强迫自己清醒。
调酒师以一块毛巾擦拭酒瓶,说:“杯子下面有他的手机号。”
许星洲在杯子下面看到一张便笺纸,上头写了行电话号码和一个潦草汉字——她盯着那张纸看了一眼,就将它一卷,扔了。
调酒师被那串动作逗得微笑起来,对许星洲说:“祝您今晚愉快。”
许星洲嗯了一声,迷茫地看着那群红男绿女。
她根本没把那个给她点酒的人当一回事,只漫不经心地扫视全场。许星洲面孔清汤寡水,眼角却微微上扬,眼神里带着种难以言说的,因活着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