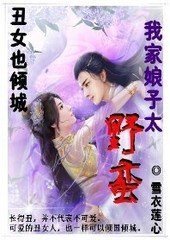余罪:我的刑侦笔记-第4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有人喊了,从车后出来。
“啊!”阴森森的环境里,骤来人声,吓得余罪一屁股坐地上了。
然后传来了女人的笑声,车灯亮了亮,两个身着警装的女人向他走来。哎呀,看清了,是周文涓和肖梦琪,肖梦琪取笑地说:“耶,就这么大胆子啊?”
“胆子再大也架不住你这么吓唬啊。”余罪气坏了。肖梦琪伸手拉他,他没理会,起身拍拍雪,奇怪地问:“文涓,你怎么在这儿?”
“总得有人守着现场吧,队里数我资历浅,总不能让师父们守吧哎,先别问我啊,这大晚上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周文涓同样疑惑地看着余罪。
“我闷出来透透气。”余罪随口道。肖梦琪上下打量着:“不是吧?我怎么觉得某些人好奇心要害死猫了?我好像知道你想干什么,可为什么不敢进去呢?”
好像是挑衅,余罪斜眼一翻回敬了句:“你猜。”
“我猜是犹豫,犹豫的原因在于,这个奇案因为大雪无法推进,而又有这么多警力,你无法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捡到大漏子。”肖梦琪笑道。
“笨死你,猜错了。”余罪直接道,“我是没见过死人,我害怕。”
肖梦琪眼睛一凸,没料到余罪这么直白。周文涓却是笑了,没想到学校的憨胆大现在却害怕,而那个晕枪的姑娘,现在已经是无畏的战士了。
“跟我来你们的来意既然相同,就一起进来吧。”周文涓道,领着两人进门了。
肖梦琪也是愁结丛生,才产生了到案发现场找找灵感的想法,没想到能遇到余罪,这样的同路实在让她对余罪高看了几眼,以前一直认为他是运气太好而已余罪犹豫了一下,在两个女人面前却是不能示弱了,迈着步,小心翼翼地跟了进去。
“咱们从楼上开始凶案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周文涓领着上楼。狭窄的楼梯,积上了雪,零乱的脚印通向楼门,刁屠户生前的日子应该不错,最起码能盖起来这幢二层小楼,在村里就应该是小富之家了。传说他也是个滚过刀尖的悍人,最后死在自己那个窝囊的女婿手上,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实在是造化弄人。
门是开的,东西原封未动,移走尸体的地方标有示意线,血迹已经凝结,黑红的块状,画着两个人形,周文涓示意着:
第390章 “羊倌”余罪再立功(5)()
“葛宝龙应该就坐在这儿喝闷酒,床上的被子是摊开的。根据邻居反映,听到了这家的吵闹声当时刁娅丽应该已经躺在床上了,两人发生了口角,然后她向葛宝龙扔了一个枕头,赤脚下了床,两人厮打在一起光脚的脚印,撕掉的毛发、指甲缝里的皮屑,都能反映出这一点来争吵中葛宝龙随手抓起酒瓶拍向妻子,老式的高粱白酒瓶子,瓶身最厚处零点六六厘米,这一击击在了刁娅丽颈后颅骨上,直接致命”
肖梦琪脸上掠过了不自然的表情,真正的现场比所有的教科书都有冲击力,即便她心理强悍,也无法揣度,多大的仇恨才能让丈夫对妻子下如此狠手,哪怕是红杏出墙。她偷瞅余罪的时候,余罪像不忍目睹一样,闭着眼睛。
“为什么照片上刁娅丽的遗容很安详?”余罪问。
问到点子上了,肖梦琪暗暗赞了个,不是心思特别敏锐的恐怕注意不到这个,她说:“是嫌疑人替妻子拢了拢头发,擦净了脸上的血迹。”
“根据这儿的痕迹,他应该跪在这儿哭过我想应该是失手,他很悔恨。”周文涓说道,突然皱了皱眉,觉得自己很矛盾。
“事后痛悔是真的,但事前痛恨也不假,不是失手,他应该恨不得把老婆亲手掐死,可真正砸死了,他又心疼了。”余罪道。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心态?”肖梦琪问。“骂老婆,打老婆,恨老婆,可又没本事换老婆,那种没能耐的男人心态。”余罪道。肖梦琪哭笑不得地看着他,这货的理论能编成教科书了,余罪却示意周文涓,“继续。”
“杀第二个人,也就是他的岳父刁福贵就不是失手,几乎是泄愤,是顺手从带的厨刀里抽了一把,直接从腰部捅了进去,然后连刺带剁,一共十六刀”周文涓道。
“他应该很愤恨,把仇恨全部发泄到这个家其他人的身上他连外套都没有穿,怒火滔天地去杀人,却还没忘记给老婆拢顺乱发这说明他对老婆还是有感情的。”余罪打断插了句。
“有感情,然后杀了她全家?”肖梦琪听不懂了。
“在很多凶杀嫌疑人的眼中,杀戮等同于拯救,或者也是一种复仇刁娅丽生前行为就不检点,婚后这一家过于强势,处处欺负窝囊女婿,不把过错归咎到他们身上都不可能。”余罪道。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看了看零乱的床铺。扔在椅背上的外套,过年的新衣,并不昂贵的一件男羽绒服,口袋里只有几百块钱,和一部用了几年贴了几处透明胶带的手机。这个葛宝龙,是只穿着件线衣跑的,上千警力二十四个小时都没找到人,想想都让余罪佩服了,人在绝境中迸发出来的力量还真不可小觑啊。
慢慢地下楼,周文涓解释了几处地方。岳母披着衣服死在床上,小外孙被攮了两刀,听到声音奔进来的二女婿,被一刀划开了颈动脉,往院门外奔着的小姨子慌乱中根本没有打开门,被他追上去从颈后也是一刀毙命。因为这几刀相当利索,专案组甚至怀疑他有过解剖类的知识背景。
“不是解剖,这是小刀手的动作。”余罪直接反驳了肖梦琪的解释。
“小刀手?他的履历里没有啊。”肖梦琪没懂这个新名词。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在履历中查到,他在后厨干了快十年了,根本就是从学徒工开始的,洗碗、配菜、红案,最后到能凑合掌勺其中红案就有一项是把块肉分开,肥、精、瘦、排骨、五花要分清,干这活利索的就叫小刀手,握刀的姿势都是这样类似于警校的匕首攻防,这样,方便攮、削、剁”余罪比画着一个奇怪的姿势。
这个虽然无从证明,但依然让肖梦琪暗暗心惊,余罪却仍漫不经心似的说着,他不时地看看院子里、屋檐下那六具裹着被子的尸身,似乎想试着看一眼,却仍然越不过自己的心理障碍。
周文涓笑了,说道:“我觉得你不应该害怕啊。”
“就像你晕枪,有心理障碍你当时是怎么样跨过这个障碍的?”余罪问。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平等的,那就是我们都会死,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和眼光去看,就没有那么恐惧了我们当警察的不相信鬼魂,就算有鬼魂,他们也应该会保佑为他们申冤的警察跟我来。”周文涓道,伸着手,拉着余罪。
昏黄的院灯下,周文涓平静的表情,像透着一种圣洁的力量,让余罪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轻轻地站到了檐前。她选了那具最小的尸身,俯下身,轻轻地揭开了白布。
孩子,像睡熟了一样,只不过面色已经铁青,身体已经僵硬。他身边扔着几枚花炮,周文涓捡起了一个,慢慢地放在余罪的手心,她灵动的大眼看着余罪,轻声道:“过了这个年刚五岁,死的时候手里还攒着花炮,口袋里也有,他一定等着第二天一起和小伙伴玩这一刀攮得很准,直接捅在心脏上,一点施救的机会都没留下才五岁,不管有多大仇恨,也不能杀这么大的孩子啊”
那是一种悲怆而无奈的表情,那是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六个冰冷的、没有生命迹象的人,就这样静静地躺着,等着进火化炉灰飞烟灭,他们静静地等待,那尚能伸张的、在灰飞烟灭之前的最后正义!
余罪没有说话,他心里泛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悲恸,一家三代六口惨死刀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发指?
他抬手看看捻着的这个花炮,慢慢地俯下身,伸手轻轻触了下那个小孩冰凉的额头又掀开了第二具尸身的覆被,应该是他妈妈,姣好的面容,已经惨白得没有血色掀开了父亲的覆被,割开了喉咙,半睁的眼睛,是一种死不瞑目的表情。两位老人,死前的惊惧还凝结着,像试图告诉后来者什么。
余罪凝视着,意外没有恶心和想要呕吐的感觉,尽管惨状很令人作呕;更意外的是,他也没有很恐惧的感觉,尽管很让人觉得恐惧。他静静地看着,像在思考着什么,像在冥冥中寻找着什么。
周文涓要说话时,被肖梦琪拦住了,轻轻地退后了几步,她知道很多顿悟总会出现在不经意的时候,比如,此时。
蓦地,余罪触电似的站起来,他喃喃着,不知在说什么,奔上了楼。两人还没明白的时候,他又奔下来了,奔进了堂屋,似乎做了几个剧烈的动作旋即又奔了出来,直奔向大门口,做了一个背后袭击刺人的动作一下子仿佛他是在作案似的,在大口喘着气,急促地说着:“挥这几刀,只需要三分钟他是在酒后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昨晚邻居听到了大声号叫他杀了人之后,第一时间应该是对,很疯狂,又是痛快又是后悔很恨老丈人一家,杀老两口很痛快,连捅十几刀;他自己没小孩,所以杀小孩也不手软;二女婿过得比他好,他也很嫉妒,所以下手很重,一刀豁开了喉可他舍不得杀老婆,那是失手;他又不得不杀小姨子,他其实并不想杀她,所以那一刀只刺向她的颈部,而没有更暴虐的手段”
余罪两眼炯炯有神,面目可怖,手里紧紧握着刀,惊得周文涓和肖梦琪不敢上前。
“该杀的,不该杀的,都他妈杀了他疯狂了,又痛快淋漓,又极度痛悔,那些心理矛盾让他疯狂了,所以他拼命地吼着、喊着然后跑!”
说做就做,余罪仰头吼了声,迈开大步就跑,顷刻就不见人影了。
“余罪,余罪你怎么了?”周文涓吓了一跳。
“没事,你看着这儿他在模拟当时的凶案现场,肯定是跑到第二个发现点了,我去吧,这儿得看着。”肖梦琪说着,顾不上周文涓的反对,朝着余罪跑去的方向,飞快地追上去了。
雪地、暗巷、昏黄的灯光,仿佛都带着血腥的气息从身侧掠过。跑了几百米后,余罪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凝视过几具尸身带来的心理阴影似乎开始发作了,他像作了案一样,拼命地在加快步伐快跑,跑得更快,根本没有听到背后肖梦琪的喊声。
这个怪异的行径把村口驻守的警力都惊动了,肖梦琪赶紧联系专案组,让那些警力别去露面,等她气喘吁吁追上余罪时,果真证实了她的想法。余罪正扶着电杆,蹲在那儿喘息,这个发现嫌疑人血迹的地方,还拉着警戒线。
这样做有用吗?
肖梦琪看着喘息的余罪,很多时候她都没法理解,这个从基层来的小警究竟心里在想什么、到底想干什么,这一次也是。现在是在找凶手的下落,而不是找凶手是谁,否则早有更多的侦破高手要通过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描摹凶手了。
“你找到了什么?”肖梦琪问。
“我在找他逃跑的方向。”余罪起身,喘过这口气了。几个方向都是黑的,远处一片通明的地方,那是五原市,他跑了几步,停住了,自言自语道,“不应该是市区,他已经透支了胆量,最害怕的就是见到人”
回头却茫然了,黑漆漆的北方,正是上千警力撒网的地方,这个方向,应该不会错。
“你找到方向了。”肖梦琪问。
“找到了,本能。”余罪道。
“本能?”肖梦琪没听懂。
“对,本能。没有预谋,没有直接动机,甚至连侵害对象都没有选择,这是种种仇怨积郁引发的血案,很简单的一桩案。”余罪道。
“你还是没有说逃走的方向。”肖梦琪问。她觉得余罪似乎知道方向,那是一种盲从。
“本能就是方向也可以说没有方向,一个年三十忙了一天,晚上吃饭又喝了酒,杀了人跑的时候连外套都没有带,就凭着一口气跑你觉得他能跑多远?我认为啊,二十公里范围之内,他仍然龟缩在哪个角落里。”余罪判断道。
“这个就有待外勤证实了,我是奇怪”肖梦琪欲言又止。
“奇怪什么?”余罪回头时,看到了夜色中若隐若现的白皙的脸,不过这个时候实在起不了调戏的心情。
“你这么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肖梦琪道。
“就像坐在专案组里,连一线都没到过,一样没什么意义。”余罪头也不回地说,向前走着,走了几步蓦地车灯闪耀过来,他捂着眼睛,一下子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有可能爬货车走吗?
还没等思考,车戛然而止,车窗里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