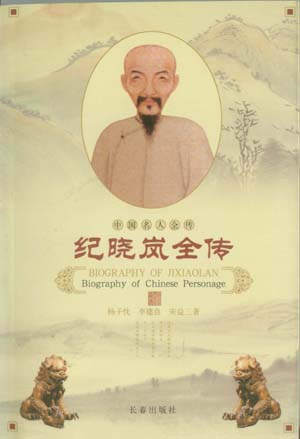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裾,位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
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这首诗写得何等凄怨,难怪纪晓岚爱不释手了。由此也可见纪晓岚的文人纯真气息,以及对人间挚爱真情的歌颂与向往。
本来,在宋明理学的体系中,只有“天理”才是惟一的、实在的,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则被绝对加以排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乃是中国传统道德可怕的变态和扭曲。
但是,压抑从来不是万能的。理学家们消灭欲念的强力主张,自晚明以来便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击。纪晓岚在写作《四库全书》提要时,也站在这一阵线之中向理学出击。他叙述了如下两则抉择于“欲”与“理”之间的故事,它们的主人公分别是北宋陈烈与南宋胡铨。
陈烈一次出席宴饮,东道主请来官妓于席间助兴,“烈闻妓唱歌,才一发声,即越墙攀树遁去,讲学家以为美谈。”对于理学道德准则来说,陈烈确是严守名教大防、坚守纯正“天理”的典范。
胡铨是南宋名臣。绍兴年间,秦桧主和,金使南下诏谕江南,他上疏请杀秦桧和使臣王伦,被谪吉阳军(今广东崖县)十年,直到孝宗即位,才被起用。在从贬地北归的途中,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曰:“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所谓“梨颊生微涡”者,即“侍妓黎倩也”。胡铨之诗后为朱熹所见,于是朱文公题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见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在这位理学大师看来,胡铨虽气骨铮铮,却因把持不住“方寸之间”的自我,从而在一念之差中堕入险恶的‘人欲”陷阱。系于人生全副身心和性命之上的伦理道德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无情坠落,胡铨由此而被判定,“自误平生”,此番情形正如乾隆帝所声言的:“天理与人欲,只争一线多。”“出此入乎彼”,其间绝无调和余地。纪晓岚却不然,他针对朱子对胡铨的斥责而发出这样的议论:
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误平生,其操之为已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
在这里,纪晓岚以一种现实的富于人情的态度来解说胡铨“归见梨涡却有情”的“失误”,其批判锋芒所及则是理学扼杀人的情感欲望的禁欲主义以及道德神圣、道德至上的泛道德主义。其立场和旨趣大不同于宋明理学家。
纪晓岚所撰《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记载了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
余幼闻某公在部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来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跑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
一对情窦初开的小儿女,只因相遇而笑便在严密礼教的窒息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现实生活中,宋明理学确乎扮演了一个非常凶残、丑恶的角色。“以风化为己任”的理学家将本来契洽人情、助人向善的道德伦理,变成“忍而残杀之具”,进而“以理杀人。”表面上堂而皇之,骨子里男盗女娼的理学家还将道当作遂私欲的再好不过的器具。
与此相比,纪晓岚以礼部尚书之尊,著书立说,有的明显赞扬至爱真情,无疑是可贵的。
方圆实战:行事多风趣,令“闻者绝倒”
谈吐能直接反映出一个人是博学多识还是孤陋寡闻,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还是浅薄无知。一个不善言谈、沉默寡言的人很难引起他人注意。在社交中能侃侃而谈,用词高雅恰当,言之有物,对问题见解深刻,反应敏捷,应答自如,能够简洁、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就能表现出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风度。
然而,高雅的谈吐是无法伪装出来的。卖弄华丽的词藻,只会显得浅薄浮夸;过于咬文嚼字,又会使人觉得酸味十足。不背后议论人,讲话注意分寸,背后表扬人,多讲其优点,当面批评人,指正其缺点。
一天,纪晓岚的朋僚、《四库全书》的另一位总纂陆锡熊的母亲70大寿,家中张灯结彩,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纪晓岚与几个同僚前往祝贺,陆锡熊见是纪晓岚等人,特别客气。纪晓岚妙语惊人,才气不凡,待宾客到齐后,特请纪晓岚撰写祝辞。
按当时的习惯,为高官的老寿星撰写祝辞的人,不是官高位显,就是饮誉文坛。这时的纪晓岚仅仅30多岁,官职也只是个编修,主人陆锡熊请他写祝辞,这已是特别看得起他。纪晓岚却丝毫没有推辞,连说:“谨遵台命。”
纪晓岚提起笔,望了一眼在座的宾客,写下第一句话:
这个婆娘不是人,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与他同来的朋友看到纪晓岚的举动,知道他要开玩笑,但在这喜庆而又严肃的场合,如此出言,大家都没有料到。陆锡熊更是惊得手足无措,坐在堂上的老夫人,满是皱纹的脸上结了一层寒霜,那怒火像正要发作。这时纪晓岚不慌不忙写下了第二句:
九天仙女下凡尘。
笔调轻轻一转,语意全变。大家哄然一声,笑了起来,正要发作的老夫人也转怒为喜,陆锡熊乐得直拍手。正在大家开怀的时候,纪晓岚写下第三句:
生个儿子去做贼,
这下又把大家弄糊涂了,不知纪晓岚到底要说什么,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老夫人和陆锡熊眼睛直呆呆地望着纪晓岚,似乎要看透他。纪晓岚也不说话,直待大家胡乱猜测的时候,他才写下了第四句:
偷得蟠桃寿母亲。
这下大家方才明白,于是众宾客都欢呼起来:“高才,高才!”
老夫人和陆锡熊也满意地笑了。
其实,纪晓岚的这四句话,并非什么上乘之作,它的意义太单薄。纪晓岚这样作,只是显示他的幽默和机智,以博得大家一笑而已。
历史上不少文人也有过类似的戏谑。据《葵轩琐记》记载,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当住在对面的富翁母亲70寿诞,向他求诗时,也曾写下这样四句话:
对门老妇不是人,
好似南山观世音。
两个儿子都是贼,
偷得蟠桃献母亲。
唐伯虎恃才傲物,潇洒风流,开这样的玩笑是可能的。纪晓岚的四句,与唐伯虎的四句话如出一辙,但第二句不同,意义更为合理。纪晓岚广读诗书,不管他是借用还是独创,都说明他机敏灵活。
流传下来的一则他为人写春联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他的博学。
春节到来,人们都知道纪翰林善于题联,一时间上门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使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不过他也真有办法,无论谁来,上联都用唐代高适的一句诗:圣代即今多雨露;下联也集唐诗中的句子做对,而且大多切合请托者的身分时况,很受请托者的喜爱。
一开始,他这种办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可是一连几天过去,手不停挥地打发走了上百个请托者,上联总是那句“圣代即今多雨露”,下联却绝无重复的句子,翰林院学士们觉得十分惊奇,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河间才子纪晓岚,究竟会背多少首唐诗?
恰好,有位前任侍郎,不久前被贬去官职,受命到翰林院行走。他看纪晓岚给人的春联,无一例外地用这句上联来颂扬皇帝圣明有道,对臣民宽厚仁慈,普施恩泽,便有意要为难他一下,也来向纪晓岚求写春联。
纪晓岚见侍郎也来求联,很是高兴,口中寒暄着,随手提笔写出了上联:圣代即今多雨露,那位侍郎看了,微微笑道:“敝人新由卿贰贬到翰林院行走。”
纪晓岚一听,忍不住嘴角一翘,心里话,这回有点不好办了,看来侍郎是有意开我的玩笑!这侍郎所说的卿贰,就是侍郎的别称,因为六部尚书为正卿,各部侍郎的地位仅次于尚书,所以又称做卿贰。这位侍郎被贬回翰林院行走,只是来这里协助工作,并不是专职官员,一下子就是连降了数级,跟“圣代即今多雨露”一句,完全是两码事,但上联已经写出来,又不好不用啊。
纪晓岚抬头看看身边的同僚,他们眼睛含着笑意,分明是要看看他这次如何写就下联。纪晓岚略一思索,有啦!抬头向侍郎笑道:“大人来得正好,有一唐人诗句,只有给您用才最合适!”
说完笑盈盈地提起笔来。同僚赶紧凑到他身边观看,只见他写道:“谪居犹得住蓬莱。”
这句下联,用的是唐代元稹的诗句,纪晓岚把翰林院比作蓬莱仙境,给侍郎用上了这样一句,说他虽然被贬,却因祸得福,到底还是归于“圣代即今多雨露”啊!
侍郎看了,佩服得直点头。同僚们也称赞起来,说他真不愧为才子。
令“闻者绝倒”这样的事,纪晓岚似乎终生乐此不疲,亦颇有一些得意。在关于他的传说中有多少“令人绝倒”,谁也说不清。他的幽默总是来得那么突兀而又自然而然,他很天真地捉弄眼前的人物,有时也自我解嘲。
方圆立身之道三: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
——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是非分得太清,泾渭辨得太明。纪晓岚善于把握认真的“度”,善于根据环境和情势,判断并决定自己的行动。认真与否,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就是能否让自己处于主动。常有书呆子,不顾客观情势,从本本出发,执拗到底,过分认真,致使自己越来越被动。
方圆实战:认不得“真”的时代
孔子昔年困于陈蔡,饿得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观光店,教弟子山去讨碗饭吃。掌柜的说:“我写一个字,你若认识,我就免费招待。”仲由说:“我是圣人门徒,不要说一个字,就是十个字,都包下啦。”掌柜的写了一个“真”字,仲由说:“这连三岁娃儿都知道,一个‘真’字罢啦。”掌柜的说:“明明白痴,还说大话,小子们,给我乱棒打出。”仲由狼狈而逃,禀告一切,孔丘说:“无怪你会挨揍,等我前去亮相。”掌柜的仍写—个“真”字,孔丘说:“这是‘直八’呀。”掌柜的大惊道:“名不虚传,你的学问果然大得可怕。”酒醉饭饱之后,仲由悄悄问:“老头,你可把我搞糊涂啦,明明是‘真’字,怎么变成‘直八’?”孔丘叹道:“你懂个啥,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在嘉庆七年,纪晓岚这位79岁的老臣,再次被谕命为会试正考官。正考官共有两名,另一名正考官是左都御史熊枚,副考官是内阁学士玉麟、戴均元。
在此之前,纪晓岚曾两次充任会试正考官,一次充任武科会试正考官。每次都谨慎从事,严于防范,没有出什么差错,录取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因而就担任正考官来说,他已是轻车熟路。可是事有偶然,没想到这次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次,纪晓岚去北京城的天桥听书,忽听得旁边有二人在低语。他回眸一看,见是两个举子模样的人。其中的一个说道:“仁兄,我有一诗想背诵于你,看意下如何?”另一个道:“这好端端的说书,还听得那诗有何用场!”那人道:“我叫你听,自是有听的妙处。”另一人道:“那么,你就说说看。”偏巧,这时说书已到了一段,屋内的声音也少了些,话也容易听得真了。这会儿,只听那人背诵道:
禁御花盈百,迟迟送漏声。
此中饶绚烂,遥听亦分明。
籁静敲愈响,红深望不成。
铃脆金个个,柯杂玉琤琤。
代把鸡筹报,先教蝶梦惊。
霞开林外曙,雾封竹间清。
园鼓休催羯,楼钟未吼鲸,
皇州春色满,更待转流莺。
另一人听了,叫道:
“好诗,好诗。”
那诵诗者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