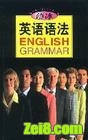国学知识大全-第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版、元椠,可观其纸墨、字体,而知当时制造及印刷的技术是。他种实物,更不待论,如钟鼎,一方面可观其铭刻,又一方面,即可观其冶铸的技术,其重要,实有过于根据其文字以考史事。中国从前科学不发达,不甚知道实物的价值,属于古物,偏重其有文字者,以致作伪者亦以此为务。(如殷墟甲骨文,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伪造者确有其人,且有姓名及每伪造一片的价格)今后实不可不翻然改图。(三)为法、俗。法、俗二字,乃历史上四裔传中所用的。这两个字实在用得很好。法系指某一社会中有强行之力的事情,俗则大家自然能率循不越之事,所以这两个字,可以包括法、令和风俗、习惯;而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在古代,亦皆包括于俗之中;所以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几于能包括一个社会的一切情形。(1)法、俗的变迁,有的很迟,所以古代的法、俗,还存于现在,这固不啻目击的历史。(2)又其变迁,大抵有一定的途径,所以业经变迁之后,考察现在的情形,仍可推想已往的情形。(3)社会进化的阶段,亦往往相类。所以观察这一群人现在的情形,可以推测别一种人前代的情形。社会学之所以有裨于史学,其根源实在于此。此种材料,有的即在地面上,有的则须掘地以求之。大概时代愈远,则其有待于发掘者愈多。历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愈远愈好,所以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
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不论哪一种学问,都是逐渐进步的,史学将来的进步未知如何,这或者连它所要走的方向,亦非现在所能预知。若回顾既往,则其进步,有历历可指的。我现在把它分做几个阶段,这可以看出史学发达的情形,而史学研究的方法,亦即因此而可知。
中国史学的进化,大略可以分做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把司马谈、迁父子做代表。他父子俩才有意网罗一切史材,做成一部当时的世界通史。(所谓世界,总系以当时的人所知道的为界限,在近世世界大通以前,西洋人的所谓世界,亦系如此。所以史记实在是当时的世界史,而不是本国史。不但史记,即中国历代的正史,称为其时的世界史,亦无不可,因为它已经把它这时代所知道的外国,一概包括在内了)在他以前,固非没有知道看重历史的人,所以有许多材料,流传下来,还有一部无名氏所作的世本,史学家称它为史记的前身。(世本亦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又有谱,即表的前身;有居篇,记帝王都邑;有作篇,记一切事物创作之原;为书之所本。所以洪饴孙作史表,把它列在诸史之前)然总还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视历史的观念,总还觉得未臻于圆满,到他父子俩,就大不相同了。所以他父子俩,可说是前此重视史学的思想的结晶,亦可说是后世编纂历史的事业的开山。这种精神,这种事业,可以说是承先启后。后来许多史学家的著作,都是从此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
第二,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刘知几,才于此加以检讨。据唐书的刘知几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几只是一个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见史通之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六家系刘知几认为正史的;二体则六家之中,刘氏谓其可行于后世的,所以其古今正史篇所述,亦以此二体为限;杂述则其所认为非正史的)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
第三,刘知几的史通,不过遵守前人的范围,对其作法加以研究而已。所谓范围,就是何种材料,当为史家之所取,何种材料可以置诸不问,刘知几和他以前的人,意见实无大异同,即可说他史学上根本的意见,和他以前的人,亦无大异同。到宋朝的郑樵,便又不同了。他反对断代史而主张通史,已经是史法上的一个大变。这还可说是史记的体例本来如此,而郑樵从而恢复之。其尤为重要的,则他觉得前人所搜集者,不足于用,而要于其外另增门类。他在通志的总序中,表示这种意见,而其所作的二十略,门类和内容亦确有出于前人之外的,(据总序自述: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十五略,都出自胸臆,不袭汉、唐诸儒,此就内容而言。若以门类而论,则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乃全为郑氏所新立)这可说是史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了。
第86章 历史研究法(3)()
第四,以从前的人所搜辑的范围为太狭,而要扩充于其外;这种见解,从史学知识当求其完全、广博而论,是无人能加以反对的,但是仅此门类,史料日日堆积,业已不胜其烦,不可遍览了,何况再要扩充于其外呢?如此,岂不将使历史成为不可观览之物么?然而要遏止这个趋势,把材料加以删除,却又不可。这事如何是好呢?于此,中国的大史学家章学诚出来,乃想得一个适当处置之法。他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为两物。储蓄史材,务求其详备;而作史则要提要钩玄,使学者可读。因史料的详备,史家著述才有确实的根据,和前此仅据残缺的材料的不同。亦惟史材完备保存,读者对于作者之书有所不足,乃可以根据史材而重作。(一人的见解,总不能包括无遗,所以每一种历史,本该有若干人的著作并行)其大体完善,而或有错误、阙略之处,亦可根据史材,加以订补。因其如此,所以作史者可以放大胆,实行其提要钩玄,而不必有所顾虑。从前并史料和作成的史籍为一谈,一部书修成后,其所根据的材料,即多归于散佚。(此亦系为物力所限,今后印刷术发达,纸墨价格低廉,此等状况可望渐变)作史的人觉其可惜,未免过而存之,往往弄得首尾衡决,不成体例;而过求谨严,多所刊落,确亦未免可惜。知章氏之说,就可以免于此弊了。章氏此种见解,实可谓为史学上一大发明。其他精辟的议论还多,然其价值,都在这一发明之下。
第五,史材务求详备,作史则要提要钩玄。这在现今的史学家,立说亦不过如此。然则章学诚的意见,和现在的史学家有何区别呢?的确,章学诚的意见,和现在的史学家是无甚异同的。他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现代史学的进步,可说所受的都是别种科学之赐。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而这个总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会明白的。要求各方面都明白,则非各种科学发达不可。所以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专门史,严格论起来,是要归入各该科学范围之内,而不能算入史学范围内的。所以说史学的发达,是受各种科学之赐。然则各种专门史发达达于极点,普通史不要给它分割完了么?不。说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是一件事;合各种现象,以说明社会的总相,又是一件事,两者是不可偏废的。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社会的总相,是专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强作说明,必至于鲁莽灭裂而后已。所以各种科学发达,各种专门史日出不穷,普通史,即严格的完全属于史学范围内的历史,只有相得而益彰,决不至于无立足之地。史材要求详备,作史则要提要钩玄,是了,然史材要求详备,不过是求作史根据的确实;而各项史材,非有专门家加以一番研究,为之说明,是不能信为确实的。详备固然是确实的一个条件,然非即可该确实之全,所以非有各种科学以资辅助,史学根据的确实,亦即其基础的坚固,总还嫌其美中不足;而其所谓提要钩玄的方法,亦不会有一客观的标准,倘使各率其意而为之,又不免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了。所以章学诚高尚的理想,必须靠现代科学的辅助,才能够达到。所以说:他和现代的新史学,只差了一步,而这一步,却不是他所能达到的。这不是他思力的不足,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如此。如以思力而论,章氏在古今中外的史学界中,也可算得第一流了。
思想的进步,是因乎时代的。第一阶段,只觉得史料散佚得可惜,所以其所注意的在搜辑、编纂。第二阶段,渐渐感觉到搜辑、编纂如何才算适当的问题,所以其所注重的在史法。第三阶段,则因知识的进步,感觉到史学范围的太狭,而要求扩充,这可说是反映着学术思想的进步。第四阶段,因史籍堆积甚多,再图扩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胀破裂,而割弃则又不可而起,虽未说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情和精力、时间,既不能兼容并包;而各个门类,以及每一门类中的各种材料,又都不容割爱,则势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种专门史亦必渐次兴起。不过现在既和外国的学术思想接触,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罢了。所以学问的进化,自有一个必然的趋势,而现在所谓新史学,即作为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阶段,亦无不可。
史学和文学,系属两事。文学系空想的,主于感情;史学系事实的,主于理智。所以在人类思想未甚进步,主客观的分别不甚严密的时代,史学和文学的关系,总是很密切的,到客观观念渐次明了时,情形就不同了。天下的人,有文学趣味的多,而懂得科学方法的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的书来,是欢迎主观的叙述的。喜欢读稗史而不喜欢读正史;在正史中,则喜欢四史等而不喜欢宋以后的历史,和其看现在的报纸,喜欢小报而不喜欢大报,正是同一理由。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作者只叙述事实的外形,而其内容如何,则一任读者的推测,不再把自己的意思夹杂进去了,这亦是史学的一个进步。
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从前的历史,不适于现代人之用,这句话,是人人会说的,然则从前的历史,其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这一个问题来,我们所回答的,第一句话,便是偏重于政治。“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一类的话,在今日,几乎成为口头禅了。这些话,或者言之太过,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读某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对于这种生活情形,知道一个大概,这是无待于言的了。我们读旧日的历史,所知道的却是些什么呢?我也承认,读旧日的历史,于这一类的情形,并非全无所得。然而读各正史中的舆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员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车辆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却并没有记载。我们读齐书的本纪,知道齐明帝很有俭德。当时大官所进的御膳,有一种唤作裹蒸,明帝把它画为十字形,分成四片,说:我吃不了这些,其余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鉴注说,在他这时候,还有裹蒸这种食物。是把糖和糯米、松子、胡桃仁,合着香药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来蒸熟。只有两个指头大,用不着画成四片。见齐明帝建武三年。裹蒸的大小,无关紧要,可以不必去管它。看它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约就是现在嘉、湖细点中胡桃糕的前身,吾乡呼为玉带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松子、胡桃仁制成的,不过没有香药而已。因近代香药输入,不如宋、元时代的多而美。南北朝时,还没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间,蔗糖也远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说的裹蒸,用何种糖不可知,齐明帝所吃的裹蒸,则所用的一定是米、麦糖,米、麦糖所制的点心,不甚宜于冷食,所以大官于日食时进之,等于现在席面上的点心;后来改用蔗糖,就变成现在的胡桃糕,作为闲食之用了。又据南史后妃传:齐武帝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荐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荐给宣皇帝的,有起面饼一种。胡三省通鉴注说:“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饼浮软,以卷肉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