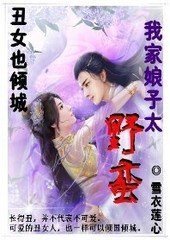凤天歌,倾城第一医后-第9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姜一闲无端地觉得这声音熟悉,细细一想,能够在闻人御身边服侍的大公公,非王富贵莫属。
这么晚了,闻人御还在里头看奏折?他是不是不要命了?
姜一闲壮着胆子朝前面走去,希望王富贵认得自己,希望那些公公侍婢们不要惊动别人。
王富贵看到姜一闲,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把她认成刺客,而是自顾自沉浸在悲伤里,时不时用哽咽的声音对着御书房里头的人哀求哭喊。姜一闲忽然心头不是个滋味,天地间仿佛都寂静了,她现在踩着的这片地上,或许一个人都没有吧。
她蹲下去,拍拍王富贵的肩膀,摆出一副很懂的样子,道:“王公公?陛下又不睡觉了?”
王富贵掩面哀嚎,“陛下生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又不愿意睡觉,身体怎么撑得住啊”
姜一闲使劲扯出一个笑容,“国务繁忙,陛下处理国事到深夜也是无可奈何。你们做下人的,不给陛下端点儿吃的去?在屋外跪着是为何?”
“陛下陛下与其让陛下用膳,公公我还不如把那些食物倒了!”王富贵忽然发狠,眼神一凛,几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又低头哀哀戚戚,“哪儿是人吃的东西”
姜一闲却是越发地听不懂了,她拉拉王富贵的衣袖,想把他的神智扯到自己这边来。“王公公,陛下吃的不都是山珍海味,怎么就不是人吃的东西了?还是说,天子贵为真龙”
王富贵有些烦,眼前这小妮子怎么竟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这些事情,宫中不都传遍了吗?她一身侍女装束,此刻不和大伙儿一起跪着,还对他问这问那。王富贵生气一指,朝着边上一个小侍女手中端着的盘子。“你去拿点碎碎吃了试试。”
一盘做得十分精致的点心,颜色红红绿绿,霎是好看。
姜一闲没有犹豫,拿起一块往口里送。咸苦的味道直冲大脑,这是什么点心?为什么要放盐?这滋味仿佛比喝了海水还要难受。她激动跳脚,直朝着花丛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呸呸呸!宫里的厨子是怎么做事的?拿着天子的工钱,做出这样的点心?这是人吃的?!”
姜一闲怒不可遏,声音也不由得大了一些。
王富贵似是被姜一闲戳中了痛处,愁眉苦脸,“哎!可不是,造孽啊!”
姜一闲忽然把自己的脸凑近王富贵,试探性地问道:“王公公,您觉不觉得,我像一个人?”
王富贵看了她半晌,不自觉地点头,“是像啊,是像”就在姜一闲激动自乐的时候,王富贵朝她泼了一头冷水,“像又怎样?公公我花了大价钱给陛下在大江南北寻跟那画中女子有几分相似之人,还不是一个一个被陛下推拒,险些给公公我降罪”
姜一闲腹诽,自己才不是像那画中人呢。
“不过,你是谁?!”王富贵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奴婢聊了这么久?
姜一闲讪讪扯出一个并不开心的笑容,道:“我是恪己殿的杂事丫头。陛下多日不去恪己殿,我便来看看,多有得罪,还请公公原谅。”
王富贵重重一叹,“恪己殿,恪己殿要是陛下自己愿意去那恪己殿就好喽”
“公公何出此言?”
“陛下在御书房,从不睡觉,多少天了,他就没合过眼!陛下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了,还不爱惜自己,咱们这些做下人的,干着急也没有用啊自那光孝皇后去了,陛下失去了眼睛,失去了鼻子,失去了嘴巴,失去了心神,这可怎么办啊!人死不能复生,天罗大仙也救不了陛下!”王富贵又是一番感慨,“公公我也尽职尽责了,一劝陛下,咱们都要跟着受罪,一跪就是一晚上呐”
姜一闲眼珠一转,凑到王富贵的耳根前,“公公,如果我闯进御书房,会怎样?”
王富贵不假思索,“死。”
“既然如此,公公,冒犯了!还请公公送我一程!”
王富贵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只听得姜一闲尖叫一声,月色下的她羞红了脸,指着王富贵的鼻子道:“你你竟然你竟然调戏我!”
姜一闲瞪大了眼,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仿佛是被毒蛇给咬了。
周围的公公侍婢皆是一副不明白的模样,王富贵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太监怎么会调戏女人?再说了这姑娘要色没色,要钱没钱,谁会调戏她?大伙儿不由得盯着姜一闲笑。
“笑什么笑?你们这些公公,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的坏事还少了?宫外不知道养了多少儿子呢!奴婢只是给公公汇报些日常事宜,却被公公那般羞辱”说至此处,姜一闲又气又羞,两只眼水汪汪地似是要哭出来。
王富贵的脸有些挂不住了,他想抽回自己的手,却被姜一闲死死反扣住。
这下可落实了他色胆包天的罪名,一个净身过的男人,牵着人家小姑娘的手不肯放了
“奴婢要见皇上,要皇上为奴婢主持公道!”说着,姜一闲拉着王富贵就往御书房里冲。
23
第一百五十章 有什么病()
王富贵恨不能把这个疯丫头打成马蜂窝,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在一个不存在什么秘密的皇宫,怕是明天,王富贵色心不改的谣言就能飞到各个角落,变幻出各种版本
闻人御熟悉的脸多了几分憔悴,然而他的表情依旧像一尊万年冰山一般,寒气凛得窒息。
他的手中握着一方绢帕,见到姜一闲和王富贵一个怒气冲冲一个愁容满面地闯进来,他戾气逼人,危险地眯了眯眼,“朕有说让你们进来吗?”
王富贵趁着姜一闲不注意,甩脱她的手跪了下去,“陛下要为奴才做主啊!”
姜一闲瞅了王富贵一眼,泫然欲泣,反驳道,“陛下,这色胆包天的公公欺辱奴婢”
她装作哭泣的样子,偷偷放出视线瞄了瞄闻人御手中的帕子,看到了半块图案。那图案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因为就出自于她之手。那是她,在闻人御出征之前,送给他的礼物。
原来他一直有好好保存。姜一闲不知心中是何种滋味,正当她出神之际,头顶传来一道阴冷的嗓音,“我大凛国宫中什么时候容一介婢女倨傲无礼了?”
王富贵心中暗暗自喜,想必这不识好歹的丫头要被闻人御降罪。还好自己紧急时刻也不忘宫中的规矩,不然,陛下可能要追究他“欺辱奴婢”之事了。
姜一闲恍然醒悟,噗通一声跪了下去,她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也顾不得膝盖上的痛了。
闻人御不知为何,心尖尖跟着颤了一下。这个场景,似乎有些熟悉,眼前奴婢的长相,自己也有些熟悉可是这些人都是谁?他为什么想不起来?
忽然头疼欲裂闻人御扶着桌子,一手狠狠地揉着眉心。
“闻人御,你怎么了?”姜一闲顾不得君臣之礼,即使他没有允许自己免礼,她已经扑到他身前去察看他的不适。
姜一闲一时间忘了自己的半吊子医术,趁着闻人御没什么力气反抗,她抓住他的手腕,摸索到脉搏的位置。那里的跳动很快,闻人御怕是身体状况不太好。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肩上陡然多了一份巨大的力量。闻人御失去了意识。
“王公公,你还愣着干嘛呀!快差人把陛下弄到床榻上去!”姜一闲急急唤着。
王富贵幡然醒悟,都什么时候了,自己还在等陛下发话平身?
恪己殿外候着三五个御医,姜一闲无法想象,自己某一天也能是独当一面之人?王富贵许是第一回见到皇帝昏厥受到了惊吓,甚至忘了处理事情的正确流程。是姜一闲提醒王富贵宣几个御医来给闻人御治病,也是她把闻人御弄到榻上,解了他几件厚重的外衣。
闻人御双唇发白,十分虚弱。她是第一回真真正正地感受到闻人御清瘦了许多,仿佛只是一层薄薄的肉包裹了他的骨架,那层层外衣之下,是他脆弱得如同空壳一般的心。
她不自觉地揪心,替闻人御掖好被子,姜一闲扭头朝外面喊着,“御医大人们请进。”
前来替闻人御看病的御医里,五个竟有四个她不认识。除了一个张御医,是她曾经一起同床过的老人精,其余四个,怕是已经被闻人御换成了自己的势力了吧。
“唉,老毛病了。”张御医摇摇头。
其他几个御医也接连叹气,“不是咱们做臣子的不医陛下,而是陛下的病因根本不在肌肤层理啊”
姜一闲心头一个咯噔,她不知道是不是如同自己所想的那样。但愿不是吧,她知道,心病比身病难医不止一万倍,何况,闻人御的心病还没有那么简单。
或许,他的心病出于一个“死去”的人?
一个稍微年轻的御医拿出纸笔,伏在书案上书写,语气中满是无奈和动容,“给陛下开一张方子吧,但是他愿不愿意喝药,这就不是臣子们能够左右的事情了。”
王富贵在一旁干着急,“是不是你们每次给陛下开的药方太苦了?”
姜一闲横了王富贵一眼,“陛下会是怕苦药之人?他上战场都不怕,中刀中枪都不怕,会怕喝药?陛下他不愿意喝罢了。王公公,你到底是怎么浑水摸鱼混到一品公公职位的?”
王富贵被姜一闲说得一张脸青一阵红一阵。他忽然心虚地觉得这女子让他害怕。
御医把药方拿给王富贵让其差人熬药,王富贵似是如释重负一般,拿着那张药方飞快地跑出恪己殿,连平时走路扭动的腰肢都变得正常了。
屋中剩下的五个御医,纷纷对姜一闲的身份感到好奇。张御医围着她转悠了两圈,眼神死死地盯着姜一闲的脸,然后沉吟道,“这是新伤,受伤之日离今日不过二十天。”
姜一闲缓缓点头。原来他盯了自己看这么久,也没有认出来自己是谁
“只是可惜,伤口尚未愈合的时候没有好好用药,即使伤口消退,以后也难免有疤。”
姜一闲淡淡一笑,“多谢张御医关心,我对外表并不在意。”
那位年轻的御医爽朗一笑,“我竟是第一回听得女子说,对自己的外表不在意。”
姜一闲垂头,不愿继续与他们多交流了。
几位离开恪己殿,张御医在恪己殿的门口顿住脚步,回头沉静了几秒。
闻人御比她离开他之时变了很多,整个人虚白虚白,眼角深凹,好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他清瘦了许多,吃的东西还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她不明白当皇帝到底每日有多少的国事需要处理,也不明白明明天下太平,哪儿每天来那么多屁国事丢给闻人御。下头的御史,巡抚,那些一品二品三品的大臣都是吃软饭吗?万事都要交给闻人御过目?
王富贵没过一会儿回来了,他的身后是四个丫鬟,每个丫鬟手里,都端着盛放药碗的盘子。
“御医开了四碗药的方子?”姜一闲皱了皱眉头,这是拿药当饭吃?
王富贵一脸的担忧,脸也不转地对姜一闲道,“不是,本公公拿四碗药,自有本公公的道理。嗨算了,也没必要与你置气。陛下不愿喝药的时候,就是拿来十碗,也不够陛下砸的。”
姜一闲一脸惨白,语气中不免带了一些负面情绪,“皇上病了多久了?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吗,还没日没夜地处理国事。你们是怎么劝的,莫非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是姜一闲第一回见到闻人御生病,往常都是他的后宫佳丽需要自己,而不是他。闻人御明明昏迷过去了,却乌唇发青,眉头紧皱,好似每一刻都在忍受着剧痛,真是令她心疼。
自床榻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姜一闲紧张地跑过去,将他稍稍扶起来,好替他顺气。闻人御还没有醒来,他咳嗽完偏着头靠在姜一闲的脖颈间,姜一闲忽然看到一团鲜红的颜色刺了她的双眼,她伸出一只手,把那东西拿了过来。
是绣了蜜蜂和兰花的手帕,上面一团散开的鲜血,分明是因人咳血而印记在上头的。
“他都咳血了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自己喝药?”
“陛下发病还是头一次,但是陛下咳血不是一回两回了。陛下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他不准请御医,就是请来御医开了方子,也坚决不喝药。他对奴才说什么听天由命只怕是只怕是”王富贵拿拂尘捂着脸庞,没了下文。
“只怕是什么?!”姜一闲急急逼问。
“只怕是陛下想怎么撒手,自己不想活了不然,民间的百姓哪儿轮的上当选太子这等好事”王富贵呜呜地哭了起来,甚至有些语无伦次,“陛下总嫌菜淡,饭也淡,就是连茶水里,也要放盐,还总说淡了淡了那不是人吃的东西,从一开始陛下吃几口,到后来陛下干脆就不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