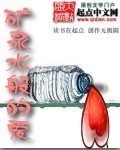漂移的恋爱-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又学到了一个测试有无心计的小游戏,问蓝璐和谢娴静想不想听。
哪有能不被趣味话题吸引的女生?她们觉得一定又是那天早上〃挤牙膏〃的心理测试,让尤美快点说。
尤美神秘地说:〃我说可以,但是你们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两个女孩心急如焚,当然满口答应。
尤美说:〃你们把老鼠,老鼠说十遍。〃
两个女孩都照做了,说了十遍,一遍不漏,尤美数着。
尤美接着又说:〃你们把'鼠老、鼠老'连说十遍。〃
两个女孩子又乖乖地把〃鼠老、鼠老〃说了十遍。
尤美突然问:〃猫怕什么?〃
两个女生听到问题出来了,异口同声地回答:〃老鼠。〃
尤美笑得合不拢嘴,知道她们上当了。
蓝璐和谢娴静想了一会终于知道自己被带沟里去了,也笑了出来。尤美补充说:〃这可以测试一个人说话有无心计。比如说每句话都要深思一下的人,就是工于心计的人,是不怎么会犯这样错误的。这样看来你们俩还是很纯洁的女孩子,还是值得交朋友的。〃两个女生觉得自己被耍,纷纷爬到尤美的床上呵她的痒痒。一会,蓝璐说这还没我知道的一个笑话有意思呢。
尤美和谢娴静催着蓝璐快说。
蓝璐笑着说:〃有一天,面条被馒头欺负了,告诉了哥哥花卷,要花卷报仇。花卷一听弟弟被欺负,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立马答应面条,要去找馒头复仇——哪知馒头没找着,半路遇见了豆沙包,以为就是馒头,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揪住豆沙包,劈头盖脸一顿毒打。回来后,弟弟面条问花卷打了么,花卷得意地拍着胸脯说……〃
谢娴静和尤美又迫不及待追问道:〃说什么了?〃
蓝璐忍不住自己也笑出来:〃花卷说:'打了,你放心吧,我把他大便都打出来了。'〃大家笑完一时回不过气来,从此发誓饿死也不吃豆沙包,兴奋得半夜才睡着。
过了几天,三个女生乘着礼拜天要去中山陵看看,她们借了自行车。本来女生骑着自行车是道很好的风景线,长裙飘逸,只是她们三个女生都没借到新自行车。这旧车是学校生命力最强、最有人性的交通工具,校长换了几十任,这些旧车却还能在学校里呆着。它见证过太多的情侣在自己身上合合分分、分分合合,载过太多的不是女友的情人,有时还要忍受主人情敌尖针深扎后胎的苦痛。受过一轮又一轮学生的苦难压迫,有时还可能运气不好,遇上体重超过二百大关的胖墩学生,一压就是四年,要是这车像动物有内脏的话,早已被这些胖墩挤压出来。比如这三辆自行车从80年代进入金大后就经历了一百多个主人,只是身价仿佛是食物链,又仿佛是现在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轮减过一轮,一次降过一次,轮到借尤美车的那三个男生手里,分别只花了十元、二十元、十五元,所以吩咐她们即使丢了也没事,看来只要在漂亮的女生面前,叫花子也会慷慨起来。
四
文学中的现代诗歌,仿佛是古代富户的丫鬟,地位卑下得厉害。这大概就在于它既好写又难写的缘故吧。当初徐志摩那些人探索新诗时,还注重吸取古典的韵律格式之类,而新诗发展到了当代——是人是鬼,都能写几句断行句子,把这些句子上下排开,基本上可以算做诗了,这些人当然都可以自诩为诗人了。有人说只要不是文盲就可以做得诗人,这样看来确实也有它的道理。而要把新诗写好,首首诗歌能留名文学史,则又难得很,所以诗人又不是容易做成的。如果要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十有八九都不是诗人。
第二部分: 第25节:十二生肖怎么没鸭?
还有人这样讽刺过诗人,说一次自己在电脑键盘前乱按一气,五个字敲下回车,六个字分个行数,信手乱打出的汉字居然也能变成一首意象不凡的诗歌。诗人听了差点吐血而亡,觉得这人的观点纯粹是对现代诗歌的诽谤,举例说老鼠在钢琴键上乱走,偶尔跑出和谐声音,算不算音乐。但这恰恰说明了问题,不见着老鼠光听见声音,而且声音和谐,外人是绝对猜不出这乐音不是由乐师奏出的,只不过人们总以为自己比老鼠高明而已。后来又爆出新闻,南方有个〃诗人〃写的诗歌获得了大奖,发奖时却得知此人是个狂暴性精神病患者,人家告诉他诗得奖了,他一脸诧异,不知来者所云,把自己写诗的事早忘了,这不能不说是对诗人的一个讽刺。西方有人说,没有傻子和弱智的人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傻子的思维能力不行,而疯子却常常可以成为画家、音乐家。看来,诗人在严格意义上也就算不得作家,可以归入艺术家的行列,他们创造的意象是和绘画音乐相通的,逻辑思维不是重要因素,所以很多诗人也承认自己半是疯子。比如写小说的作家一般很难精神分裂,因为他们写出的句子中内在的逻辑联系得紧密,一环扣着一环,思维多是约束的流露,并不完全是信马由缰。而诗人则不同,他们多半以为自己的思维能突破时空限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就口无遮拦,想着想着就乱想了,容易精神分裂。有人说古典诗不也是诗么?可是这又与新诗有绝对区别的。写旧诗的人有许多约束,格律的、音韵的、格式的,无所不在,写起诗来规规矩矩,居然越写境界越高,心态越好,即使寒瘦如郊岛,创作时虽然也痛苦万分,如入泥犁,写完后发觉得意的句子还是欣喜无比,没听说哪位古典诗人写着写着想不开就去卧轨,当然古代也没铁轨。那就算上蹈海,那些被水淹死的旧诗人,很多都不是自身情愿的,比如渡海遇风的王勃和临江醉酒的李白,当然政治不得志的屈原除外,都是无奈掉进水里爬不起来呛死的,鲜有朱湘这样主动跃江、伺身喂鱼的新诗人,而杀妻的诗人上千年也就出了徐渭一人。可新诗从20世纪开始后还不到一百年,就出了顾城,由此看来旧诗让人变态的可能性似乎远远小于新诗。
这不,金大分校区文学社的学生对中国新诗很感兴趣,其实说中国新诗仿佛是说陶瓷美国造一样,这新诗本来就是西洋的舶来品,与鸦片在传播上除了时间先后外,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好比鸦片成就了不少中国做这个生意的富商,而新诗成就一小部分人的名声外,害死的人也绝不比鸦片少多少,比如朱湘、海子这样的人生前中了毒害,死后就都到缪斯女神那算账陪钱去了。现在写新诗的人往往看透了诗歌的本质,对它的态度多半是消遣,仿佛对待情人一般。比如这个发起诗歌朗诵会的男生,要他在诗歌、外语考级和女朋友之间选择两样的话,落选的肯定是诗歌。但诗歌仿佛贱得很,人家对它不好它还越对人家好,比如至少可以让这个男生在金大的圈子里成一下小名,别人知道他是〃诗人〃,而没人觉得是他成就了诗歌,称他〃人诗〃。尤美班里一些偶尔写诗的人都被这个男生邀请了去,尤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在被邀之列。去么觉得自己又不是诗人,不去么又在一个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做人不能这么决绝。后来回到宿舍发觉谢娴静也在被邀请之列,惟独蓝璐不在此列。谢娴静说是班里的一个男同学和那男生是朋友,是他把我们两人给供出去的,这下尤美明白了自己成〃诗人嘉宾〃的原因了。只可惜蓝璐没被邀请同行,噘着嘴在一边看书。有时公益的活动虽然自己也并不想去,可虚荣的人还是希望被列在邀请之列的,这样面子就好看些,至少心里不会见别人走后有怨恨邀请者的感觉。那主办的男生仿佛有先知先觉,知道蓝璐即使邀请了也不会去的,所以干脆来个未卜先知,不邀请她,或者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蓝璐的存在。可见大学女生的相貌是多么重要,在公共场合,美女可以当鲜花的作用,而丑女则仿佛饭桌上飞来飞去的苍蝇一般,会让人咽不下饭。蓝璐这天早早起床去了图书馆,免得见着谢娴静尤美在她面前走时,心里尴尬,好像成了被天鹅们遗弃的丑小鸭——更可惜的是,十二生肖里没鸭的位置,蓝璐属鸡的。
金大主校区到分校区有一长段的路程,需要过江,得坐校车。现在的学校纷纷扩建,比如浙江的那所大学,什么学校都收购,仿佛是郊区的垃圾回收站或者深巷接客的女人一般,来者何物何人一概不拒。学校规模扩建大了就要搞分校,这主校和分校的地位仿佛有着大妻和小妾的尊卑,这里边最忙的是校长,仿佛要在大妻小妾间维持协调,分了两处的一校,其实与两校无异,一个校长不得不两边看管,哪边都要不出事。比起全国其他的大学,金大的范围还是属于小的,没鲸吞旁校,所以校长忙里还可以偷偷闲。分校的学生到了大三就可以到主校区上课,仿佛丫鬟进身小妾或者弃子归家,这对学生倒没什么伤害,只是每年学校要为老师在校区间授课来回的接送,花费不少的费用,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后,往往把校车坐满、站满,大有不坐白不坐的怨气。尤美和谢娴静不愿意和他们挤一车,闻他们的汗臭。上回去中山陵骑自行车上了当,她俩决定这次不再借车,借了也上不了大桥,万一把轮子陷进坑洼的桥面,拔不出,那就惨了——可见大桥之老。两人乘了公交车过了江,这公交车还算争气,在老得像地雷炸过的大桥上,还能坚持至少三个轮子着地。
第二部分: 第26节:两人好到“相食以沫”
到了浦口,分校的景色展现在她们的眼前。她们是第一次来分校,原本以为分校的设施不会比主校区好,哪知道丫鬟小妾通常都比大妻美丽许多。这里面有山有水,山是假山,水是河塘,有长亭回廊,典型的江南风光,尤美和谢娴静这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前同学说金大是江南第一学府了,复旦哪有这个阵势。
正陶醉于对名校的联想之中时,远处亭子中的景象让她俩大跌眼镜:一对恋人赶早起来谈恋爱,两人搂在亭子中,正吻得猛烈。尤美猜想大概其中一人没钱吃早饭,肚里饿得发慌,可能连牙都没来得及刷,就找来了对象,两人好〃相食以沫〃。尤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谢娴静,谢笑着说忒恶心,让尤美别说了,再说就要吐出来了。看来大学中起早的人也未必是真勤奋的人。
尤美和谢娴静实在找不到朗诵会指定的逸夫馆在哪,于是问了一下同学:〃请问逸夫馆在哪?〃这逸夫馆仿佛是大学的形象工程,每个大学都会有这样的楼。尤美以前一直不知为什么好多大学有逸夫馆,谢娴静告诉她说是香港的邵逸夫捐资的。
这逸夫馆躲在了最北面,俩人在得到同学的指引后,径直走了过去,到门口时发现一张欢迎牌,字迹潦草,隐约看出是〃热烈欢迎各位老师、诗友来到原创诗歌朗诵会现场〃。
()好看的txt电子书
下面紧写着一行小字:〃嘉宾们请到三楼306大教室。〃
进入了教室一看,那教室已经被桌子围成了圈,仿佛开董事局会议。大概有三十来人,议程差不多已开始,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学生,也有老师,尤美和谢娴静扫了一眼,都担心自己的导师刘文正也在。一看他不在,心里宽松了许多,那感觉像吃饱后发现周围没人,可以借机松一下过紧的皮带一样。
同班的男生沈周喊尤美和谢娴静过去,示意那边给她们留好了位置。这沈周就是第一天就讽刺班长的那位男生,他父母都是画家,出生扬州,但是喜欢苏州的画风,崇尚明代沈周这位才子,恰好又姓沈,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沈周给她俩介绍说:〃那位站着说话的男生就是发起者,他是本科的小弟弟,叫马克。〃尤美和谢娴静听了介绍都想笑出来,说:〃为什么不叫卢布呢?〃沈周一向油嘴滑舌,不假思索地说:〃马克值钱吧。再说你们怎么不往'马克o吐温'这个大作家的名字上想。〃俩人一听德国货币变成了美国作家,掩嘴而笑。
沈周示意马克再介绍一下刚来的两位女生,马克知道了他的意思,介绍了起来。此时马克愣了一下,发觉这个尤美好像在哪见过,一时间没能往洗发水广告上想,只是说:〃刚才来的两位女嘉宾是中文系研究生,诗人尤美和谢娴静小姐。〃小姐在当今已经成为贬义的词,不料有研究生和诗人的头衔作为定语,这〃小姐〃仿佛还了魂,变成了世界上排名前三位好听的词——另外两个词是〃我爱你〃〃讨厌〃。
大家朝尤美的方向望去都觉得她很眼熟,又一时想不起,大概心想天下的美女都很相似而丑女则各有各的丑相吧,所以都没深加追究,没一个人把她和洗发水广告联想在一起,尤美来到金大后也没提,因为她觉得这个广告曾让她伤心过一次。
尤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