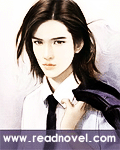[主受]阳光如约而至-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年的冬天,袁大军看到了满大街的孩子拉着“雪橇”上学。不过人家是两个人自由组合,一人一程替换,他是从头拉到尾。这个冬天,袁大军每天都盼望着太阳出来把雪晒化。可这个冬天的雪格外的多而大,还格外的冷。到寒假回家,苏尚喆都是坐在反扣的板凳上让人拉回家的。
苏尚喆说:“大黑大黑,要被常宝追上啦,跑快点。”
那个傍晚一群孩子出来捉迷藏的时候,袁大军等常宝藏起来后,偷偷点了个炮扔在他屁股后头。常宝吓得跳起来,一下碰到了头,半晌没晕过来向。袁大军想,让你跑那么快,崩不死你!
7。尚武的梦想
一九七六年,社会并不是不彷徨,小城并不是不混乱,学生的成绩虽然受标榜但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第一位的,孩子们的生活也并不是井然有条的,然而苏建之一家却是幸福的。苏尚武苏尚雯接连初中毕业入高中,却神奇地避开了上山下乡的紧密几年,得以留在了父母身边。
对于大批下乡的知青青年的生活和痛苦,这些孩子们毫无所觉,依旧活得恣意潇洒,且对于一切据说利于国家建设的事情都热血沸腾。在苏尚喆的记忆里,一天苏尚武偏挎着书包跑回家冲着老爹喊:“我要下乡支持建设,为什么这次没我的名额?”
尚安琪二话没说把大儿子的嘴巴给捂住了,老爷子三步并两步关了门,这才抖着手指着大孙子气得浑身发抖。下乡对孩子来说可能是另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而对于父母来说,有些时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灾难。
苏建之和尚安琪的同事们中间不乏有人的孩子跟着大潮去了农村,如今想回来却无从下手。虽然有地区已经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或病退的名义返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每个地方都是巨大的关系网,一人不批准,孩子就一年不能回来。多少人在城里哭天抹泪想把孩子弄回来,孩子们也努着劲儿的想返城却为了几个可怜的名额争破了脑袋,最终却迫不得已的继续留在那穷乡僻壤呢。
苏尚武“积极向上”的后果就是,被家里三位长着关在房间堵着嘴教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苏尚喆收拾好自己的小书包趴在窗户上等袁大军来喊的时候,看见了摇摇晃晃下了床,带着浓重黑眼圈的哥哥。
“哥你要是下乡,我和姐以后都不要你了。”
苏尚武心里还存着火呢,听弟弟这么说眉毛一拧就想发火,看着弟弟乌溜溜的眼睛又把话咽了回去。
唉,弟弟不懂哥的心,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尚武扭头看看开始匆忙准备上班的爸妈,趴弟弟身边小声说:“老师说了,要把知识带到需要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哥是戴过红星帽的人。”尚武低头把胸前的五星徽章扶正了,低声嘟囔,“说了你也不懂。我都懒得说,咱爸咱妈活得太小心翼翼,尤其是咱妈,生活太小资。别人都忙着国家建设,她还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我同学都说了,他妈说,咱妈要不是运气好没参演过反革命剧,早年肯定被批斗进去了。”
苏尚喆对那些动乱的印象并不深刻,所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父母的保护都避开了他的双眼。他唯一的记忆就是尚安琪喜欢摸着他的头说,要不是多多聪明,你爸爸现在不知道被抓哪儿去了。
在他对母亲隐晦的话语理解里,外面那些戴着红袖章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的人随时都能化身暴徒。他们带走了母亲的领导,带走了父亲的同事,摔碎了家里奶奶留下来的一切东西(破四旧)。
“妈妈说,吴叔叔还没回来,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
“老师说他不男不女,还总唱讽刺革命的戏。”
袁大军在下面喊,“多多,上学啦。”
苏尚喆跳下小板凳,脸拉的很长,“你要是让他们把爸爸妈妈抓走,我肯定打你!”
尚安琪收拾妥当从里屋出来,嘴里唠叨:“爸你不用做饭,中午我早回来。记得把馍馍晾出来别捂着。”
转头又指着尚武狠狠低声威胁,“你要是敢提,小心回头让你爸剥了你的皮!不懂事!”
尚喆跑过去跟着母亲下楼,出门的时候还扭头看着自己的哥哥,扁着嘴眼睛里带着怒气。
尚武觉得自己和弟弟有代沟了,自己的抱负弟弟一点都不能了解。
文革带给了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什么?他跟着学生去贴大字报,轮班帮忙看守压在自己学校的嚣张反动分子,他因为夜里抓住过偷偷和“反动分子接头的人”而得过表彰。文革期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时候他坐在教室里跟着老师一起听广播里的歌声,一起唱着《东方红》,一群学生唱到热泪盈眶,体会那种最真实的激动。
他们身体里热血沸腾,每一滴都写着热爱国家热爱毛主席。
尚武坐在教室雄心壮志的时候,尚喆还是个小奶娃;尚武开始戴着五星帽积极进步的时候,尚喆被看顾的好好的站在大院里吃糖葫芦;尚武怀着建设国家的梦想想要为国家添砖加瓦时,尚喆背着小书包站在窗前等着那个黑不溜秋的大圆脸来叫,然后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他太小资,脱离人民群众。
尚武觉得,自己的弟弟太乖了,乖的一点都没有男孩子该有的热血和激情。虽然昨晚被三个大人堵在房间嘴里塞着布巾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教育和抨击,尚武还是觉得,家里再搞资本主义路线,也不能阻挡自己社会主义的脚步勇猛前进了。
他不知道这次之所以老师没有找他问话,是因为尚安琪私下做了多少工作。他不知道之所以没有列他的名字,尚安琪从一家人的口粮里省出了多少,都用委婉的方式和他的班主任做朋友,然后作为朋友间的互相扶持孝敬了别人。尚武环视这个拥挤的小屋一周,整理完书包雄赳赳气昂昂,怀揣着自己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奔向了远方。
尚武戴着大红花站在一群下乡知青中间的时候,尚安琪正在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是前不久尚安琪去了趟上海进修,专门找这剧的编导学过来的。尚安琪甩着粗长的辫子踮着脚尖高高跃起,依旧美丽的身体在空中旋转。有人推门进来喊:“尚老师,你家尚武要离校下乡啦,戴着大红花,街上正欢送呢!”
尚安琪一脚踏空摔了下去,好半天都没能站起来。瘸着脚追出去的时候尚武正咧着嘴冲欢送的队伍挥手,脸上的笑要多自豪有多自豪。他要建设国家去啦,他将会变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太多,尚安琪要积极向上,要拥护国家建设。她挤开人群抱住自己的大儿子,狠狠的捶了他两拳,带着浓重的悲伤。脸上是慌乱中没有洗干净的妆,红扑扑的脸蛋,掩不住腮红下真实的苍白。
尚武说:“妈,我建设国家去了。”
尚安琪抬手去摸他的脸,使了暗劲儿,拧得尚武眼泪哗哗。尚安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你好样的!”
尚武说:“哎妈,疼,嘿嘿!”
这个秋天,刚高一的苏尚武怀揣着他卫星升天般的伟大梦想主动建设国家去了;这个秋天,同样高一的苏尚雯爱上了文字,凭着两首歌颂这座城市歌颂工厂工人的酸诗进了学校文学社;这个秋天,多多依旧乖乖的上学放学,“欺负”袁大军,温书发呆养兔子。
兔子生了,阳台上的小木笼被迫变成了小木楼。老爷子的琐事又多了一项,观察小兔子的成长,然后帮小孙子写观察日记;这个秋天,相比其他人仿佛一帆风顺泡在福窝里的尚安琪,开始为大儿子焦心。他吃得饱吗,睡的好吗?会不会在乡下被地方的人欺负了?会不会劳动的时候伤着手脚了?累的睡不着觉了?这个秋天苏建之也多了一件事,聆听迅速进入更年期的尚安琪唠唠叨叨,或者是深夜的唉声叹气。
事实上尚安琪的唠叨不仅仅针对苏建之,家里任何一个人在她身边停留,都能听见她说不完的话。
尚雯放学晚回家的时候,尚安琪正对着帮忙抻毛线的苏建之说:“人家都去乡下看儿子,咱们什么时候去一趟?你总说不去不去,不利于尚武表现。你知道尚武才多大吗?他还半个孩子呢。要是到了乡下像刘梅说的,要掏大粪担土可咋办?”
见尚雯回来话题转移,“又上哪儿野去了?以后放学早点回家。”
苏建之连忙脱手,将毛线递给自己闺女。
“诶,你这是抻毛线呢还是自己玩儿呢?高点高点,还是给你织毛衣用的。”
“啊,母亲,您的唠叨像一首夜曲,流淌在我心里。”
“滚!就知道写这种酸臭的句子。”
“啊,老娘,你长了两根白头发。”
“……老苏!老苏你过来,谁昨天说我满头乌发似海带的?”
尚雯哈哈大笑,“我的文艺细胞绝对遗传我爸。”
苏尚喆在尚安琪暴走要找镜子之前走过去,扒开头发给她拔白头发,顺手藏起来四五根白的,嘴里说:“啊,拔成黑的了。”
漂亮的妈妈头发开始白了,都是苏尚武不听话造成的。
苏尚喆在小小的日记本上写到——哥哥去乡下了,妈妈很生气很生气,头发都白了。我也很生气很生气,决定把零食都吃掉。姐姐说,乡下很多鸡屎,河里很多吸血虫。还说,到了乡下都吃不饱,大家都是吃树皮。我给哥哥流(留)了一包饼干,给他吃。王蓉告诉我她喜欢大黑,说他可有气盖(概)了,我讨厌它。
这个年代的远离意味着什么?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并不明白,苏尚喆更不明白。他开始习惯没有哥哥的生活,也开始习惯一家人饭后围着桌子听尚安琪读尚武的来信。
尚武的信总是充满生机的,他开头总是这样写——爸爸妈妈爷爷弟弟妹妹,见信佳!
他说:秋后的乡下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很清闲,帮着村里做一些小事。东家挑挑水,西家补补房子,还帮着学校带一年级的语文课。深深觉得有爸爸这样博学的父亲,和妈妈这样气质绝佳的母亲,对自己裨益良多。我用爸爸教给的知识来教孩子,还教他们唱着我们的田野,跳妈妈教的四步舞,他们很开心。家人勿念,我过的充实且快乐。
而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他们这批孩子被分到了河滩地,秋冬没有农事,便被分配了去挖河道修大堤。第一天从淤泥里挖出一条泥鳅,尚武还兴奋了半天。第二天手上起了水泡,浑身散了架似的开始难受。所有的人都这样,老知青却劝告他们坚持下去,不然搞特殊,娇生惯养不利于和村里人团结。
尚武挖了半个月的河道,肩膀每天都脱臼似的疼。终于在无尽头的河道里,在无数知青隐忍彷徨的话语和表情里,混乱了他建设国家的梦想。他找不到挖河道和卫星发射有什么联系,不懂得为什么几个老知青要可劲儿巴结公社里的头头,也无法给那些像犯人一样在鞭子看管下劳作的人冠上什么十恶不赦的名头。
那夜白发苍苍的老人裹着包袱沿着崎岖的小路给儿子送饭,看到他时扑通一声就跪下的举动还是狠狠捶了他的心,让他回头看那些“激情四射”带着红星帽进步的日子,竟发现他们做的,并不都是对的。
河段是按人头分下来的。像他们这些男生,不管大小,都是一人一天两米。而挂着被批斗牌子的,不管老少,都是一人一天三米五。干不完,不能回去吃饭。清理主河道里的泥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米,一般的小青年不紧不慢,一天也才正好赶出来而已。如果中间偷懒了,必定要加工。
尚武他们和“反动派”的河段中间隔了一定的距离,河岸上也没有人抽着旱烟监视。
李瘸子是个将近五十的男人,听说是个大富农,曾经圈了三四十亩地,家里还盖着两层的小楼。小楼已经成了公社,男人的老婆也已经上吊死在那场动乱里。听说之前并不瘸,那条腿伤在批斗会上。听说男人的儿子因为阻止抄家态度恶劣,被活活打死了,女儿如今嫁给了村里最穷成分最好一直没娶上媳妇的一个秃子。还听说他们罪有应得,剥削无产阶级,生活奢侈每天享乐。
尚武还在四肢不听使唤的倦怠期,那天的两米任务直到天黑都没有完成。其他人先后回了公社,为了不落后,尚武还是坚持要把剩下的挖完。
那晚月光算不得好,尚武摸黑坚持把自己的两米挖得和别人一样深才收了铁锹。不远处李瘸子已经不在了,他那三米半还有一小半坚强的躺在那里。尚武浑身酸痛地爬出河沟,走了不远就看见前面李瘸子猫着腰一瘸一拐的往前走。
尚武不远不近的跟着,想看看这个已经被打折了腿的反动分子又要干什么坏事。跟了不久,就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人迎上去,塞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