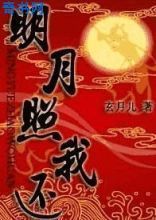我还是过得很好-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是本无路的一片绿林,走的人多了,踏出一道极窄的裸露土地,像是少女青丝间柔和的分发线。
一程道路距离不远,一段路程走得不长,越过匍匐的山丘,突破遮挡着月光与天空的层层枝丫,陈琛的眼前豁然开朗。
唐宵征回身冲他伸出手,仿佛披戴着漫天星辰,又携着垂悬蜿蜒的山涧清流。
“认得么?”等两人在这巧夺天工的观景台上彻底站稳,唐宵征再一次询问,然后果不其然地,看到陈琛茫然摇头,于是他再给提示,指着山谷对面,一片整齐的阶地,“那是烈士陵园。”
陈琛盯着那边许久,缓缓睁大眼睛,恍然大悟,“这里是……扫墓那年来过的地方!”
“嘘……”唐宵征的食指堵住陈琛唇边溢出的高呼,不久后微弯眼睛,柔和的像是换了个人,他低声说,“你想起来了。”
透过峰峦匍匐的弧度,他好像看到许多年前天光明朗的一天。
彼时陈琛和唐宵征还都是高不过同班女孩的小学生,一个捏着尚青用白娟扎成的精致漂亮的小雏菊,一个攥着自己用卫生纸揉成的粗制滥造的所谓白花,站在扫墓的队伍里,站在“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巨大石碑之下,一个接一个,爬上长长的阶梯,把手里的白花扔进花圈围起的石碑的脚下。
那时孩子们还不甚明晰爱国教育与春游踏青之间的区别,在上午日程结束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成堆成伍,聚在各式刻满功绩与生平的墓碑周围,各自分享着零食与午餐。
样式可爱的软面包,桶装的滚来滚去的果冻,亦或半袋儿都装着空气的薯片……在一双双手之间传递。
烈士的英魂栖于地下,望着鲜血打下的一片山河,终于让后人安居乐业再不愁吃穿,大概是很欣慰的,但河清海晏的盛世里,人与人依旧有点差别。
彼时唐宵征便拎着自己只装白馒头和小袋装榨菜的口袋,游离在外,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
与许多同学不一样,唐宵征的节俭不是来源于家庭贫困亦或是妈妈严格的约束,而是全然来源于不知章纪舒几天之后才能清醒着拨出一笔生活费供他花销的恐惧。
于是兼顾自尊与将将滋生出的面子观念,他忽视了所有招揽和邀请,打算找个无人的角落,悄悄解决自己的午餐。
于是乎所有人都放弃了再次邀请,毕竟这个从不跟他们一起喝校门口一块钱一杯的奶茶,买五角钱一沓的英雄卡片,或是一起出去疯玩度过周末,而总是脖子上挂着公交卡,按时放学回家的男孩,不过就是成绩足够好深受老师喜爱,所以不会被捣蛋的男孩儿们欺负的一个陌生同窗而已,不来就算了。
当然,这些人中没有那个从来不会看人脸色的陈琛。
唐宵征大步走在前面的时候,不必回头就听见铁勺撞击饭盒盖子的清脆声响,这使他更加烦躁,莫名其妙的赌气之下,步速愈来愈快。
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追赶之间,就已经走出了老师规定的活动范围。
陈琛已经不记得两人到底走出去多远了,他只记得唐宵征停下来赶他离开的时候,自己就站在这个隐蔽观景台的边缘,喘着粗气一脸茫然。
“为什么要我走开?”小陈琛一屁股坐在地上,扯开不久前才刚被系好的红领巾,小狗似的喘,“还要去哪里呀,咱们不如就在这儿吃饭吧。”
“……我没钱。”事实上小时候的唐宵征从来都没钱,可即使在陈琛面前,这三个字儿也是头一回从他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他想说所以我没东西跟你交换,你别来烦我,自己去吃饭行不行,可他想起陈琛那么爱哭,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我知道,可我不是来要钱的。”陈琛全没听出话外之音,打开自己的饭盒,尚青精心准备的菜花花绿绿铺在白米饭上,是一张小老虎呲牙咧嘴的笑脸,他献宝一般拿起来给唐宵征递过去,“你看,今天没有花椰菜,放了好多小香肠。妈妈说做给咱们两个人吃的。”
“还给了我两个勺子,两双筷子,还有两盒牛奶。”唐宵征大概看不到自己的表情,他也忘了自己本来想说什么,只听见陈琛语气突然慌张起来,夹着泫然欲泣的哭腔,“哎?筷子怎么只剩一双了,不是又被我弄丢了吧……这怎么办啊?”
“不许哭!多大点儿事。”唐宵征的执拗不翼而飞,一屁股坐在陈琛身边,打开了口袋取出自己的,“这双给你拿回家去,什么也别说,你妈妈不会知道的。”
于是盒饭一人一半,馒头一人一半,小袋儿榨菜一人一半,两个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小孩席地而坐,在罕见没有下雨的清明山间,样样都没能吃完,最终全被唐宵征收进口袋,带回家凑活凑活,成了之后的晚餐。
后来哨音隐约响起,两人急匆匆往回跑,陈琛一边攥着自己先前宣誓才被老师给系好的红领巾,担心会不会自己犯了错又被收回去,一边还信誓旦旦回头跟唐宵征交代,像是念叨着某种奇妙的咒语,“就说是馒头不小心滚过来了,咱们只是捡馒头所以跑的远了些,老师不会罚咱们的,我的红领巾也没有问题,不会的不会的……”
事实证明,陈琛的确从小就不会撒谎,又总是多虑,馒头不会从山腰滚到山顶,老师对红领巾也并不像他那样看重,批评教育一番之后,清明的行程再一次开始。
后来陈琛拎了筷子勺子回家,那时候没发育起来的智商还不足以令他自己反应过来,即使不说,两双不锈钢的筷子忽然有一双变成了木质的,这怎么无法瞒过尚青的眼睛,可那时尚青什么也不说,笑一笑,装作没看出差别。
“你怎么还记得这个地方?”唐宵征的一声轻笑,拉回陈琛飘出去很远的思绪,他回神,“经常来这里爬山?”
“没有。”唐宵征摇头,嘴角上挑,“单纯的记性好而已。”
“嘚瑟……风景这边独好,我也记得。”陈琛望着他皱了皱鼻子,偷摸换只脚继续站立。
唐宵征没说的是,记住这个地方,不是因为风景,是因为人,也许没什么特殊的事情,也许都是些无聊的戏耍,只要跟陈琛有关,他就不知怎么的,记了好多年。
好多年……他侧身去看陈琛,看到他不断变换重心的站姿,突然觉得有些疲惫。
他发现原来两个人都在长大,都在变化,陈琛已经不再是那个没心没肺又随心所欲孩子,会怕新衣沾了灰尘,所以即使累的腿疼,依然强忍着战直。
而自己也不再是那个倔强执拗都很表面的单纯小孩,开始顾虑着莫须有的未来光景,克制所有汹涌而来的想要亲近。
真累……
沾衣浮尘只要清洗就能干净,那自己放纵心意去亲近的后果,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无可挽回呢?
名叫唐宵征的这个人,仅有的一去不复返的人生啊,是在向谁妥协,又在为谁而凑活?
许久,许久,久到脚下着了火似的烟尘融成一片悠远的浅灰,耳边近似自语的呼唤。
“琛琛。”
“嗯?”
陈琛回头,瞳仁映出月光下骤然逼近的阴影,唇瓣触及有些野蛮的湿润的温软。
世界在眼中颠倒,旋转。
陈琛脑海里凌乱的回想,清炒年糕,松鼠桂鱼,油焖大虾,炸素丸子……
他确定自己没有喝酒,又确实有些不胜酒力。
颤抖的心跳和跌撞脚步中,陈琛伸手环住唐宵征的脖颈,在黑暗中,探索两个人的亲密。
凌晨,陈琛跟着唐宵征回了他无人的家,上楼之前,看到这人跑进唯一亮着灯的一家便利店,不一会儿走出来,两手空空揣进口袋里。
“你……买了什么?”某种奇妙的预感下,陈琛横跨一步,拉开半臂的距离。
“这些。”唐宵征冲他撑开口袋,路灯之下,露出里面装着的小瓶透明啫喱,和一小盒商标醒目的橡胶乳制品。
“哦……哦。”咽了下口水,陈琛撇开视线,心跳之余竟然有些断断续续的窒闷,“我看清了,你收好。”
余下便是久久的无言,唐宵征用放在陈琛那里的备用钥匙打开门,回身,落锁,开灯。
“随便买的。”他回身,脱下外套挂在门边,拍拍陈琛的肩头,“留着备用,别紧张。”
“我的卧室今早——昨天早上收拾过,你去我屋里睡。”他走出去两步,又回头,“我睡我妈的房间。”
“啊?”本有些莫名拘束的陈琛听了这句回神,“干嘛?不是每次都在你的房间挤挤么,你干嘛?”
“今天不行。”唐宵征停下来,想了想,突然走近脱掉陈琛的外套,“我可能忍不住。”
他也只是脱掉了陈琛的外套,掸一掸挂在门边,“去洗漱吧,你那套东西放在老地方。”
“干嘛去?”陈琛这回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衣角。
“睡觉。”唐宵征好像又变回了熟悉的那个人,笑一笑,“不然跟你大眼瞪小眼?去吧,你收拾完我再用浴室。”
“……我不。”好半天,陈琛抿抿唇,突然兴师问罪,“你怎么这样儿的?”
“不问问我,就买了那些东西,也没问问我,就搞什么坐怀不乱的,你倒是柳下惠有风
度,我呢?”他手上攥的紧,指尖都被捏的没了颜色,“我,我也没说不愿意啊,那我要主动求你跟我睡,是不是有点儿潘金莲的感觉……”
陈琛踮起脚吻在唐宵征脸颊,那话的余音便化作湿热的水汽,虚虚擦着耳廓钻进脑海里,钻心的痒,“我就是有点儿怕疼,你轻点。”
山海的某一隙,朝阳正懒散地升起,天色擦出黯淡的灰,快亮了。
唐宵征拉上窗帘,满室昏暗中,压进迷离的喟叹里。
“……新年快乐……”当浅色的窗帘也无法再遮住天光时,粗重喘息中有人低低呢喃。
唐宵征替他掖好被角,笑了笑,心知,在一起这件事,无论如何辩解,都已经不再是试一试这样容他逃避和敷衍的说法了。
第四十六章 ——世界喜忧参半
天光大亮,焕然的清风拂散前夜的落雪,南方的城市薄雾蔽日有些阴暗,北方的朔桑却依旧高空万里无限晴朗。
如同迥异天气一般,在一个又一个365日的轮转之后,这个世界,依然喜忧参半。
当久不曾主动汇报过自己动态的梁断鸢收到唐宵征迟来的新年祝福,并从字里行间看出这位口是心非朋友的人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时,这个大个儿正身处离校不远的三甲医院里,下颌胡茬发青甚至还穿着睡裤,极其少有的显出些不修边幅。
距他不到10米远的身后,“精神卫生中心”六个大字儿,悬在门诊楼入口的正上方。
大概五分钟之后,安易持的身影从入口处显出来,梁断鸢掐了烟挥挥手,打散周身缭绕的尼古丁的刺鼻气味迎上去,“怎么样?”
“好像不是太好……”安易持依然笑着回话,只是那笑意比起早先,显而易见的有些疲惫,他把手里拎着的口袋递给梁断鸢,颔首就将表情隐进毛茸茸围巾的边际里,“大概要花些钱了,我去打个电话,可以再等等我么?”
“嗯,去吧。”梁断鸢注视着他走远,遂从纸袋里取出各式各样的诊断结果,从中搜寻着简明易懂的结论。
半晌,圆滚滚的一只麻雀跃上高枝,扑簌簌抖落一阵细雪,抱团的冰晶划过纸张上“重度抑郁”的字样,划过“重度焦虑”的结果,也划过“建议入院治疗”的倡导。
最终打着滚越来越近,停在树下人捏着纸张的拇指边缘,不多时浸湿纸张,扭曲了“有自杀倾向”这几个油墨尚温的清淡的字迹。
梁断鸢仍站在原地,翻来拂去看着结果,一遍,两遍,三遍……等“有自杀倾向”几字儿再次突兀地映在眼底时,猛地停下来,拔腿往安易持消失的方向追去。
好似《罗拉快跑》里那个红头发小姑娘拼尽全力奔跑的场景,往事折叠颠倒,又一次在梁断鸢脑海里上映,匆匆流逝的这一月时光,他不期然又走了一遭。
1月18日,寒假留校的学生被要求搬到南区集中住宿,那天,不愿回家的安易持背着一个双肩包,低头穿越一众行李箱堆叠掩映的人群,顿了顿,敲响大学以来从不曾回去过年的梁断鸢宿舍,大敞着的房门。
1月21日,在公司做完白工凌晨回来的梁断鸢撞上安易持满是清明的空洞双眼,那是不寻常的第一夜。彼时易持呆愣着看了看他,只笑一笑,说担心他彻夜不归,在等他,后来有意观察之下,第二个通宵,易持抿抿嘴,说“白天喝过咖啡”,第三第四个通宵,易持翻个身,把罪名推给一杯奶茶,亦或是半杯可乐……终于,到了一周之后再问,易持甚至听不见问话,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娃娃静静盯着天花板,半晌之后回神,再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