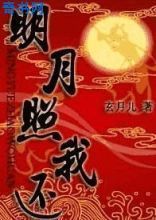我还是过得很好-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还盼着我以后能坐办公室享清福呢,就算是我这种废物……也不想让妈妈失望。”
他没听到预期而来的嗤笑,迟疑着转头去看时,李柬窝进座椅里,用一个随意且舒适的姿态,他伸手随意扒拉斯剑的脑袋,半晌感叹,“你长大了。”
斯剑那时候并不太懂,只随着李柬的动作摇摇晃晃。
“没什么对和错。”李柬摁灭了烟蒂,扔进档位边的易拉罐里,“曾经喜欢的东西,现在让你难堪,并不是喜欢错了,只是你长大了,别怀疑自己。”
“还有啊,忘记说了,别人的眼光和看法,听一听就罢了,横竖活着的人是你自己。”那天临下车前,李柬好似这才想起来似的回身又补了一句,“但是我这句你一定记着,学校外面还是学校,要想活的好就逃不开学习,好好念书。”
“呵,站着说话不腰疼。”斯剑跟在他身后,举着书包遮住脑袋,几步跑进楼道,很有些不服气,“你自己不就是早早没去念书了么?”
“我?”李柬摇了摇头,像是有些无奈,他说,“我命不好啊。”
那一声悠悠的叹息扩散出去,点亮了下一层昏暗的夜灯。
彼时斯剑只是一怔,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他跟李柬道了晚安,转身推开自家大门的时候,心里在想。
长大……我大概真的是长大了。
从前讨厌的,譬如说教,能让他跟妈妈怄气不肯吃饭,能让他跟老师对峙不进课堂,可现在话从李柬嘴里说出来,他忿忿之余竟觉得有些道理。
一颗被很好的抚慰到的心,便是从那天开始,稳稳当当落到李柬身上去的。
张晓莹第一个察觉了儿子有些不对头,只是偷摸翻完了斯剑的日记,也没找出什么可疑的女孩子,外加几次大考斯剑名次稳步上升,甚至把之前宝贝的紧的MP4都交给自己看管,她细细想来,终于是没有再多加看管。
也就没能及时阻止斯剑陷到人迹罕至的另一个坑里去。
斯剑开始在意一切与李柬相关的事情了,有些不由自主,他那样聪明,于是不久之后就心下了然。
他看穿了自己,破天荒的犹豫和无措,甚至唯一一次撞上陌生女人来看望李柬妈妈,有些莫名的心虚和不安。
斯剑用未经历练的克制压抑自己,藏起想要亲近的欲望,却管不住私自打量的渴求,他也就逐渐看穿了李柬,发觉那样张扬夺目的狠眉戾目之下,居然是个堪称坚毅温润的灵魂,这人表里不一。
斯剑少年时曾有许多不着边际的幻象,瞧着李柬眉弓一抹凌厉的疤痕,摸着这人手心粗粝的茧子,想这一定是打架斗狠留下的勋章,毕竟有这样威武的体魄和气势,就像小孩怀抱着猎枪,热血冲头总会难以控制。
不曾想李柬指尖划过眉间那抹痕迹,懒洋洋解释,“跑长途的时候想撒尿,停车准备进路边树丛里解决,翻过排水渠的时候没注意,被铁丝网挂了一道,没勾掉眼珠子实在算是运气好。”
他又翻转手心看了眼泛白凸起的老茧,旧事重提看着斯剑,“这就是没有好好念书的代价,只能干些力气活儿来养家。”
甚至当斯剑打卡似的拍打他的大臂,询问如何练就这样一身肌肉的时候,李柬叼着烟卷笑出声,刚吐出的眼圈重又给他吸进嘴里,像个新手似的被自己呛得咳嗽,“不用练,天生的。那话怎么说来着,天生我材必有用。”
彼时斯剑伸手拍打他的背,撇撇嘴角表示不屑,“呦,这会儿不是个文盲了,还会背诗?”
李柬眼神一顿,笑意收敛了,目光落向遥远的虚空,“你不知道,文盲懂的东西也有很多。”
斯剑摸着牧马人的保险杠恋恋不舍时,觉得这头蛰伏野兽一般的钢躯铁体,一定是李柬翻山跨水带回货物的坐骑,它穿越狰狞原始的林间绿野,负重捆绑着试探律法的违禁暴利商品。
可能是走私偷渡的芯轮部件,是封面性感的露骨杂志,是堆积如山还未宣发的智能手机……
但他没想到种种臆想全是假的。
牧马人的确走野路,却不是多么风景卓越的地方,而是那种遇上下雨就滑的寸步难行的狰狞乡道,常常需要掏钱请农户开着拖拉机前来牵引。
李柬十天半月之后回来,推开泥泞不堪的车门下来站定,拉开后备箱给他看一眼,里头全是形状丑的不定性,颜色脏的不分明的海绵样品。
他踹一脚轮胎,干涸的泥巴落雨似的掉在地上,堆成一座座脏乱的小山包,随手抹一把车玻璃,露出个能看到内里的窗口,歪着嘴角笑,“你说这车?借钱买的,到现在还欠了一屁股债。那时候太年轻,不懂事,该买个五菱小面包之类,结实耐用,还省油。”
斯剑本该死了心的,李柬早跟他透了老底,连一层遮羞布也没能留下,他还有什么能够幻想的呢?
这一点也不酷,大他两轮的老男人,完全就不是个一呼百应的大哥,他甚至常常被海绵厂里雇来干活的民工以罢工相威胁,整日忙的头打脚后跟,全然是个疲于奔命的,普通男人。
可斯剑觉得自己有些过度成长了,他跟不上自己的喜好,也控制不住对着李柬油然而生的心疼,隔三差五登门拜访的陌生女人让他又难受又愧疚,他只能尽力把心思放到书本上去,以期忙碌和紧张能驱散无孔不入的李柬的身影。
那是张晓莹人生最轻松惬意的一段时日,再不用操心儿子的成绩,想着多年辛苦没有白费,斯剑已然一只脚踏进好大学的门槛了,是以收拾收拾人至中年发现了新的爱好,开始饭后睡前,跑去跳跳广场舞。
而斯剑同班三年之久的同学,却是自打那时开始,才认清了这人的真面目,原来这蔫吧自闭的小孩儿其实很暴躁,说话做事直接的让人有些打脑壳。
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高三下半学期,张晓莹闲谈过后带回来几句闲话,说李柬和他女朋友就要订婚,已经开始商量彩礼了,斯剑闻言并没有异动,照常背包去了学校。
那时当班的英语老师怀了孕,大着肚子一般不会在课堂上下来走动,据说是生怕同学们带着手机会有辐射,可她又向来是个绵软的性子,是以课堂上吵闹不堪听不清听力,还有过分者居然坐在最后一排偷偷传着篮球。
女老师气急了也只是开门出去,在通风良好的楼道里大喘气。
班长拍桌站起来,扶一把眼镜弱弱喊了声,“都别吵了!好好听课行不行?”
浑惯了的几个小子无人理睬,一片混乱之中,安静做着阅读题的斯剑对了下答案,往卷子上画了个大大的红叉,翻着书包找出体育课用过的乒乓球拍。
他直直走向最后一排,球拍狠狠掼向喧哗最盛的那人,电光火石之间,球拍打中课桌书兜的挡板,发出一声巨响旋即擦着那人鼻尖过去,打掉了一片墙灰。
这样大的力道若是真打在人的脑门上,免不得要见血,没人知道斯剑是相信自己的准头,还是根本就不在意会不会打中人。
像被人摁了暂停键,教室之内陡然生出一片寂静,女老师闻声推门进教室时,便是一根针落下也能听见响动,斯剑捡起地上的篮球横肘一把丢出了窗外,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人,很有些阴恻恻,“狗日的,欺负孕妇?”
同窗几载,斯剑一鸣惊人,此后在同学之中的风评一度超越了涛哥,是个实实在在的狠人。
某个角度来讲,斯剑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理想,虽然这是在对李柬的不满和求不得的怨气的推波助澜之下的一时冲动。
若一切都按部就班能顺利的往下进行,李柬娶妻生子开始转换重心,斯剑继续忍耐考学离开,往后寻寻觅觅遇到别的恋人,大概两人就能像条相交直线,随着时间流逝渐行渐远。
毕竟斯剑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再怎么喜欢,他也总不屑于插足别人的姻缘。
可成也萧何败萧何,正是因为这点儿难以丢弃的正义感,斯剑打破了界线,气冲冲在李柬身上刻下了自己的标签。
那晚斯剑穿好鞋袜跑下楼来,直直冲向牧马人的后座,拉开车门看也不看,推着李柬挤进车厢。
彼时顶灯还没来得及熄灭,李柬带着满心无力和沮丧眯了眯眼睛,他冰凉的手边突然传来一阵温暖,迷茫和错愕之下没能发出声音,眼前这不请自入的侵略者贸贸然开了口,“我妈说,订婚的那件事……黄了?”
第三十一章 ——倒霉的斯剑(三)
天地宽阔,夜风萧索,每一处变幻的霓虹之下都有无处可归的游人。
亮起的窗口之中,是瘦小的母亲调汤煮面等他回来,也是苛刻市井的女人满腹疑惑等他给个交代,为什么好端端的,突然不肯订婚?
她这辈子遭人嫌弃的时候太多了,多到如今被准亲家母指桑骂槐说了好一通难听话,却也不觉得自个儿受了屈辱。
李柬不想回去,他无处可去,高大的身躯蜷缩在车里,好似花花世界哪里都不能容下失意颓败的一副躯壳。
他希望无人打扰,又期待有人关照,他看着突然近在咫尺的斯剑,如坠梦里,他甚至有些不敢动,怕一不小心发出动静,就打破了镜花水月生出的幻影。
“啊……”李柬眼里盈蕴着烟雾,迷迷糊糊了很久,终于给斯剑一巴掌拍醒,垂目在自己手心摁灭了烟头,“嗯。”
“哎——”斯剑没来得及阻拦,掰着他的手凑近去看,那宽厚的掌心已然留了个红肿的凸起,“你干嘛?!”
斯剑手足无措,李柬轻车熟路。
他笑了下,皮笑肉不笑的更像是嘲讽,那幅度小到斯剑以为自己眼花,“没事,过段时间会有新皮长出来。”
“至于么……”斯剑心疼,可他不敢叫李柬瞧出来,于是眼看前窗,紧皱着眉头,“13亿的一半都是女人,找谁不是找?她自己瞎,你他妈的这么消沉干嘛?”
耳边李柬默不作声,仰靠着椅背呆了许久,“你太小了,你不懂。”
“你——”斯剑深吸了一口气,他怒火上头,就忘了自己那许多期期艾艾的夜晚,“我不懂什么我不懂,就那点儿情情爱爱的麻烦事儿,多厉害似的?”
“情情爱爱?”李柬重复着,看过去,“不是,我不信那个。”
“那你难过个屁啊!害老子白担心一场。”斯剑心里痛了一下,像被一根极细的针尖戳进心包,可大概针尖实在太细,让他觉得是场幻觉,“走了走了,你自个儿呆着吧。”
斯剑起势很急,倒像是逃命,他手都放上了门边,却被一阵牵扯拉的斜斜躺了回去,大概磕在了李柬大腿上,头骨有些闷闷的疼,“你……”
他说不下去,打了个寒颤,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一滴温热的,微咸的水珠,落在斯剑鼻尖,顺鼻翼一直滑进耳骨之上的发线里。
那年快要而立的李柬,眼眶通红,鼻翼翁张,泪水从睫毛根部逃逸,一滴一滴,全落在斯剑脸上。
“这么多年了……原来我还是没有活出个人样来,还是要给人看不起!”
那张胡子拉碴的脸隐入黑暗里,其上带着连窗外灯光也无法照亮的悲伤和不甘,那一瞬的画面,偌大的世界只有斯剑一人能从头到尾完整地收藏。
李柬撑着前座椅背的手臂青筋暴起,愤怒都显得如此隐晦,字字好似磨碎在齿缝里,
“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没念好书,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连媳妇都讨不上的穷鬼……我娘上辈子欠了谁,今天要被人指着鼻子骂出门来?你太小了,你不懂,男人在外面抬不起头不算什么,可要是连他娘也要被人这样对待,那就是挖心挖肝的疼啊?你懂不懂?”
李柬向来什么都肯说,斯剑眼里这人好像不在乎面子。
但其实事实正好相反,自尊和骄傲是人与生俱来担挑的包袱,李柬并不例外,他只是善于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遮盖事实。
譬如他眉弓的那道疤痕,根本就不是忙着撒尿刮伤得来的,买来的那辆白色牧马人,也全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甚至谦称文盲,都不过是句玩笑。
那样多的废话里,唯有一句作真——他命不好。
那年李柬十几岁,如今他自己都有些记不清了,老爹开车载他,要回老家参加亲戚女儿的婚礼。
车子从服务区开出去时,老爹刚支使着他拆开一包炒香的瓜子,“找个袋子来接着,别把垃圾洒在车上。”
老爹很爱惜车子,香槟色的一辆大众小轿,买来一年半,跑了将近两万公里,从来也没有刮过蹭过。
天气晴朗的一天,路况良好的道路,有说有笑的父子……谁也没想到前方埋设着巨大的陷阱,一辆满载货物的重卡正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岔道之前倒车。
李柬低头吐个瓜子壳的功夫,前窗隐约出现巨大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