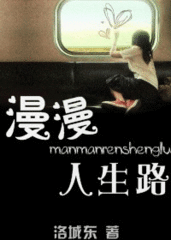无造作不人生-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杜若飞沉默下来,欲言又止。
苻容继瞅着杜若飞的脸色,看不透他在想什么,忐忑间无意识地攥紧了手机,棱角刺进手心也不觉得疼。
“我是一个人住,你回去也是一个人住。”杜若飞慢慢地说:“不如,你就把我这当作家吧?”
闻言,苻容继蓦然睁大了眼睛,指尖不可察觉地微微有些发抖。
“家”。
苻容继每每见到这个词,脑海里就剩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他的母亲是戏剧团的演员,父亲则是自由作者。
戏子与文人,郎才女貌,在话本里,演的是缱绻如梦又不食烟火的美好故事,但在现实里,只能为了窘迫的生活渐渐陷入凡间的泥沼里。
他们偶尔吵架,关紧着房门,穷尽粗鄙的语言叫骂——
“我天天在外边累死累活的上班,回来还要伺候你个大老爷们吗?做个家务你是会死吗?”
“天天喊你出去找份固定点的工作你不?守几份没人要的破烂稿子真把自己当个玩意了?”
“所有姐妹里现在谁不比我风光比我过得好,我当年怎么就倒贴了你这个窝囊废,窝囊废……”
狭小的三居室,尖锐的哭喊刺得耳膜疼,苻容继自顾自地躲到衣柜里,试图隔绝聒噪。年幼的他翻着学校发的成语教材认字,发现整页整页写得全都是“貌合神离”。
吵完架后,母亲会再打开房门,过着自以为不会更糟糕、更悲哀了的小市民日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柴米油盐,满目苟且,从无可奈何到习以为常。
即使不够完美,但家还是家,苻容继原本以为所有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直到那天,他窥见了鬼魅。
那日,学校组织高年级消防演习,于是给低年级放了假。苻容继独自在校门口徘徊了一会,自己走回了家。
家里没人,空荡静谧。
母亲应当是去上班了,父亲不知为何也不在家。
临近了冬至,万物萧瑟。风从没关紧的窗户漏进来,在滞涩的空气留下了冷意,衣着单薄的苻容继打了个哆嗦,爬进了卧室衣柜里,迷迷糊糊之间睡了过去。
他是被喘息声吵醒的。
苻容继揉了揉眼睛,透过衣柜的门缝向外望去,然后在下一瞬间,如堕冰窖。
他见到了鬼魅。
高大,赤_ruo,男人的模样,恐怖如斯。
父亲被鬼魅压在身下辗转讨饶,呻yin一声接着一声,断断续续。
床板仿佛承受不住他们重量般地吱嘎作响,嘈杂刺耳。
苻容继被吓得胆颤心惊,手脚冰凉,浑身止不住地在发抖,他想哭,却又好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地扼住了喉咙,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眼前在发黑,他拼命地捂住自己的耳朵想要隔绝什么,可是没有用,所有的声音像无孔不入的小飞虫,从他的指缝间钻进耳膜深处,肆虐地啃噬他的神经。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屋外的大门砰地一声打开,有人在尖叫,有东西被砸碎,整个世界开始坍塌,所有一切支离破碎。
母亲打开衣柜见到苻容继时,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见到了从阿鼻地狱爬上来的恶鬼。
“妈妈还会回来吗?”苻容继问父亲。
父亲最近一直在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家里到处都是烟味,西下残阳的光落进烟雾,朦朦胧胧。
“会回来的。”父亲动了动眼睛,也不看他。
“爸爸,我好饿。”苻容继说。
“哦,你好饿,你饿了……”父亲重复着苻容继的话,似乎过了很久才能反应过来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起身去厨房,翻着这几日被剩下已经焉巴的蔬菜,做了盘青椒盖浇饭。
苻容继吃了一口,撇了撇嘴,饭菜里似乎忘记放盐了。
但他什么也没说,安安静静地吃完饭,又洗好了碗,跪坐到客厅的茶几前做完了今天的家庭作业。
冬季的天黑得尤其早,不过八点的光景,余晖的光线已经完全湮默到地平线里不见了踪影,再过一个小时,就正式入了夜,天色晦暗,空气冰冷。
苻容继无所事事,早早地洗漱完毕,窝到了床上去,父亲过来替他掖好了背角。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呢?”苻容继问。
“快了。”父亲说话时还是不看他:“等我走了,就回来了。”
“你要去哪?”
“也不去哪,可能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光影绰绰,苻容继看不清父亲的表情,读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快睡吧。”父亲说。
苻容继是被尿憋醒的,他躺在床上天人交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忍不住喊了出来:“爸爸。”
无人应答。
苻容继只好自己摸索着爬起来,小声地呼喊着试图寻找着些依靠:“爸爸……”
客厅没有人,厨房也没有人,浓稠冰冷的黑暗里,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更衬着这份诡异的静,静若废墟,仿佛入了无人之境。
苻容继来到阳台,呆呆地抬着头站了一会,月明星疏,银光如洗,极亮但又偏偏冷得渗人。
他不由自主地就打了个寒噤,一股莫名的恐慌从心底里冒了出来,他跌跌撞撞地迅速跑回房间躲进被窝,就好像只要慢了一步,角落里的魑魅魍魉就会扑上来撕碎他般。
他没敢从阳台上往下看,其实他一低头,便能找到自己的父亲了。
他的父亲正躺在楼底的地上,身下的血沿着水泥板扭曲的纹路慢慢流淌,然后逐渐凝固起来,远处的路灯怜悯般地投过来几缕微不足道的光,照出一片惨淡。
冬日的夜晚冷极了,没人会发现他,他将在这儿躺整整一个晚上。
周遭都安安静静,悄无声息,月亮目睹了一切,但它守口如瓶。
有风吹进屋里,被钢笔压在茶几上的纸张簌簌地抖了几下,纸上写着的是遗书:
“余,数十年穷尽碧落黄泉,上下求索不得开解,今以此书与世永别,自省缘由,一负妻儿信任关怀却不自持,二恨自己离经叛道眷恋同性。
辜负信任尤可悔过偿还之,恋上同性却为原罪该万死……”
这一年,苻容继九岁。
再过7天,是他十岁生日。
第9章 【九】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母亲的精神逐渐变得有些不稳定。
戏剧院给了他们一笔钱并帮着申请了补助金后,辞退了母亲。他们母子二人便从原来的居民楼搬进了更加便宜些的平板屋里。
苻容继一边努力拿着奖学金,一边做着零散的兼职补贴家用。他独来独往,形单影只,即不敢交朋友也不参加活动,因为他付不起社交里所需要的任何一项费用。
孤僻,乖张,这样边缘化的人物原本是极不讨喜的,可偏偏苻容继生了一副好皮囊,态度生疏却始终礼貌,偶尔也会友好地笑笑,叫人无论如何也讨厌不起来。
“喂,你待会买一箱水搬到操场去,剩下的钱当你的跑腿费了。”有同学递过来一张红票子。
苻容继接了下来,买水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课后的兼职也赶得上。
今天是学校的篮球比赛,操场上人声鼎沸。
苻容继将水搬到后勤处,略带憧憬地看着比赛的少年们。
操场上,那是明媚的阳光也抵不过的热情,蝉儿嘶声力竭的鸣叫也被掩在了人群的呐喊声中。
有人突破防卫高高跃起,他手里的篮球划出了一个完美的弧线,稳稳地落入篮筐中。
“三分!”
“赢了,赢了!”
人群欢呼起来祝贺少年,他开朗地大笑着,一把脱了自己的球衣掷到半空中,惊起一片此起彼伏的高呼声。
许多后苻容继已经不记得少年的样子了,他只记得那少年汗津津的健康躯体,线条紧绷完美,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在太阳的照耀下,好像在熠熠生辉。
苻容继就那么怔怔地注视着,喉头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
当晚,他梦见了鬼魅。
被鬼魅压在身下的不是父亲,而是他自己。
天地都在旋转,星辰一颗颗从天上坠落下来,溅起万千火海,难耐的欲望从火里剧烈喷薄而出,借着鬼魅刺进苻容继的身体里,一层接一层地点燃了最隐秘难言的东西,激起密密麻麻的欢愉感。
苻容继醒来时,察觉到身下的被子湿漉了一片。
他呆呆地坐起,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俯身开始作呕,可是他什么也吐不出来。他抬手去擦嘴角,却擦到了满脸的泪。
他紧紧地抱住自己蜷缩起来,哽噎着泣不成声,揪紧的手指刺进了血肉,可是疼痛也盖不住满心的绝望。
他并不是什么都不懂。
他只是怕自己什么都懂了。
“2001年同性恋就从中国的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了,它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刘医生善意地看着他面前少年说:“所以你并不需要任何心理治疗。”
苻容继的脸色有些苍白,嗫嚅着没有说话。
“你需要的是正确地认识自己。”刘医生说:“你有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
“那我是正常的人吗?”苻容继问。
“你是,你当然是。”
刘医生笃定的态度让苻容继微微地松了口气。
“总有一天,你会遇见值得爱一辈子的人,即使他和你有着一样的性别,那也不妨碍你们相伴执手。在此之前,请积极向上地生活下去。”刘医生又说道。
苻容继点点头。
“这上面有我的私人电话。”刘医生递过去一张名片:“你若是有什么解不开的郁结,可以找我谈谈。”
“谢谢您。”
苻容继小心翼翼地收好名片,放到贴身处。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小雨,雨声淅淅沥沥,洗涤万物。苻容继坐在公交车上看着连绵不绝的雨滴落下来,没来由地响起了泰戈尔的那句诗词——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车窗的玻璃模模糊糊地倒映着苻容继的面庞,他对着自己温柔地笑了一下。
母亲的病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她甚至连苻容继是谁都无法明白地弄清。
高中的学业也给苻容继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精打细算着规划好剩余的积蓄,协调着兼职的时间段。
所有的困苦都砥砺着这个少年,将他的心智磨炼得愈发成熟。
高考结束后,他藏起了国内某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询问了刘医生精神病患者住院的治疗的费用及手续流程后,开始打工攒钱。
他十八岁生日那天,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公民。他以家属的身份在医院的确认书上签了字,送母亲去接受正规的治疗。
他获得了一份正式的销售工作,白天奔波在外,晚上摆摊卖卖夜宵,周末在小饭馆管管账赚点外快,所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着。
再然后,苻容继就遇到了杜若飞。
生活的轨迹好像有些不受控制地向预期之外偏离了一点点。
杜若飞对他说:“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你和我,天生一对!”
杜若飞问他:“我公司财务部这几天刚好缺人,所以我想问问你能不能来帮忙?”
杜若飞安慰他:“阿姨她今天唱的戏是中春秋亭避雨那一折,虽说情节跌宕波折,但是结局却是喜剧。”
杜若飞的偶尔态度强硬:“现在整理下东西跟我走,我去车上等你。”
最后,杜若飞说:“不如,你就把我这当作是家吧?”
苻容继蓦然睁大了眼睛,指尖不可察觉地微微有些发抖,他突然想起了自己遇见杜若飞的那一天。
那一天阳光微晒,无风无雨,当时的他还以为,那一天只是生命里最普通平凡的一天。
在遇见杜若飞之前,他已经独自行走了很久很久,甚至都做好了暮年孤老的打算。
其实孤单一个人并不是活不下去,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但如果有人愿意给他一个家,那就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苻容继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缥缈,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连尾音都在发颤。
“好啊。”他如是说。
下一刻,杜若飞展颜而笑,灿烂如阳。
晚饭毕,杜若飞兴致勃勃地自酒柜取出一瓶酒,又取了高脚杯,献宝似的斟好了递给苻容继:“Riesling的白葡萄酒,尝尝看?”
苻容继没有推辞,接过杯子抿了一口。
杜若飞问:“怎么样?”
苻容继喝不出个所以然,只好说:“挺好的。”
杜若飞笑着和苻容继碰了碰杯,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把一整杯酒喝完了。
但苻容继从小到大只喝过酒精度趋于无的家酿米酒,这一杯葡萄酒下了肚,还没几分钟他就开始觉得发昏。
“杜总,我……”
苻容继喃喃唤着,他想告诉杜若飞自己有些醉了,但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哐地一声栽倒了下去。
杜若飞骇然地丢了手里的杯子,赶紧上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