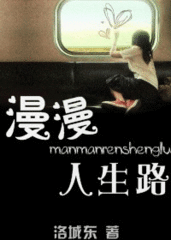混音人生-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一段漫长而柔软的沉默之后,我问他,好看么?
“好看。”
他说,“我简直想娶你。”
第126章
我说,娶啊,敢娶就敢嫁。
我也就现在有胆量说出这种话,有口无心,其实我对婚姻没有半点儿概念,图个嘴上痛快。他却好像当了真,虔心思考起这个问题来:“这可是你说的。”
“……你等等。”早知道不跟大龄儿童幼稚鬼开玩笑。
“我算算啊,”他眼睛往上瞧,一本正经地掰着手指头算:“旧金山那边是给扯证的,还有我当年读书那个地方……”
“别自说自话啊爸爸。”我用拳头轻轻一撞他胸口,“再等一年,好歹让我攒够老婆本。”
“那不叫嫁妆么,到底谁娶谁。”
“闭嘴,都一样。”
话都不说了,俩人就那么脸对脸站着,谁也不提进去的事儿,挺奇怪的。
因为在外面的时候才是“我们俩”,进了这个门就不是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小声问他。
“不是来骚扰你的。”他戴戒指的那只手摸了摸鼻尖,“待会儿老周得跟我走,把工作交接的事儿办妥。我打算给他批五个月的假……正好到十月过完,连结婚带生孩子一步到位。”
我赞许地:“想得挺周到。”
他很谦虚:“你眼光好。”
“……”
这个同时往俩人脸上贴金的套路有点过于曲折,以至于我半天没有领会到其中的精神,他直接推门进去了。
“打扰了——”
见来的人是他,原本在镜子前帮夏皆整理头纱的周靖阳放下了手:“少爷。”
我从镜子里看到夏皆披上婚纱的模样,揉了揉眼睛。
——记得小时候老师布置关于母亲的作文,孩子们总会以妈妈的外貌开头,“我的妈妈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乌黑的长发扎成马尾”,我从不缺乏描述她的修辞,此时此刻却只觉得词穷,腹中空空,无以言表。
她转过身来,提起层层叠叠的蓬松裙摆和宫隽夜问好,“来啦。”
时至今日,他在她眼里已经不算是生人,早些年的可怕印象有所改观,再加上我失声那次他确实帮了大忙,也就被我妈视作同圈好友,丈夫的上司和儿子的“大哥”。
“刚才是谁打来的?”
“网站那边。”
“哦……你觉得怎么样?”
我回到她身边,和她站进同一面镜子里,调整手脚摆放的姿势,许久才说出一句,很美。
她问我,你说这身婚纱吗。
不,我是说你。
后来她试穿完毕,看腰围处显示仍有富余,叫她再过一个月穿起来也不必担心,她便由周靖阳陪着去里面的房间把婚纱换下来,我这边还得试个领结,不知是条纹的还是印花的搭配出来效果好,老板干脆拿了好几种让我挨个儿试过去,老板娘过来帮忙,她熟知每种领结的打法,这样节省时间。
就在这个猫一样姑娘用她娇柔的手指为我翻弄衣领时,我听见她的笑:“嗨呀,那家伙盯着你连眼睛都不舍得眨,我都看累了。”
我不回头也不看镜子,把我看中的那只领结交给她,放进丝带装饰的纸盒里打包。
“那你去休息,”我也笑,“我替你接着看。”
服装的事情敲定了,接下来还有来宾和场地等等问题需要解决。依他们俩的意思,婚礼没必要太繁琐,走个形式而已,大家见证过、然后痛痛快快的吃喝玩乐就行;邀请的人也不用太多,是双方关系最近的亲友,礼金更没要求,只要人肯来捧场就好。
我也认为这样很棒,亲自去通知了何故和费娜。两人得知此事的反应各不相同,相比同为女性感情细腻的费娜,何老师这位铁汉柔情的男子反应尤为激烈,他拿到那张我亲笔书写的请柬,想笑又不敢笑,用一种让人听了就想打他的语气说:“真敢当宫少老丈人啊,厉害了我的哥……”
没有司仪没有奏乐没有接亲游戏,场地直接安排在了一家露天的花园式餐厅,到时候把桌椅挪到室外,仪式就在草地上举行。
如此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月,夏皆的婚礼如期而至。
那天我比闹钟起得还早,洗了澡修了眉毛,穿戴得当,提前两小时去餐厅等候客人。
不多久何故过来帮我的忙,接待了几个周靖阳的同事,也都是宫隽夜那边的人,多少都认得我,碰了面嘻嘻哈哈的打趣一阵,份子钱随得很厚。
费娜和栗子阿姨在给我妈化妆,宫隽夜和周靖阳开车去接人,赶到餐厅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半。
十二点整,婚礼开始。
之前我们跟餐厅的工作人员商量好,对草地上一个白色的凉亭稍作布置,让新郎新娘在那里交换戒指,从餐厅大门到亭子之间的这条路就由我牵着夏皆走过去,直到把她的手交到台下的周靖阳手上。
“妈。”
我和她站在屋檐下,她挽着我的右手臂,我的左手搭在她手背上,隔着白色蕾丝手套抚摸她凸起而坚硬的指骨。
“你紧张吗。”
这次她没有回答我。
我想不管是什么东西,一旦人习惯了等待,在得到的时候都会双手颤抖吧。
当“结婚”这个念头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它就不再只是孤独时心理安慰,一个人逛家具城时的触景生情,或是面对他人出双入对时的自卑和赌气。她想要结婚。
她最擅长的洒脱仿佛陡然间丧失了使人信服的能力,变成了狼狈的出尔反尔。曾因为独立而骄傲,把情情爱爱看作辛苦生活中必须摒除的弱点,哪想得到未来会遇见一个让她宁愿违背誓言放弃原则的人。
其实谁会怪罪她的反悔?
“我愿意”是一句多么动听的话。
我牵着她的手,正如她曾牵着我的手,她把我交给苦尽甘来的漫漫人生,而我将把她交给一个托付终生的人。
直到那个男人的手取代我的手,我退后,怀里抱着她的捧花。初夏的天空一碧万顷,阳光透明得像琉璃,照得人睁不开眼,我远远的站在她身后处,幽蓝色的影子落在草地上,被风吹得飒飒轻响。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证婚人不是别人,正是周家父母,那段诗一样简短有力的誓词我一句都没记住,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交换戒指,相拥的身影被人群的欢呼和抛洒的花瓣所淹没,这的确是一场迟到了许多年的婚礼,幸运的是,他们依然得到了最好的祝福。
这就是结局。
我却无法阻止某种突如其来的悲伤痛击我的胸口,在香槟开瓶声中我滴酒未沾,如鲠在喉,抱着那束红得扎眼的花,难受到无以复加,转身拨开背后像鸽群一般聚拢在草地上的宾客,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其实我早该想到,终有一天我会失去她。
作者有话要说: 我不行了太几把困了,睡一觉起来再出柜吧
第127章
她似乎发觉到我的逃避,从举杯庆贺的宾客中喊了我一声,那声音像一朵小小的浪花,顷刻间便被海潮般的风抹平。和所有的快乐与祝福相比,我更希望她不要发现我——我为这份微不足道的矫情感到羞耻,它暴露了太多我至今不愿承认的软弱——在这个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婚礼上。
可我等不了了。
我走向站在树下的男人。
我早就看见他,在我想要逃开的路上,他和我一样远离热闹,却不像个被冷落的人。他从来都不是被冷落的那个。他只是拥有一种本领,一种永远能够在我无处着落的时候、给我一个温暖的巢穴让我藏躲的本领,只有他有。
他身上的衬衣是我熨的,香水是我挑的,手机里最后一个电话是昨晚拨给我的,我在懵懂年少时仰慕他,尝他抽过的烟,写关于他的歌,我仍记得他十九岁时的模样,又在他痛失双亲的那天与他邂逅一面,却背对他跑往相反的道路,兜兜转转许多年,终究回到那个没有听众的酒吧里,不可自拔的爱上了他。
他说我会给你一切,而你要挺直了腰杆好好的活。
他说好吧听你的,等你攒够钱了来娶我。
我陡然醒悟,我一秒都不能再浪费了。
“妈妈,很抱歉我现在才有勇气告诉你。”
我望着身披婚纱追赶来的女人,那把那束玫瑰塞进宫隽夜空出的臂弯里,绛红色的花瓣簌簌散落,我知道在西式婚礼上人人都想抢到这束花,因为新娘的花捧代表了爱情的赠与,接住它的人会受到爱神的眷顾。
我颤抖地抓紧他的手。
“这是我喜欢的人。”
也许是我抖得太厉害了,让他错将这份冲动解读成了不安,以为我渴求他的扶持,下意识的把我的手包裹在了掌心里。
夏皆睁大了眼睛。
“我想给他一个家。”
我设想过种种障碍,和有可能遭遇到的质问,甚至是打骂,在我还没有充分准备说出这被我掩盖了快两年的秘密的时候。然而当我在不计后果的冲动主导下说出了口,大脑放空如同飓风过境,思考跟上了本能的速度,弄明白自己告诉了她怎样的现实,整个人就被负罪感死死钉在地上,动都动不了。
我早不说晚不说,偏要这个属于她的好日子里给了她当头一棒,我他妈到底干了什么?
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低头看着她从裙摆下露出的白色软皮鞋,她的手用力攥住裙子上一簇簇的白纱,像是要把它们撕碎,目光飘忽地对上宫隽夜拉着我的手,我却不想松开。
无论如何都不想。
她说,已经很久了,对吗。
“是。”
宫隽夜代替我回答:“到下个月就两周年了。”
我看了一眼他沉静如水的脸,又回头去看夏皆。
“这样啊。”
她的手指放开了,好像丢掉什么让她烦恼的负担,嘴角弯曲的线条变了几变,最终化作一个朦胧而微酸的笑:“……挺好。”
所以呢?
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周靖阳走了过来,他身后是一脸欲言又止的何故,他或许猜到了这边发生的事情,于是主动放弃了介入的话语权。我知道在所有旁观者里,他是看得最清的,他知道有些事儿外人插不了手,所以压根儿没试图去说服和纠正。
他能做的只有和周靖阳一块儿扶住夏皆的手臂,说,起风了,披件衣服吧。
她把他们都推开,问我,夏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我说我知道。
“我对得起自己的心。”
她怔了怔,接受了之后短暂的沉默。
“那就好。”
她深吸了一口气,竭力将那画得精致的眉毛舒展开,双手合拢在胸前,肩膀耸动,就像开心地拍了一下手。
“希望你下次回来,能跟妈妈讲讲你们俩的事……”
我站不住了。
我想象不到她在刚刚那两句轻描淡写的话里吞咽了多少原本令她无法接受的内容,也想象不到这囿困我两年的心病能以这种方式被切除,过程很仓促,感受也不够真实,但我知道我不能继续站在这儿什么都不做,连再见都说不出口,拉起宫隽夜就要离开,他却反握住我,坚持说完最后一句。
“谢谢你。”
他的手指张开,复又包裹住我手掌的轮廓,微微欠身向她颔首,几乎是郑重而恳切的。
“新婚快乐。”
他把那束花带走了。
这场婚礼只有我们俩提前退出,出了餐厅是一片广场,阳光照耀着铁黑色的雕塑,浓绿色的树荫繁茂而安静,哪怕正午时分路人寥寥,我穿一身白他穿一身黑,手里还抱这么一大束玫瑰花,看着还是让人误会。
起初是我拉着他走,后来变成他拉着我,用跑的。
“去哪儿!”我在后面问他。
“不知道。”
我猜他也会这么说,所以心中没有丝毫迷惑。
“那就走吧。”
“你刚刚。”
我们穿过蛰伏在绿荫里的石板路,长椅上坐着几个闲谈和遛狗的人,午时的暖风熏得人快要睡去,他突然转过身来,我没防备,跑得满脸通红撞在他身上,五月的玫瑰挤到我下巴底下,扑鼻的幽香让我眩晕。
“跟我求婚了。”
他声音不大,周围却依然有人看了过来,我干脆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是啊,怎样。”
他大概没见过有人出柜都出得这么死皮赖脸的。
“你不答应我可回去上学了。”
我勇敢地翻出白眼,腰又被勒紧了一点,心跳得快吐出来了。
“……实在是太帅了。”
嘴里说着只可能出现在十六岁纯情少女口中的话,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突然被他勾住膝窝打横抱起,他的嘴唇隔着花瓣重重的亲了我一下。
“我又爱上你了。”
我要爆炸了。
“去买戒指吧。”
“都说不用了!你败家不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