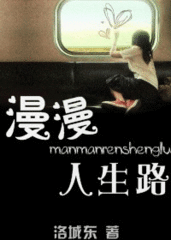混音人生-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垫的还是全班的底。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因为喜欢上了说唱,在英语上极其下功夫,收效显著;另一方面是对理科实在提不起兴趣,我难以抗拒数学课上阵阵袭来的睡意,物理化学之流背背公式好歹能拿个基础分,而对于号称照猫画虎就能求解的计算题,我是没有一点头绪,选择题连蒙带猜,命中率也是可怜。
我多少有点歉疚,尤其是当夏皆在家长会后回来、反过来安慰我的时候,那种无法回应对方期待的歉疚感更盛。
因为我打心眼儿里不在乎,不在乎成绩不在乎排名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每天塞着耳机做作业,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才是我真正觉得惭愧的。
必须做点儿什么改变这种现状。
单科小测成绩下来的那天,十三岁的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被触发了对人生的思考。
放学后,我和李谦蓝行至护城河上青灰色的石桥,他校服外套搭在肩上,纯白色T恤服帖的勾勒出后背的弧线,他撩起衣服擦了擦脸上的汗,不以为意地,“让你同桌教你啊。”
——哦,差点忘了,年级第三就坐在我旁边。
我并不了解乔馨心这个人。
她肤色很白,穿衣打扮干净讲究,像个一丝不苟精密周转的机器,日常生活里好像没有任何多余的节目,听课,学习,看书,课间会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不跟那些话很多的女生一起结伴上厕所,偶尔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嗓音透着一股病态的空灵。
虽谈不上拒人于千里,不易接近也是肯定的。
可我从小到大有过深入接触的女性也只有我妈而已。
这个岁数的男孩儿女孩儿是很爱起哄的,但凡谁想要搭讪和示好,大家便会对这种心知肚明却不宣于口的“禁忌”表现出一种别扭的期待;若是班里真有那么几对“谈恋爱”的,那就天天都是现场直播,舍己为人地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
所以尽管我想说的是“你能给我补习数学吗”,也像是可笑的告白一样开不了口。
不过很快我发现,我们俩有个难得的共同点,就是在晚自习塞着耳机做题。
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学校曾明令禁止各种电子产品的携带——当然是没用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一套条条框框的规矩,但还是能被机智勇敢的同学们钻空子,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而晚自习就是大家解放自我的时刻。在老师看不到的地方,聊天的,看课外书的,吃东西的,传纸条的,玩手机的,甚至还有在后排打扑克的,白天在老师面前的一派沉沉死气荡然无存,好像天一黑就现了原形一样。
连乔馨心这样的好学生都会一边听歌一边学习,像她这种教科书般的优等生,已经算是很出格的事情了。
也就是这一天,老师布置了必须要在晚自习结束前完成的作业,并请了课代表去讲桌上坐镇,谁写完谁才能回家。庞大的习题量惹得人心惶惶,聊天的没工夫聊了,打牌的没心情打了,一时间教室里只剩下奋笔疾书的唰唰声,听得人心里发慌。
乔馨心依旧塞着耳机听歌。
然后还是全班第一个交的作业。
在一个我认为正常人难以企及的时间段内,她搁了笔,摘下耳机站起来。
全班人的脑袋都跟向日葵似的围着她转,时不时还听见窃窃私语声,我几乎可以想象到谈论的内容和语气。可我的关注点是她放在摊开的书本上的两只耳机。
黑色的索尼,看上去价格不菲。
由于周围过分安静的缘故,近距离下的我听到喇叭里传出高昂而激烈的破碎声,好像硫酸一样带有某种诡谲的侵蚀性,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乔馨心交了作业从讲台上下来,她伸手把及肩的黑发挽到耳后,面孔清秀,步伐从容。
等到她落座,我想都没想就无比自然地问出口,“你听的是……摇滚吗?”
教室的白炽灯下,她缺乏血色的手伸展开了搭在书页上,闻声微微侧过脸,烟灰色瞳孔落拓的望着我。
我竟然从中看到了一些慑人的冷光,比沉默更惊心动魄。
“是Acid Rock,迷幻摇滚。”她轻声说,“还有黑金属。”
——那之后的许多年,我在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都必定要听听他耳机里的秘密。是情歌还是民谣,是乡村还是朋克,音乐是人心的横截面,剖开他的爱他的痛,他的追求他的过往,他所有不可言说的暴虐与温柔,只有喜欢的歌绝对不会说谎。
我全都听得见。
第9章
期末前的最后一次数学测试,我以险险超出及格线五分的战绩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万众期盼的周五下课铃打响之后,我把卷子折了两折夹进数学书里,整理好课桌和书包,一抬头,已经有两个人在外面等我了。
——从我这个角度恰好看得到靠在墙上的乔馨心,她深蓝色的手提书包背在左肩上,双手插在稍长的秋装外套口袋里,让人觉得她可能很冷。她一句话都不说。
而她对面的李谦蓝,自打站在了门的另一侧,俩眼珠子在就奋不顾身的扑在了人家身上,又不敢看得太放肆,情到浓时反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走在他俩中间的我也着实不算个适合谈笑风生的对象。
所以就是三个闷逼。
“……”
事情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一个月前,李谦蓝听说我成功抱到了学霸的大腿,愤愤不平的表示这也行?“女神也太过容易攻略了,花式搭讪到这儿完全派不上用场啊。”
“排除我是用美貌征服她这一点,”我说,“我数学是真的差,实事求是。”
他闻言沉思了半晌,“……不然我下次英语交白卷吧。”
我难以抑制内心的鄙夷,朝他翻了个空前绝后的白眼,“你不如当着女神的面把自己腿打断,她还可以去医院照顾你。”
这下李谦蓝也沉默了。
我怀疑他真的在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
我痛恨在他缺少智慧的情况下还如此没有勇气与魄力,于是自作主张的同时把俩人约出来,到了学校外面一家很受欢迎的小店里一起吃甜点。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已经能和乔馨心像普通朋友一样正常交往,起初她除了在每堂数学课课后给我讲解知识点以外,并不做无趣的寒暄——而这正和我心意,我也不跟她说废话,顶多偶尔聊聊音乐。
据说她父母都是老师,母亲教舞蹈父亲教音乐,含金量相当高的双亲组合,还有个哥哥也是在读艺术生。在这样富饶的成长环境下,她也走音乐道路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是,她抛弃了最符合形象的古典音乐,迷上了摇滚。
包括我也为这种和本人相距甚远的爱好感到惊讶,细细想来,却觉得十分有个性。
她待人也诚恳,做事认真,只是言语不多,现在专注于面前的一份芒果班戟。我脑袋空转着,看到这家甜点店的老板走到我们桌前,往对面的墙上张贴着什么东西。
店老板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穿涂鸦图案的T恤,染了一头姹紫嫣红的头发,正吹着不成调的口哨,将一张海报铺展开。
我注意到身旁俩人现在跟我一样,都抻长了脖子去看那卷起的边角逐渐露出来的大字。
“乐队个演。”
李谦蓝“啊”了一声,转头看我,“你听过这个乐队么?”
我摇摇头,而我身边的乔馨心点了点头,“知道。”
她放下勺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抽出一张湿巾擦拭手指,做了个“多谢款待”的手势,说,“是这边的地下摇滚乐队么?”
这次接过话头的是年轻的店老板,他转过身来神采奕奕地一拍巴掌,“嘿!这你们也知道啊!”
我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没什么插嘴的余地,只得低头继续对付剩下半杯冰淇淋球,耳边还听着他们的对话。“就明天晚上,在四号大街的破晓酒吧,因为是组队的周年庆所以不收门票,八点开始……不过你们几个小孩子嘛,建议找个大人或者结伴儿去。”
“怎么?”
“怎……?”店老板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嘴里支吾着叼上根烟,“那帮玩儿音乐的厉害是厉害,就是乌烟瘴气什么人都有,看你们小,想去看还是注意点吧。”
店老板这一席话给了我格外强烈的画面感,我眼前登时虚构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景象,全是从电视剧里抠出来的:几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表情颓废眼神沧桑,身上能抖出一片撒哈拉大沙漠,扯着嗓子在台上又蹦又叫,台下的人跟嗑了药似的,群魔乱舞,忘乎所以,好像下一秒就是世界末日。
这是多么酷的一件事啊。
——站在那样的舞台上,看下面的人跟着你疯狂,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先是没说话,抬眼想看看李谦蓝和乔馨心的反应;原来我走神的时候他们已经凑在一起说话了,我很震惊,但这也是意料之中,只见李谦蓝就像一个罹患口吃多年的病人忽然回了春,不晓得说起什么,满脸迫不及待的激动。
他问我,夏息,去看吗?
我手里的勺子“叮铃”一声滑进杯底的奶油里。
“啊,行啊,去。”
说这话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眼乔馨心,她两手交握着,嘴上依然没说什么,瞳孔里却有一点点不明显、但足可看透的雀跃,她好像真的很想去。
想想刚才店老板说的话,我懂得李谦蓝的意思:怎么可能放这么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姑娘一个人去呢,我们俩怎么说也得做个陪客。
是男人都会有这样的自觉。
我也没再多犹豫,直接答应下来。“明天晚上七点在学校门口碰头。”
“嗯。”
夏皆得知我要跟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写了一脸的高兴。
我知道我在她看来比同龄孩子多出一种阴郁的气质,不够开朗天真,从小就没什么玩伴,她会将责任一股脑儿的揽到她自己身上,这让她不安,甚至于难受。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同情过自己,或者说,对既得的事物没有任何不满。
但是看她开心,我也很开心。
这种开心一直持续到我们三个在学校门口汇合。
两男一女这样的组合不管在什么场所都有点怪异,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假装对此浑然不觉,其实心里也是坦荡的。
晚饭都是在各自家里吃的,我们走在路上说起来和家人打招呼的问题,我和李谦蓝两个男生不怎么需要操心,乔馨心倒是有点难为情的表示,只敢和哥哥说自己跑出来听演唱会。
“因为父母讨厌我玩摇滚,这是肯定的。”她叹了口气,“我还要花许多时间让他们接受。”
“我爸妈也还以为我要当学者呢。”李谦蓝一本正经地说。我扯着一边的嘴角配合地笑了笑,心想,我还没敢告诉夏皆我要当歌手这件事。
在我妈看似离经叛道实则稳妥保守的世界观里,玩儿音乐的人逃不开两种结局。
一个是天桥摆摊卖唱,一个是下乡慰问演出。
真是想想就酸楚得不行。
我不愿花太多时间想这些让我头痛的未来,因为眼前已经走到了酒吧的大门口,一束雪亮的灯光投在我脸上。
第10章
始一进门,我的魂儿就好像被什么东西从眼皮底下正大光明的偷走了。
回过神来,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勾头缩脚、年纪轻轻的烟鬼,暗哑的灯光把他们的身影照得宛如妖魔,门里人影幢幢,正放着开演前的热场音乐。我和李谦蓝把乔馨心夹在中间,嘴里客客气气地说着“借过”从他们身前走进去,但仍感觉得到流连在我们身上的视线。
里面没有路,只有人与人之间狭小的缝隙。看来这个乐队的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我按着李谦蓝的肩膀竭力寻找着主角们的身影,被来往的女人撞了好几次,她们纷纷回头,手臂上纹着妖艳的纹身。
我胳膊忽然被人捉住,是那种曲起肘部、不容置疑的动作,女生手臂纤柔,力气却大得吓人,直接把我和李谦蓝从人群密集处扯到一块稍微有些松快的空地上。
“看那里。”
乔馨心的声音整体比环境低了八度,能够轻易从喧嚣的叫喊声中分辨出来,我环顾四周几乎看不到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净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有四十多岁眼神不善的古怪男人……李谦蓝拍了一下我的后背,让我往台上看。
我踮起来的脚自始至终就没挨过地面,前面时不时有人举起手机录像,我需要不停地变换站立的角度。
我看清楚站在台上的是五个人,一个留着清丽短发的女人,一个人高马大的胖子,键盘手贝斯手鼓手都隔绝在灯光外;胖子说话带着浓郁到不可能误会的北京口音,笑起来有种心宽体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