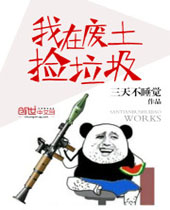废土与安息[第一部]-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废土干巴巴道:“不想做,走开。”
安息的鼻尖从他下巴一路蹭到耳边:“别啊,来做嘛,怎么做都行,给你内射。”
废土生无可恋道:“不要,我要去内射别人。”
安息噗地笑出声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废土撒娇式地发脾气,情不自禁摸了摸他的脸颊,把他略微长长的头发拨到耳后。
“以后去了虚摩提要把胡子留回来,不能这么帅。”安息说。
废土斜眼看他:“有胡子不帅吗?”
安息亲他下巴,又亲他嘴角,废土十分不配合地抿着嘴唇,冷着脸看他扒在自己身上亲来亲去。
安息撩起他衣服的下摆,啄了啄他的腹肌,又吮了一下他的乳头,被废土一把按住额头:“干什么你,别毛手毛脚的。”
安息把手放在他裤裆上,抬起眼自下而上看着他:“都硬了。”
废土语气也硬邦邦地:“我乐意硬着。”
安息只觉得他闹脾气的样子既幼稚,又可爱极了,将脸埋在他小腹下方隔着裤子舔了一下——几乎是瞬间,那里就又涨大了一些。
废土抵着安息额头的手变成了揪着他的头发——安息在床前跪直身体,将废土的阴‘茎掏出来捧在脸前,一手握住柱身,鼻子埋进毛发里,从根部一路舔上来,舌尖在圆头上画了个圈,又舔舐起柱身下面的肉棱。
废土爽地“嘶”了口气,一手捏着床沿,一手揉安息的耳朵。
安息原本就没怎么做过这件事,但废土兴奋的性感表情伴随着喘息声刺激着他的五感,叫他忍不住拼了命想要去取悦这个男人。
他来来回回吞咽舔舐,直到下巴酸痛,口水溢出嘴角,才叫废土射了一次。
他把射过后半硬的阴茎清理干净,放回到裤子里收好,带着恶作剧的笑容和精液的气息朝废土索吻。
再见啦,闭上眼之前,两人都在心底说。
隔日清晨很早的时候安息就醒了,他看了天花板很久,才敢转过脸去看隔壁的床。
上面空荡荡的——被子叠得一丝不苟,床单也拆下来了。
他机械化地撑起身体——墙角的远行包也不见了。
他有些茫然地左右看了看,发现自己枕边有一张字条。
安息打开来,这次里面只有一句话:
这次离开的是你,扯平了。
他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摸出胸口的小包,把字条叠好,和废土曾经在山顶休息站留下的条子放在一起。
第四十章 独立日
安息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才意识到屋里实在太过安静了——没有废土,医生也不知在哪,世界被隔绝在两步之外。
他慢吞吞地挪下床,拉开活板门顺着梯子爬到地下室——这里和昨天还是一模一样的摆设,冯伊安的床铺未动,甚至他随手搁置的水杯都没变过位置。
安息心里有点纳闷,一边刷牙一边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精打采地,眼神空洞又茫然。
简单洗漱了一下,安息饭也没吃,就锁上门出去了。
天地无情,今天的废土之上仍是晴空万里,一丝微风也没有,他有些恍惚——一切都变得有些陌生,好像自己是第一天见到这片焦土似的。
安息先是来到集市大门口的管理处,找轮班的守门人领了钥匙——定金是冯伊安垫付的,说是刚好抵这几天帮他看店的工钱。安息捏着钥匙,仔细研究管理处门口的大地图。这个地图很明显不是一个时期的作品——集市的老三区绘完的时间最早,已经被风沙和酸雨腐蚀得颜色较旧,外围的几个区颜色较新,安息即将要去的E区颜色最鲜艳,像是刚订上的。
在不远处的集市大门外,电网那头不知今日为何特别吵闹,里外围了好几层嘈杂嗡鸣的人头,空气中飘散着一丝不安的味道,像是铁锈混合着消毒液。可安息此刻没有关注热闹的心思,只远远看了一眼便离开了。
他按照地图指示的方向穿越番城市场而过,一路走过各式各样的商铺,看着摊子上的防砂靴和过滤芯,又看着摊子后面的一张张脸,忽然间,他们的脸都变得模糊起来,好像被高温的气体给扭曲了,变成了浑浊空气中的黏着分子。
安息越走越快,脚步控制不住地几乎要奔跑起来——他觉得身体周遭的空气实在太干燥了,拼命吸收着他体内的水分。然后他意识到了,模糊的不是人们的脸,模糊的是他的眼睛。
安息猛地刹住脚步,站在原地急促地喘气,他低下头——黄土上出现了几个湿润的斑点,但转瞬间就蒸干了。
他缓缓地呼出肺里的空气,胸口渐渐平息下来,于是继续迈开步子。
今日的地球引力似乎格外强大,一声不吭地把安息朝地心拉扯,叫他每一次迈步都无比沉重。他照着越来越稀少的标识费力地寻找着E区,到了E区后,又晕头转向地试图定位98号房。
番城集市不愧是废土上第一大城,新区的避难房都长成一个样,安息终于成功地迷路了。
集市延伸到这里已经十分荒凉,此刻日头正盛,人们大多躲在室内,安息走了二十分钟愣是没找到一个能询问的人。他已经满身是汗,头发黏在额头上,喉咙发干,舌苔快和上颚黏在一起。
安息余光忽然捕捉到一个人影,他连忙快速朝着那个拐角跑去——那人在烈日下却穿着一身黑,层层围巾裹在兜帽外面,像旧事宣传册里的死神。
安息一下有些退缩,但想到不知下次遇到路人又得是什么时候,只能做足心理建设,克服恐惧,迈出独立日的第一步。
“你好!”安息叫道。
可那人像是没听见一般,连脚步都没停。
安息又更大声地叫了一次:“你好!”同时快步追上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次陌生人终于停下步伐,缓缓地回过头来,露出了半张脸。
之所以是半张脸,是因为那颗头颅上,确实只有半边脸。
另外的半脸肌肉萎缩凹陷,像是被强酸还是烈火侵蚀过,依稀可见头骨的形状,仿佛大白天见了一具骷髅。
安息膝盖一软,差点没站住。但他还是努力捋直了舌头,问:“请问,你知道……”
对方仅剩的一只眼上下滚动着,分明是在从头到脚地打量他。安息的生存警报霎时间哔哔作响,背后汗毛倒立,在大热天出了一身冷汗——他忽然意识到,如果问了对方门牌号怎么走,不就变相告诉了别人自己住所的地址吗?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安息大喊一声,转身逃了。
跑出一段路后又拐了几道弯,安息又快走了几步,回头数次见身后确实没人才停了下来。他背靠着滚烫的铁皮——一个租屋的外墙,惊魂未定,同时有些得意——如果废土知道了,会不会夸自己反应快、有警觉意识呢?
可他同时也意识到——废土不在这里了,等他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忘了这件事,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得到废土的表扬了。
再说了,废土在这的话,怎么可能叫他一个小时连一个门牌号都找不到。
安息摇了摇头,甩出几滴汗珠和几丝沮丧,
这种四四方方的集装箱状避难屋根本就没有房檐,太阳又悬在头顶正上方,大地上一点阴影都没有。安息把汗水蹭在手背上,又在裤子上抹了抹。
他抬起头眯着眼眨了眨——几滴汗水浸到眼睛里了,他面无表情地扫视着这一座座铁盒子熠熠反光的外皮,瞳孔慢慢睁大了。
单数,隔壁也是单数,这一排的屋子门牌全是单数,安息恍然间精神起来——自己的屋子是双数,从进这个区时的分岔路开始就走反了!
安息这次照着号数递减的方向摸索回了E区的入口,朝着丁字岔口的反方向看去:2号房,4号房……
十五分钟后,他终于来到了门牌98号。
安息租到的是一个可以算是简陋的单间——没有窗子,只有一个床和一张桌子,连凳子也没有,地上一层灰,十分像他和废土离开避难站时落脚的第一个休息站。
这样也不错,安息想——这就是我的起点了。
安息在屋子里走了几圈,随即意识到这里面积实在太小了,天花板也有些低矮,只得坐在床上开始盘算——先继续在医生的摊子里帮忙,摊子客流量挺大,可以做一块宣传招牌摆着,看能不能从帮邻居们维修家电开始,也试试帮过往商队升级武器。反正有医生的脸做招牌担保,希望能先凑上第一个月的租金。
安息又环视了一圈屋子——没有洗浴室,也没有通水管。他暗自打算着等回去医生那里把东西都搬过来后,首要任务是找到E区的公共浴室和净水供应站。
安息抿了抿干燥的嘴唇,深吸一口气从床上站起来。
回去的路途比来时快了很多,安息回到冯伊安屋门口正要开锁,门却从里面被大力推开——冯伊安从里面冲出来,和他照面之下也愣住了。
安息从没见过冯伊安这个表情。
冯伊安不复平日喜笑温和的样子,面上十分严肃冷硬,问:“你跑哪去了?找你半天!”
安息茫然道:“啊?我,我领钥匙去租屋了,正准备回来拿东西搬过去。”
冯伊安脸色不太好看,拉着他说:“别管什么东西了,快跟我来。”
冯伊安人高腿长,安息几乎要小跑起来才能勉强跟上他——他喉咙冒烟,到现在也没喝上一口水,但却不敢插嘴。冯伊安一路来到集市正门也没停下,直接带着安息来到电网之外——早先在这看热闹的人已经退散了一些,安息这才看到里面的场景——今日无风,黄沙还未将满地的血迹掩盖起来,反而结成了一坨坨暗红色的块状,按照这出血量来看,绝不止一人重伤。
安息觉得脚下踩到了什么,移开鞋子一看,竟然是半片人耳。
他踉跄地后退几步,这才想起来之前闻到的气味是什么——是血腥和死亡的味道,是皮肤被枪眼烧焦、是骨头被重挫击碎的味道。
冯伊安已经走出好几步,发现安息还站在原地一脸空白地盯着那些血迹,解释道:“你还记得昨天需要做手术的那个伤员?我们做完肢位缝合手术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才送回到伤员集散大棚里。但是那里条件很差,你也知道的,病毒细菌浓度又高,到了晚上他情况就开始不稳定,我就留在那守夜了。”
安息有些惊疑不定地点了点头,不确定这对话要走去什么方向。
“今天早上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大棚里忽然抬进来两个人,”冯伊安说:“我本来没注意,但他们穿着太过明显——红色的披风。”
雅威利赏金团!安息一下有了不好的预感,昨天和火弗尔正面冲突的场景浮现在了眼前。
“于是我去问了问,才知道早上外面有两拨人起冲突,在集市门口就打起来了,但具体怎么开始的大家都不太清楚……于是我就去案发现场看了看,结果找到了这个。”
冯伊安递过来一块灰黑色的电子屏幕,安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废土的天气气压仪,屏幕被子弹击穿,上面蛛网密布。
安息颤抖着接过来——不可能的,也许只是相同的型号呢?
他把屏幕翻成背面——那里有一块独一无二的白漆,安息手一松,气压仪掉在地上,屏幕彻底碎了,无数晶莹的细屑散落开来。
“他人呢?他还好吗?”安息失声叫道。
冯伊安摇了摇头:“不知道。”
安息心脏骤然缩紧,提到了嗓子眼——不是才重伤恢复吗?不是才好手好脚地离开吗?不是终于要去梦寐以求的虚摩提过不再提心吊胆的生活吗?为什么才半天时间,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安息又觉得无法呼吸了,他胸口大起大伏,带着哭腔问:“什,什么叫不知道,米奥肯定没事吧?他不是,他不是可以很快复原伤口吗?不是不管多严重都能愈合吗……”
冯伊安打断他:“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不知道米奥怎么样了,他不在这,不止他,整个雅威利赏金团也都不见了。”
安息屏住呼吸:“什么意思?”
冯伊安看了看他,掏出一块布把气压仪裹起来收好,拽了拽他袖子示意他跟上:“送进来两个雅威利队员,一个撑了没一会儿就不行了,另外个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但伤得也很重,估计是断定他必死无疑,才把他留下的吧。”
安息又再一次回到了这个恶臭闷热的伤员帐篷里,他看着病床上的人——那是一张过分年轻的脸,面色苍白,嘴唇毫无血色,眉头紧紧皱着,在昏迷中经受着不去的疼痛。他的红色披风上有些颜色更深的部分,想必是染上了鲜血。
他破碎的衣料下面,从胸口到腹部再到大腿全都裹着层层纱布,绑结的方式是冯伊安的手笔。
冯伊安说:“等他醒来,就能问问他知不知道米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