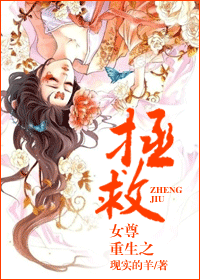拯救男二-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了会儿,沈寄一直沉默不语,垂着头,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
徐南柯问道:“沈小寄,睡着啦?”
沈寄脑袋顿了一下,似乎是惊醒,道:“没,师兄,怎么了?”
徐南柯便道:“你倒是说话不算话,不是说好了,等我回来和我讲你的身世。来说说看,今日江诗河都和你说了些什么?”
沈寄沉默了下,才捂着嘴咳了声,开口道:“上次无凛提及沈若云时,师兄也在场,我当时并没有以为然,心中却想,沈若云不是鼎鼎有名的清元派前任掌门吗,传闻中以一己之力合并几大门派,还研究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仙器,这样厉害的人,怎么可能是我爹呢?”
原剧情里,沈寄一出场就是在侯府遭受不公平待遇,却没有介绍他亲娘到底是谁,只是说侯爷不喜这个儿子,原来这里竟然暗含了隐藏剧情。徐南柯打了六十八遍游戏,也是废柴得很,居然还没有打到这一关,就让沈寄死掉了。
只是这样一想,倒是非常符合原剧情的尿性,据他所知,男主角的身世可是另有来头,绝非孤儿小乞丐那么简单。既然如此,身为第二个男主的沈寄,身世怎么可能没有玄机呢。
若是沈寄是沈若云的儿子,那就说得通了。
只是他怎么记得清元派前任掌门沈若云最喜欢研究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其中还有个什么叫做什么凤的……徐南柯没有细思,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沈寄脸色有几分苍白,又觉得他刚才那话似乎带了几分自嘲,想来应该是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真正身世,便安慰道:“沈若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现在已经元婴期,马上就要比他还厉害了。”
沈寄垂着头,声音中听不出什么情绪,淡淡道:“那是自然,至少我不会和他一样。江诗河与沈若云是多年好友,虽然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倒是和江湖传言差不多。”
徐南柯被引起了好奇心,道:“怎么?”
“他和我说,沈若云与他当年约定同时突破分。神期,他成功了,沈若云却失败了,于是郁郁不得,后来走火入魔受到反噬,变成了个病秧子,心中更无法接受,于是抛弃妻儿,从此不见踪影。一连多年没有出现,后来江湖上便以为他是死透了。”
若是抛弃了妻儿,也实在太可恶了些。沈若云的妻子不过是普通凡人,自然要寻找其他活下去的法子,还不知道在凡间活得怎么狼狈呢。或许后来实在熬不下去,匆匆将孩子丢给富贵侯府某个小妾,也说不定。
这就不得而知了。
徐南柯见他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评价起亲生父亲,心中也有点百感交集,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毕竟他也是一介孤儿,根本连父母的面都没见过呢。
徐南柯有几次打游戏,都试图找出自己身上的隐藏剧情,找到当初生下自己的是何人。
但是根本找不到,游戏给他的设定便是没头没尾的。
谈起这些事情,氛围好像一下子变得低沉了似的。徐南柯感觉到沈寄心情有几分低沉,烛火曳曳,在他脸上落下一小片阴影,分明火已经很旺盛了,却还像很冷似的,不停拨弄着柴火。
徐南柯却并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沉默片刻后,笨拙地转移了话题:“你刚才说,你不会和他一样,是什么?”
沈寄又咳了声,压抑在喉咙里,忽而抬起头来,一双黑眸望着他,映着摇曳烛火,淡淡道:“沈若云不负责任,才抛儿弃子。我若是喜欢一个人,便求一生一世,这辈子,下一辈子,都看不进去别人一眼了。”
可不是嘛,徐南柯虽然看不清他神色,但也能想象出他一本正经的小模样,那感觉就好像瞧见毛都还没长齐的小兔崽子妄谈情爱一样,不由得忍俊不禁,轻笑一声。
沈寄过于死心眼了些,所以在原剧情里,才会因为得不到徐灵,因爱生恨,最终黑化。可这反倒是他的致命缺点。
盘算了下已经攒到了的七百分积分,徐南柯心头一动,近来剧情倒是一直在往前走,沈寄先是获得了灵丹、无凛的真气,此时又在江诗河的帮助下突破了元婴前期,应该是能提升很多爽度才对。可不知道为什么,积分始终涨势不大。
难不成,情窦初开的时间到了?
想来也是,光斩关过将拿到各种法器,却没收到后宫,有什么用?沈寄能爽吗?女性读者看着能爽吗?
但想到这一点,徐南柯不禁有些发愁,因为沈寄始终没有表现出对徐灵多看一眼的迹象,徐南柯几乎要以为他被魂穿了,又或是改变了性取向。不管怎样,这次回到清元派后,就该着手起给沈寄牵姻缘的大事啦。
但不知怎么的,徐南柯又有点微妙的烦躁情绪,就好像种了多年的一棵白菜,开始跑到别人的院子里去,要拱别人的猪去了。
作者有话要说: 待会儿还有一更,大约九点吧,修好后就发。
这两天和技术小哥测试得焦头烂额。不是有些读者反映前面1…18章有些混乱嘛,我咨询了技术小哥,研究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这部分看得很错乱的读者使用的是安卓版4。7。8。1版本,升级成4。7。9版本就行了。为此好像损失了好多小天使,我也没办法了。
但是他说其他读者都没有我这种现象,可能是我中彩票了吧。【笑着活下去,绝望。jpg】
☆、第30章 药王谷(四)
第二日,徐南柯的听力也稍稍下降; 听什么都听不真切; 朦朦胧胧的; 仿佛夹杂了很多噪音。眼神更是下降; 几乎看不清什么东西了; 只是能勉强辨认出几个黑影。
天还未亮,他醒过来,发现地上一团黑影; 应该是沈寄还未离去; 在地上铺了一层床单; 似乎还在熟睡。沈寄一向勤快; 从来都是四五更天就起来; 将一切都收拾好了,今日居然如此惫懒。
徐南柯估计他是昨夜太累了; 便没有惊醒他,便悄悄起床; 将自己床上的被子提起来; 胡乱地扔到他身上。因为看不清,也不知道盖住他的头脚没有。
徐南柯出了屋子; 就见腊梅树旁依稀立了一人影; 身影修长; 黑发如墨。
他低声道:“谢长襟?”
谢长襟冷冷地往屋子里看了一眼,扬声道:“压低声音做什么,做贼心虚?”
徐南柯赶紧“嘘”了一声; 压低了声音,笑道:“大清早的扰人清梦,就不地道了。”
谢长襟见他居然是害怕吵醒屋子里那人,眉头一扬,顿时袖中真气激荡,屋檐上的瓦片“噼里啪啦”跳起来,又震耳欲聋地掉回原位置,这下屋子里的人,就是睡成猪,也得醒了。
“……”徐南柯无语地看着他。
谢长襟冷冰冰的声音密声入耳:“蠢东西,我把你养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你去养别的东西?”
你把我养大?你把我揍大还差不多。徐南柯简直要气笑了。可此时毫无真气,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默默忍下这口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谢长襟怒气腾腾地盯着他,他也眯着眼睛回盯。
两人怒目相视半晌,决定暂时放下仇怨,谈正事。
两人走出院落,寻了一处风雪小一点的地方,在石桌两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就有两名女子过来沏茶。此处竟然也有结界,这整个药王谷中,无处不是结界,每一处假山竟然都别有洞天。若不是这两名女子带路,只怕徐南柯还要走丢。
徐南柯喝了一口,入口寒凉宛若冰块,这江诗河居然很有情趣。
谢长襟手指摩擦着茶杯,面上如寒霜,道:“我是来辞行的,我已经问过江诗河,他承诺了你不会有事。”
徐南柯早知如此,要死不活地翻了个白眼,便道:“那你要回哪里去?赌城去?”
谢长襟莫名奇妙睨了他一眼:“自然是回孤鹜山。”
徐南柯手中茶杯微顿,他还以为三师兄在赌城是有特殊的任务呢,皱起眉,讶异地问道:“总不会你下孤鹜山一趟,只是为了四处走一遭,到处吹那破招魂曲吧。”
谢长襟侧目看他一眼,一言不发,只是冷冰冰的脸上写了四个大字:狼心狗肺。
片刻后,谢长襟又密声传音道:“你究竟还有多久回山?”
徐南柯没了修为,被他这简短的几个字震得耳朵疼,忍不住摸了摸耳朵。好心情却被这个问句给破坏了,谢长襟希望他回去,无非是孤鹜山上还有数不清的事情等着他做,数不清的人等着他杀,可他真的想回去吗?
徐南柯突然觉得,回去也没什么意思,等这病好了,倒还不如带着沈寄四处历练,游山玩水去。不过自己原来的身体,还是要拿回来的。
见他半晌没说话,谢长襟脸色也愈发冷了下来,两人半晌没说话。只有谷中风雪飘洒,万籁俱寂。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徐南柯视力又弱了些,谢长襟连同他身后的万丈风雪,都只化作一片。
徐南柯按了按眼睛。
“师兄。”这时,身后有人走过来,沈寄已经起来了,衣衫有些乱,玉冠还未束,一头长发在风雪中飘扬。
徐南柯应他一声:“嗯。”
“你们在聊什么?”沈寄走到他身前,也未坐下,抬眸盯向谢长襟。
谢长襟自然不喜欢他,一见他就故意激将他,挑眉道:“自然是聊你不知道的事情,我与你师兄相识多年,多得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沈寄笑容倏尔退却,眉梢一跳。
徐南柯对谢长襟的秉性最清楚了,一向山中有虎偏向山中行,看起来清冷俊雅,其实十分不怕死,一张嘴开口,不是讥嘲别人,就是挑衅别人。他生怕沈寄少年意气,经不得激怒,便打圆场道:“哈哈,沈寄,不要和他计较,他一向烦人。”
沈寄转眸,视线落到他脸上,语气平静,丝毫不酸溜溜,道:“师兄对他的评价倒是不错。”
徐南柯:“……”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这是吗?这是吧!“烦人”两个字横看竖看,正着听倒着听,都不是什么褒义词啊!
谢长襟既然已经成功地激怒了沈寄,心情不由得大好,一口将手中茶杯饮尽,然后站起身,对徐南柯淡淡道:“既然如此,我便走了。”
徐南柯还没回答他,沈寄已经微微一笑,左手从乾坤囊中拿出来一只白色的团子,与风雪混在一起,徐南柯完全辨认不清那是什么,却能感觉到谢长襟顿时脸色一变,又惊又恼,身体僵硬得像一块铁板。沈寄将毛茸茸的团子朝他身上一送,他回身便躲,呼吸都变得僵硬,躲得狼狈,几乎连滚带爬地跑了。方才还长身玉立宛若天人,此刻已经浑身沾雪狼狈不堪了。
徐南柯托着下巴,望着他三师兄匆匆离去的身影,惆怅道:“沈寄,你学坏了。”
沈寄将怀里那只兔子放跑,袍子一拂,四平八稳地坐在原先谢长襟的位置,左手捏起茶壶给自己倒茶,无辜道:“师兄,我是无意的。”
当晚,谢长襟向江诗河告辞后,便收拾了东西,借了一匹马,准备回到孤鹜山上去,他翻身上马,缓步经过谷中的酒窖,无意打量了一眼。他心中猜疑,倒是想知道,沈寄这小子究竟拿了什么和江诗河交换。
仅仅是酿酒几日?江诗河有这么好心么。
却没想到见到沈寄从昏暗的酒窖中走出来,左手拿着剑,剑有些残破了,右手不自然地垂着,血滴了一路。
谢长襟不禁侧目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白衣浴血,从头到脚,尽是一片脏兮兮的血污,黑沉沉的眼眸却十分有神采,在酒窖旁边的花池子里,扔了剑,抱起一只几人合抱的大酒缸,劈头盖脸地就往头上浇,缸子里的酒将他脸上的血污冲掉,露出惨白面容。
他甩了甩头,将挂在头发睫毛上的酒和血珠甩掉。
谢长襟微微一怔。沈寄察觉到墙外有人,朝这边看了一眼,不过似乎到了强弩之末,并未在意,用酒将身上冲刷得湿透,盖住血腥味后,便提着剑勉强走了。
谢长襟持着缰绳在原地顿了片刻,又往徐南柯住的院子看了一眼,这才转身离去,马匹飞驰,踏雪无痕,风雪里一瞬间消失踪迹。
谢长襟走后,这药王谷中更加寂静。接下来徐南柯又在药水里泡了两天,第二日开始,完全变成了个瞎子,眼前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走路都要摸着桌子椅子,于是沈寄削了根长树枝给他,让他做拐杖。
徐南柯从有意识开始,什么时候不是天资比别人更厉害,看得比别人清晰,听得比别人远,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体验,还怪新奇的。乐呵呵地拿着拐杖东戳西戳,偶尔戳到院子里去溜达两圈,但是外面实在太冷,几乎可以把他冻僵,因此他很少出门。
沈寄在的时候,会谨慎地把他面前的桌子椅子等障碍物搬开,又将拐杖上的细刺细心拔去。拿软布给他擦脸,端水倒茶之类的事情一并承包。除此之外,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