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矿[重生]-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征手下一痛,发现尤志死死捏住了他的手,许征仔细一看,发现平时坚强无比的男人,此时眼眶通红,仿佛再多一秒就能哭出来。
许征在他背后推了一把,把尤志推到霍君宁身上。
尤志埋在霍君宁肩膀,小心又珍重地抱住了她,声音带着哽咽:“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我也等。”
霍君宁用手轻拍着他的背帮他顺气,这些日子在霍家压抑了这么久的情绪突然放松下来:“你别哭呀。”
“叮咚。”又一阵门铃声。
为了不打扰到客厅里的两人,许征走去开门。
门外站着个穿西装的贵气男子,面容尚显青涩,许征却觉得他长得有些面熟。
西装少年身后站着四五个保镖。
许征被他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遍,眼里的敌意才化作勉勉强强的认可,他一张口毫不客气道:“霍君宁呢?我找我姐。”
许征把人放进来后,少年一看见客厅里抱着的两人,气得头发都炸了:“你们,给我放开。”
“成章?”霍君宁看见了一脸怒火却拼命压制的弟弟,“你怎么来了。”
霍成章。
许征在心里默念了遍这个名字。
他记起来了,这人不就是后来的首富吗?
霍家大少,霍成章。
报道上写,他有个去世的姐姐。
也难怪尤志一听见霍成章这个名字就各种不齿。
霍成章年纪轻轻,却表现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眼神轻蔑地瞟了眼尤志,带着浓浓的嫌弃:“就是他?”
尤志最看不惯人装逼,要不是顾忌着霍君宁在场,他当场能把人教训得跪下喊爸爸。
有人替尤志出手,尤信弹了弹他眼镜框,流里流气道:“你又算哪根葱?”
霍成章面色难看,握紧了拳,冷声道:“离我远点。”
“尤信。”
“小章。”
尤志和霍君宁同时开口。
尤志:“滚回来。”
霍君宁:“别闹。”
尤志走上前,把尤信拉到身后,比霍成章将近高出一个头,气势十足地憋出一句话:“五百万,让君宁和我在一起。”
霍成章嘲笑地切了一声:“土包子。”
尤信撸起袖子:“我发现你这个人很欠揍。”
霍成章额角起了青筋:“不要挑战我的忍耐。”
战火骤燃,气氛越发焦灼,许征及时制止:“停,都坐下来,慢慢说。”
四双眼睛同时看向他,许征觉得自己像个幼稚园老师。
一人倒了一杯茶,总算心平气和地将所有话摊开。
霍成章虽然老大不乐意,可那是霍君宁的选择,他有什么办法,甚至还答应不把霍君宁来找尤志的这件事捅出去。
三年期间,两人都见不了面,如果尤志依然未变心的话,霍成章考虑在父母面前替尤志美言几句。
最后,霍成章把霍君宁带走,临行时跟尤志放话:“不是五个亿的生意,就不要说出口了。”
尤志忍了又忍,直到姐弟两走后,才爆出一句国骂。
“哥,要不要我找人帮你揍他?”尤信贱兮兮道。
“少给我添乱。”
第二天,许征也走了。
处理完尤志的家事,他得管管自己的。
要是再不回迁丰,许时在家里估计能把他床都给拆了。
许征刚下火车,提着包往家里走,却在不远的拐角处,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许时背靠着墙,一只脚往后踩,单腿弓起,面前站着四五个男孩子,看着和许时差不多的岁数。
四五个人将许时团团围住,许征刚一上前,就听见许时一声冷笑,眼神中的残暴令人望而生畏:“找死啊?”
对面的人腿都快软了。
许时手里的砖头砸向其中一人背部,那人顿时跪在他面前。
“大哥,冷静啊大哥。”周围人劝道。
许时嫌不够,正欲再砸,突然一转头看见距离他不过三米远的许征。
手里的板砖颓然落地,猛得落在他脚上。
许时面上一片惨白,冷汗顺着下颚滴落,晕染在地面。
这样的许时,是许征从未见过的。
尤志对他的抱怨还在耳边。
“逃课打架,抽烟喝酒,毛都还没长齐,就学人家社会上那套,学校里还收了帮小弟,捧着他做什么大哥。”
“只要他不祸害人家小姑娘,我就该烧高香了。”
许时。
许征一直都以为他是团棉花糖,只是内馅不知为什么酸了。
今天他才幡然醒悟,扒开那层外表后,许时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糖。
他就是个黑心汤圆。
作者有话要说: 明天入V,希望喜欢的朋友能支持一下,我不知道该说啥,最近赶V章赶得快吐了,下章给你们发小红包,两天内2分评论的都有。
希望你们生活少点烦心事,过得都能开心点。
差点忘了推自己的预收,必须推一个,主攻预收:《一刀一个渣攻》(可点进作者专栏查看)
骆城云穿进一本渣贱文,里面的渣攻日天日地、为所欲为,动了心却不肯承认,反而把人留在身边使劲折磨。
贱受心灰意冷日渐憔悴,不爱了却无法摆脱对方的控制。
骆城云成了那个贱受。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亮出了手中的刀。
真男人,不要废话,武力解决。
第二十九章 (三合一)
眼睁睁看着许征走到他面前; 许时动了半天嘴; 憋不出一个字。
“不解释解释?”许征意指目前的状况。
“你们,先滚。”许时回过头; 声音嘶哑; 强忍着暴怒。
走得近了; 许征才发现面前这四五个人,就是上回他和许时上街发传单时遇见的面孔。
当时许时还紧张地躲他怀里; 许征以为许时是怕被同学认出觉得丢人。
没想到; 是不能有损大哥的威风。
周围人屁滚尿流地散了,被许时打的那个也被两人合力架走,只剩下他们两个。
许时这才直视他的目光,眼里是发自心底的恐慌; 干涩的声音带着颤抖,向许征示弱道:“哥; 我疼。”
许征看了又看,最终还是放心不下; 弯下腰对许时说道:“上来。”
背起许时; 许征一步步走回家。
许时将他抱得很紧,死死不肯松手。
他在害怕。
他怕这一松手,许征就不要他了。
“你再紧一点,我就要断气了。”许征被他勒得呼吸不畅。
许时小声道歉:“对不起; 哥。”
糟心弟弟。
许时在他背上的分量很轻; 就算背着他绕着整个迁丰转一圈都不费力。
奇怪; 平时不是挺能吃的吗?
一定是因为挑食; 以后得多让他吃点蔬菜。
不对。
他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许时才对。
许时把脸靠在许征肩上,吐出的气息炙热而烦闷。
还是太轻了。
许征的想法又回到了最初。
背着许时进了家门,王业萍和许敬言都在上班,家里就他们两个。
许征把许时放到床上,压抑下心中所有困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许时处理伤口。
许时的脚上被砸得很惨,指甲盖开裂,从中间整个断层,指甲边缘溢血,半干的血渍结成硬块,小心拉扯才将棉袜完全脱离,脱到一旁的白袜子染上了点点腥红。
看不见的时候还好,一看见伤口,许时就受不住了。
由惨烈的视觉转化为痛觉神经,只觉伤口处阵阵生疼,一缕一缕的疼痛往脑子里钻,许时凑过来抱着许征叫疼。
许征一手拿棉签一手拿消毒水,冷静道:“松开,我给你上药。”
许时这才不得已抓上床边的杆子。
许征皱眉,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疼。”许时叫唤道。
“还没碰呢。”许征只是用棉签沾了药。
“哦。”许时乖乖闭嘴。
等到真正开始上药的时候,许时浑身都在颤抖,死死咬着牙。
许征的动作很轻,干净利落,用纱布将许时的伤口包裹好后,发现许时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
“好了。”许征一句话,许时才睁开眼。
许时怕疼。
小时候家里人碰他,手一重他就哭。
许时睫毛湿漉漉的,唇角被咬流血了,他恍惚间开口:“我好疼啊,你抱抱我好不好?”
许征把人拦进怀里,心疼地抱住。
“知道疼还砸着自己?”许征简直不知道说他什么好,想责怪他吧,偏偏自己狠不下那个心。
许时贪恋他怀抱的温暖。
他怕疼,可是许征的出现,让他连疼都可以不顾。
“对不起。”许时再度道歉道。
许征啼笑皆非:“你跟我道什么歉。”
“前面在街上,究竟是什么情况?”上好了药,许征没忘了这茬,“他们叫你,大哥?”
“我好疼啊。”许时开始耍赖。
许征执着道:“不要转移话题。”
“我要疼死了,哥。”许时在他耳边委屈道。
“不想说是吧。”许征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最终也没打算把人逼进死角,而是妥协道,“行,你不说,我自己找。”
“其实也没什么。”许时突然开口。
许时的语气显得冷淡疏离,还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不是什么好孩子。”
“只是你想看到我变好,我就尽量装成你希望的那样。”
“可惜还是被你发现了。”
声音越到后面,越发细微,一开始好不容易鼓起的底气逐渐溃散,就连尾音都带着不自觉的颤抖,像是等待许征的审判。
宛如被拔了刺后焉了吧唧的小刺猬。
惶惶不知所终。
“是吗?”许征喃喃问道。
许时没回答是或不是,只是肩膀不自觉往后缩了些。
许征心中天人交战,一方面许时承认得果断,把自己贬到了地下,另一方面却告诉他不是这样。
最终情感上的倾向占了大多数,许征缓缓开口道:“可我不这么觉得。”
不带太多情绪的声线,语调很平,可对许时来说却带着救赎的意味。
许征镇定自若地反驳他,像是告诉许时,又像是告诉自己:“谁说你在我面前的时候,不是真实的?同样是你,只不过面对的人不同。”
许征见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人数不胜数,今天还和你是过硬的交情,明天转头就能捅你两刀。
大多数人脸上或多或少都会挂起虚伪的面孔。
可许时没有。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或笑或闹,或喜或烦,许时都很自然。
流露的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
眼见不一定为真,但用心感受总做不了假。
许时怔住,仔细地观摩着许征脸上的神情,发现不像有假,这才放心地笑了。
“谢谢你。”我的哥哥。
我果然,最喜欢你。
许征陷入沉思,他在思考:
在外人面前,被逼出另一面的许时,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许时毛绒绒的脑袋就搭在他肩上。
抱着他的时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姿势。
许征突然想到。
当初他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两年,剩下许时一个人,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他只不过离开两天,许时都难受得要命。
漫长的两年时光,才将许时磨炼成今后那副模样。
沉默独立,不轻易招人烦。
因为他没有了可以依赖的对象。
许征心里一阵发酸,恨不得回到过去,像现在这样,抱抱那个孤立无援的许时。
就在许征还沉浸在自我感动里,忍了许久的许时忍不住开口:“哥你压到我伤口了。”
“对不起。”许征立刻松开。
“你快去洗澡吧,一股火车味。”许时嫌弃地皱了皱鼻子。
在确信了许征待他一如往常后,许时又恢复了本性。
许征随手将他头发揉乱,轻骂道:“小没良心的。”
等许家父母回来后,许时脚上的伤自然是瞒不住他们。
许时借口说是从床上滚下来时摔的。
王业萍揪着他耳朵骂他:“你梦里是当猴去了是不是?这么点大地方还想着打滚,摔不死你。”
许时的耳朵都红了,许征出来,把人护在身后:“睡觉的事,谁能控制呢?”
王业萍这才作罢,想了想后凶巴巴道:“这几天你跟你哥把床换一下,知不知道?”
“知道了。”许时求之不得。
许敬言在一旁补充道:“我明天把床上的栏杆加高点。”
王业萍拍案赞同:“加,最好给我加到半米,看他从哪里滚下来!”
不得不说,这几日因为伤情,许时得到了优待。
家务不用干,书也不用看,成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
可许时本人对此并不感到快乐。
他再也没有办法跟着许征了,当不了许征身后的小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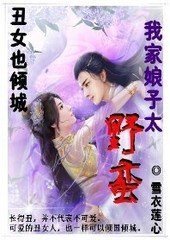
![[重生]天生丽质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