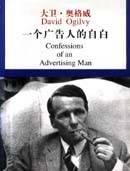自白-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感染导致的低烧,最好能挂个水,好得快点儿。”
“挂水……得花多久?”黎蘅问道。
“两个消炎,快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吧,”医生抬头看了黎蘅一眼,见他一脸的不情愿,又道,“实在不想打针,就口服消炎药,退烧可能会慢一点。”
“没事,”黎蘅一想到拿了药就能回简书病房,心情立刻轻松起来,“麻烦您给我开口服的药吧。”
“成年人了,还怕打针?”
黎蘅只觉得脑袋跟心都飘飘忽忽的,不知是不是发烧给害的,虽知道没必要解释,却忍不住顺着医生的话头,坦诚道:
“不是,我……我爱人在住院,我要照顾他。”
医生没说什么,写了张处方单,夹在病历里递还给黎蘅,末了还加上一句:
“那祝你们早日康复。”
不相干的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黎蘅感到仿佛真得到了好运一样开心,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飘回病房的。
简书的护理床被微微摇起了一点角度,人安安静静地躺在上面,洁白的被子被腹部的弧度高高顶起,那套看着就很复杂的胎心监护仪已经撤走了,病房顿时安静了许多,黎蘅进去的时候,简书正小心翼翼往靠门的一边侧过身子,不知是不是过程中牵扯到了腰腹,简书下意识地想用缠着绷带的手去按揉,刚一动作手掌的刀伤就钻心的痛,简书小小嘶了一声,抬头见黎蘅正快步走过来。
黎蘅扶好微微侧身的简书,拿开了他有伤的手,自己给他慢慢摁着腰,一边摁,一边忍不住想,之前迷迷糊糊的时候,他的阿书该是有多害怕,才能用那只碰都碰不得的手那样死死抓着自己的手腕?
难怪有好几次,纱布上都殷出了血。
像是彼此间真的有感应一般,黎蘅的手将将用力在简书酸痛的地方,摁得人终于舒服了些。
简书闭眼歇了一下,才问道:“去看医生了吗?”
“看了,就是稍微有点发炎,医生开了药,吃过就没事了。”黎蘅轻声回答简书。
“吃了吗?”
“吃了饭再吃——你饿不饿?”
简书觉得头晕恶心,没有食欲,于是摇了摇头。
“是不是还想吐?”
“嗯,一点点……”
“最近用药多,你刚醒,身体又虚,我问过医生了,这是正常的,别担心。”
简书当然知道。刚刚医生来的时候,都和他说过,所以这会儿只觉得黎蘅可爱:最担心的那个,倒是安抚起别人来了。
“阿蘅,下午了……”简书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嗯,下午了,”黎蘅揣测了一下简书的思绪,又道,“医生说,你现在病情还没算稳定下来,最好在安静昏暗的环境下休养,你再忍几天,之后带你去外面晒太阳。”
简书笑了笑,解释道:
“我是说,你快去吃午饭吧。”
“我不急,再陪陪你……”
“我急……”简书还是有些别扭,明显地退缩了一下,才接着道,“你要按时吃药的。”
“好,我马上就去。”
黎蘅嘴里说着,身子却完全不挪窝,仍旧保持节奏地给简书按摩。
“还有啊……”简书这会儿肚子又开始痛,撑不住闭上了眼,“你回家拿一下,我床头柜的文件夹……你们那个设计稿,就是老改不好那个,我给想了个方案,你看看,能不能用。”
黎蘅僵了僵。
还以为简书病前是在做实验室的工作,却没想到,竟是在给自己解决麻烦。
感觉到腰腹部舒适的按揉停止了,简书有些烦闷地动了动:“嗯……给,按按……”
黎蘅几乎要怀疑自己的心是给扔进高浓度的柠檬汁里泡起来了,否则怎么能那么酸?意识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已经自觉地俯下去,在简书额头用力亲了一下。
若不是病人需要绝对的安静,黎蘅觉得自己非得大喊几声,才能排遣堵在自己心口的五味杂陈了。
“下回不许了……”
简书被亲得很舒服,没回答黎蘅的话,在枕头上蹭了蹭,有些长的头发被蹭起一绺呆毛。
黎蘅拿简书没办法,又给他掖了掖被子,帮人揉着腰,看他睡觉。
可是下回,我还想帮你啊。
简书在心里回答。
(67)
等身上的管子撤得七七八八了,简书就被医生要求要适量运动。
卧床半个多月,唯一一点好处就是之前耻骨分离的伤好了一大半,现在腰胯活动的时候,不再疼得让人心慌了。
简书还没被允许出病房。他自己也有感觉,现在听到嘈杂的声音,或是在过于明亮的环境下,都会有些头晕胸闷,因为这个,他还常常和黎蘅开玩笑,说自己可能已经变异成了吸血鬼。
黎蘅笑答,那正好,你咬我一口,我们就可以一起永生不死了。
说起生死,简书的心绪总有些异样。好像心里的某些东西正在变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好像是一种莫名的渴望,从搅扰了他很久很久的黑暗里面露头,引着他去设想:如果明天、后天、下一年、下下年也还能见到眼前的人、还能和他一起做一些别的事情,该多好。
这种渴望很是脆弱,大部分时候,它很快就会被扼杀在更加“现实”的意念面前:别妄想了——心里还是有个声音这样和简书说——你都不一定值得活过今天。
简书开始有一点讨厌这个声音,原以为已经可以与它和平共处了。
黎蘅这句玩笑只说过一次,看简书神色不太对,此后就再没提了。还有许多事情有待改变,但并不急在这一时,黎蘅其实做梦也想看到简书无忧无虑的模样,但他更希望,无论简书愿意怎样活着,只要他是自由的就好。
两种想法,究竟哪一个更值得谴责一点呢?黎蘅没找到答案。
黎蘅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陪简书在病房里走动。其实有挡光的窗帘,外面的天气究竟是好是坏,对里面的病人来说,都没有很大差别。但莫名地,黎蘅就是很希望能对简书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起来走一走吧。
之前已经练过几次,加上最近饮食渐渐恢复正常,简书身上不那么绵软无力了,只是孩子长到接近八个月,分量确实不容小觑。
进入孕后期,胎儿的压迫和血压的不正常让简书呼吸不畅,所以不得不时时带着鼻氧。人自己也很习惯了,只是走动的时候,黎蘅一只手扶着他,一只手还得帮他拿便携的呼吸机,简书腿上力气不够,只好自己伸胳膊搭在黎蘅肩上借力,动作比较别扭。
两人走得很慢,胎儿也随着大人的动作在里面做运动,给简书添了很大麻烦,宝宝的小手或者小脚蹬在简书胃上,总让简书有一种自己吞了铁似的闷胀感,走一阵子就得停下来喘气。黎蘅几乎每走一步都要问简书能不能坚持,这样围着病房里的那一小片空地走不了几圈,人便已经出了一身的汗。
黎蘅心疼不已,面对面揽了简书趴到自己肩上,抚他的背脊,过一会儿又给他揉腰。
“我要是有三只手就好了。”看简书自己怎么趴好像都不舒服,黎蘅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唔……当妖怪吗……”简书喘息着与黎蘅玩笑道。
“对啊,当妖怪,你怕不怕?”
黎蘅说话的时候声音总是刻意压得很低,附在简书耳边,气息拂过他的耳根,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不怕……我是齐天大圣,能、降妖除魔……”
“行了行了,你现在这状态顶多只能当唐僧,被妖怪吃掉。”
黎蘅实在舍不得简书难受成这样,还要强撑着精神和自己开玩笑,不让自己担心,把人的脑袋轻轻摁到了肩上,不让他出声。
简书沉默下来,专心喘气,过了一阵子,才又道:
“……唔……阿蘅,想吐……”
黎蘅听了也不急着挪地方,从简书身侧把人扶稳站直,让他能卸掉大半力气,侧靠在自己身上,然后慢慢给他顺着被胎儿挤占得不剩什么空间的胃。
每次走累了,简书都会有这种不适感,起初黎蘅只会手忙脚乱地给他找地方吐,后来却发现,简书其实吐不出什么东西,只能空耗力气,便专门跑去问护士、问医生,学来给人缓解的办法。
这些事情黎蘅一个字都不提,但简书都知道。
医生每次来查房都要说恢复得很好,黎蘅每次听了这话,都要夸他坚强,但简书知道,若没有黎蘅恰如其分的照看,自己恐怕根本没法体体面面地活到现在。
一个连自己受伤了该去哪个科看医生都不知道的男人,面对他的时候,却永远是可靠又专业的模样。
这样好的男人,怎么就便宜了他呢?简书有时忍不住思考。
大概折腾了有一个多小时,简书才成功躺回床上。今天人走得过猛了些,带来的不适让简书出了一身冷汗,后背的衣服都快湿透了,黎蘅让人侧躺着,自己到洗手间打水。
简书入院起,就在黎蘅的安排下住进vip病房,有独立的卫浴,设施一应俱全。黎蘅似乎从不惮于在简书身上花钱,简书有精力的时候会阻止他,但这一回,也确实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说什么。
高级病房有高级病房的好处。简书只要能起身,就自己坐在浴室里洗澡,病得最重那几天,也有专人来护理,家属是插不上手的。因而今天,当简书歇息了一阵睁开眼睛,见到黎蘅正站在自己面前拧毛巾的时候,吓得心都抖了抖。
黎蘅察觉到,抬眼看了看简书,解释道:“你今天肯定没力气了,在浴室里坐不住的,我帮你擦擦,很快就好。”
简书心伸手把盖在胸口的被子拉到头上,盖住半张脸,摇头。
黎蘅一看,人耳朵尖已经红了。
“阿书,我们孩子都八个月了,你……”
黎蘅话说到一半,也说不下去了。两人唯一那一次,还是酒后不清不楚的结果,总的算起来,真不算坦诚相对过。
黎蘅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简书还是摇头,手死死拽着被子道:“不……”
黎蘅叹了口气,伸手替他把蹭起来的呆毛摁下去:“这么捂着会臭的。”
简书:“……”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感和神秘感?
否则被人捏住七寸,问题就比较大条了,简书想。
(68)
两相僵持了一阵子,简书终于败下阵来,犹犹豫豫地放开了拽着被子的手,脸偏到一边,几乎要把自己闷进枕头里,鼻氧蹭到一边也无暇多顾,没一会儿,喘息就急促了起来。
黎蘅看了也心疼,伸手去挠简书露在外面的后脑勺,轻声道:
“实在不想,咱们就不弄了,好不好?你换换衣服,湿了的别穿身上……”
黎蘅话还没说完,简书就摇了摇头打断。
“要弄……”他闷声说。
黎蘅停了停手,知道简书这是又在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
“想什么呢,快把自己闷死了都?”黎蘅问。
在想什么呢?
想自己的丑陋,突兀地挺在外面的肚子,横亘在腹部的那条手术疤,还有生长在那刀口里面的扭曲又阴暗的过往;想自己竟是那么的别扭,控制不住心底爪牙似的自厌感,但每每放任了这样的想法,却又开始嫌弃自己懦弱无聊;他希望自己什么都能和黎蘅直说,不让他担心,可是又觉得,心里那些被捂烂了、化脓了的伤口,剥出来给谁看,也不能给阿蘅看到——万一他也厌恶自己、害怕自己了,该怎么办呢?
简书在想很多,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沉默填满了两人之间看不见的那些沟壑,变成一堵墙。
过了好一阵子,简书才活过来似地动了动,把脸从枕头里挖出来,冲黎蘅笑。他以为自己把那些苦涩和挣扎掩藏得很好,然而黎蘅却还是全看在了眼里。
黎蘅忽然觉得鼻酸,赶忙低头摆弄盆里的毛巾,掩饰道:“水冷了,我重新去倒一盆,你盖好被子。”
说完便落荒而逃。
真没用啊——他想——这么小小一桩事,又把简书弄得不舒服。
等他再过去的时候,简书已经自觉地略微调直了床头,正半躺着解病服上的扣子,脸上没什么表情,寡淡得如同一尊石膏像,大概是精力还没恢复过来的缘故,他的手指有些微微颤抖,动作得不太利索。
黎蘅接过人手里的活,将简书上衣敞开,简书下意识地抬手挡了挡腹部,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有些无措地把手移开。黎蘅看到,他伸手去挡的地方,是服用安眠药那次抢救留下的刀口,如今被孕腹顶起,变得有些扎眼。
平时给简书按摩涂药,黎蘅几乎都隔着衣服被子来,倒没有考虑别的,只单纯不想简书害羞或是着凉。
但直至今日,他却发现,这些遮挡住他视线的东西,给简书的,竟是赖以生存的安全感,是连对他也不能坦诚的真实。
黎蘅心情有些复杂,却没说什么,只假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顾左右而言他地对简书说,宝宝好像又长大了点儿。简书不答话,微微弓着背,把头埋到黎蘅的肩上。
他线条近乎尖锐的蝴蝶骨,像是随着呼吸的频率在起伏,他的脊柱笔直漂亮,因为背上没肉的缘故,也节节分明地被皮肤勾勒出轮廓。黎蘅拧了毛巾,小心而又眷恋地在上面一一擦过,擦了一遍,又返回去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最后干脆伸手环住简书的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