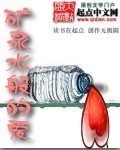自深渊的爱-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姚致敏特意请了医护人员在这边照顾,但是换药的时候,霍定恺却总是亲自动手,他生怕护士不够体贴,弄疼容晨。
容晨在火灾中吸进了烟气,嗓子都是哑的,霍定恺不让他多说话,他说大致情况他都知道了,接下来让他处理。
纵火案很快被警方找到了线索,嫌疑人是几个无赖,起初他们在警方那儿很硬气,坚称只是为了谋财,随便选定的目标。
姚致敏当然不会这么便宜放过他们,重重施压后,嫌疑人终于吐露了实情,是有人拿钱要他们做这件事的。
线索查来查去,就落在本地一个官僚的秘书头上,并且那个官僚确实是任祖年的人。然而再往下查,出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官僚在家中自尽了。
姚致敏和霍定恺都很吃惊,他们没想到任祖年下手这么狠,为了不牵连到自己,不惜结束手下的生命。
“两败俱伤。”姚致敏将警方送来的报告摔在桌上,“任祖年折损一员猛将,咱们也吃了亏。”
此刻他们是在容晨休养的那座宅邸,在场的还有从盛铖赶过来的郝林。
霍定恺靠在沙发里,他慢慢抽着烟,目光落在对面的乌木镂雕窗棂上。这庭院据说是明朝的,里面一切都保持原样,这样古朴雅意的窗子,常常旁边坐着一个簪花的妙龄女子。
没有缘故的,霍定恺想起了许珊。
嫁入容家,许珊收敛了很多,穿着打扮给人感觉非常精心,是那种刻意讨好的精心,她生怕人家提起她的过去:做过吧女,当过裸模,读书太少,男朋友太多……
然而无论她怎么努力,外界仍旧有嘲讽之声,霍定恺还记得有家小报嘲笑她“披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下面配着一张许珊从新年酒会里出来,妆有点花了的疲惫照片。那次酒会来人很多,容家是主角,她和雍容华贵、出身名门的容霁妻子站在一起,简直就是给观众制造天然话题。
她在容家过得不快活,公婆都不喜欢她,虽然不是故意给难堪,但多年老佣人的女儿一下子变成了儿媳妇,容晨的父母很显然不适应这突变的角色。
唯一爱护她的就是容晨,不管外界扑来多大的风雨,他都努力替妻子挡着,如果有人抨击许珊,那他一定以百倍的力度抨击回去。那姿态常常让霍定恺无比的嫉妒,嫉妒得要发狂,甚至怨恨容晨从不曾这样卫护过他——他当然想不到,这女人需要面对的风雨比他多得多。
但许珊却始终感激他,因为她能嫁给容晨,是靠着霍定恺在公婆面前说好话,而且两个大伯子流露出有意无意的鄙夷时,霍定恺也从不落井下石。她甚至对丈夫说,容家,连容霁的女儿都瞧不起她,孩子们嘲笑她喜欢在开水里加白砂糖,觉得粗俗,笑她是个乡下大妈——容家唯一肯公平对待她的就只有霍定恺,所以她一辈子都会记得霍定恺的好。
这话从容晨那儿转述到霍定恺耳朵里,他只觉荒谬可笑,这世上,没有人比他更痛恨许珊的了,到头来,痛恨的对象却拿他当天下第一大善人。
见他不出声,姚致敏以为霍定恺是在思索对策,于是他就说,任祖年蛰伏了这么些年,恐怕等着的就是今天,他想反扑,所以接下来,一场不见血的战争是免不了了。
“这事儿,关键不在任祖年。”霍定恺放下烟,突然淡淡地说,“这不太像他的性格,这样的壮士断腕。他以前不会做的,突然露出毒牙,恐怕是有恃无恐,他也不在乎折损什么猛将。”
姚致敏一愣:“老四,你的意思是?”
“虎狼长出了新的牙齿。”霍定恺轻轻叹了口气,“任时飞是他的第一副獠牙,但当年牙长歪了,开始往里剜肉了。他不得不把牙拔掉。不然这几年,他不会如此安静。”
一直没出声的郝林,这时候终于发话:“事情总能让四爷说个正着。老虎真的长出新牙了。”
他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份资料,放在俩人面前:“这个,就是任祖年的新獠牙。”
霍定恺拿过资料,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男人的照片。
是个而立之年的男性,刻板的发型,黑框眼镜,五官十分端正,但没有任何表情,因此脸孔看上去平板得很。那人浅黑的肤色,着装一丝不苟,鼻梁和眼睛的角度都堪称完美,但玻璃珠一样的瞳仁,透着一股冷冰冰无生气的感觉,让人没法喜欢。简而言之,此人一眼望去就是个政客,但和容霁那种政客不同,他并非是把虚伪的面具戴在脸上,而是,他本身就是虚伪。
霍定恺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人是个“非人”,所以哪怕他张开嘴,从里面冒出布谷鸟的叫声,霍定恺都不会感到奇怪。
“这人是谁?”他好奇又厌恶地问。
“萧竟。”郝林说着,抽出里面的详细资料,“两年前,他开始担任任祖年的机要秘书。”
资料表明:萧竟是斯坦福毕业的高材生,回国后不久就被任祖年弄到身边,也有传言说,任祖年想把女儿嫁给他。
“什么背景?”
“平民出身,父母是矿业局退休工人,家世方面没什么可提的。但本人勤奋好学而且头脑相当不错,任祖年很器重他。”郝林顿了顿,“叫我说,纵火案的幕后策划就是他。”
屋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姚致敏终于说:“反正对抗已经势不可免了,就算长出新的獠牙,咱们再给他拔牙就是了!”
霍定恺也点点头:“接下来,咱们都过不了轻省日子了,好在盛铖经历过那么多风波,也不忌惮再多一次。老姚,往后南方这边,你多担待。”
姚致敏立即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南边你就交给我好了。容晨往后再有事,我提头来见。”
霍定恺笑起来:“别别,真用不着那么夸张,而且我已经打算带小晨回去了。”
郝林犹豫道:“三少恐怕不会肯的吧?”
“我管他肯不肯!”霍定恺恨恨把烟头扔进烟灰缸,“刚来一个月就搞成这样,你叫我还怎么放心把他丢这儿?容晨性子过激,做事情莽撞,再留这儿,只会给老姚他们添乱。我还是换人过来,我想过了,就让邱睿顶替他。”
郝林不由苦笑。
“还有,这个萧竟。”霍定恺拿起那帧照片,“郝林,你再去查一查,我总觉得……”
“四爷是觉得哪里不对?”
霍定恺踌躇半晌,他轻轻叹了口气:“也可能是错觉,有点面熟。”
“四爷见过?”
“不,我没见过。只是感觉上不对劲。”霍定恺停了停,继续道,“查得越细越好,尤其他父母那边,刨根问底的查!”
容晨的烧伤不严重,伤口结痂,疼痛变得轻微,他可以起身在院子里小范围的活动。没过两天,他就呆不住,嚷着要回去工作。
“包得像个木乃伊,就你这样子,怎么回去工作?”霍定恺讽刺他,“你想大家再分神来照顾你?”
容晨却低着头,过了一会儿,他才哑声说:“好歹,也得出席追悼会吧?”
霍定恺知道,他说的是那名罹难的员工。
霍定恺轻轻叹了口气,他把声音放缓和:“那不是你的责任,那是意外。你不是神,救不了所有的人。”
容晨呆了呆,好半天,他才缓缓点头:“是啊,其实我谁都救不了。”
他的声音嘶哑难听,是想起了旧事。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霍定恺找来一套围棋,这是他们小时候最爱玩的东西。
春日,气温回升,院子里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俩人在老梅树底下,摆了桌子手谈。霍定恺的棋艺比容晨强很多,也是出了名的强手,那些爱棋的老总们,大都和霍定恺有过厮杀,纵横商界这么多年,霍定恺输棋的次数屈指可数。
面对一个永远赢不了的对手,谁都会觉得气馁,偏偏容晨乐此不疲,他可以一连输半个月,却不会因此就不肯再玩。
今天霍定恺仍旧执白子,起初容晨总是坐得很端正,就像那种真正在世界大赛上拼杀的棋手,身体会离棋盘较远,要特意伸长手才能下子,那姿态,像身后就摆着描金松鹤屏风的大国手。
可是下着下着,他就会忘却周围,一心铺在棋盘上,特别是棋局进入收宫阶段,容晨就会浑不顾外界,紧张得把头埋得低低的,眼睛死死盯住棋盘,身体不断慢慢前倾,头发都快碰到霍定恺的衣服了,几乎整个儿压在棋盘上……小时候,有一次他没坐稳,咣当一头栽倒在棋盘上,逗得旁边围观的容霁他们大笑。
虽然是面对最疼爱的弟弟,霍定恺下棋的态度永远认真谨慎,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他知道,故意输棋会惹容晨生气,就算再巧妙的让步,都能让那小子瞧出来,那会导致容晨更愤怒,因为他觉得被霍定恺小觑了。
但是霍定恺也从不做那种非得把容晨逼得丢盔卸甲、片瓦不留的事,虽然方圆纹抨是一个残酷的胜负场,围棋的和局概率大约是几千分之一,输或赢就如同黑子和白子一样冷峻分明、无余地可言,但每次俩人下了几个小时,容晨的输势已成定局,再加上那小子开始哧溜哧溜的吸鼻子,分明是在使劲儿忍着泪,这种时候,霍定恺就会笑笑,站起身说:“哎呀这么晚了,算了不下了。”
今天仍旧是如此,下到一半,黑子的颓势就开始显露,霍定恺瞧着容晨咬着牙,好像牵动了纱布底下的伤口,他忍不住懊悔道:“算了不下了,外头风太凉……”
“我要下!”容晨抬起头,气哼哼盯了他一眼,“输也要输个明白!”
然后,他一把抓起一枚棋子,放在棋盘上。
霍定恺定睛一瞧,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容晨刚刚落下的那枚子,竟然放在了一块已经被白棋围得水泄不通的黑棋中!
这一大块黑棋原本看来还有一丝活气,虽然白棋随时都可以把它吃干净,但只要对方一时无暇去顾及,那总还有一线生机,尚可苦苦挣扎一番。可是容晨这么一招,却将自己的黑棋吃了,明白是自杀的行径。
霍定恺一时骇笑:“你气糊涂了?”
岂料容晨抬起眼睛,似笑非笑瞧着他:“谁生气了?”
那之后他的举动,更让霍定恺困惑不已,只见他又取过一枚黑子,下在剔去了刚才那片黑子后显出的空位上。
这下,霍定恺的眉头拢紧了。
刚刚容晨那步棋,看上去虽无异于自杀,但是它也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被去掉了大片自己的棋子后,黑棋劣势尽管依然存在,但白棋在这一下子豁然开朗后,却蓦然显出些许致命的缺口!
而黑棋,虽然仍没能改变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局面,但在风云变化之下,却隐隐透出一股亡命反扑的凶狠气势。
会出现这个局面,这是霍定恺没想到的。
容晨稍稍往后靠了靠,让自己坐得更舒适一些,他抿住嘴,有点得意的着看着低头沉思的霍定恺。
霍定恺的心头,莫名笼上了一层不祥的阴云。
“你啊,总是这么干。”他轻叹,“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能牺牲。”
“为什么不行?”容晨盯着他,他双眼晶晶亮,“只要赢棋就行了呗,牺牲算什么?”
这也是容晨的习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剑走偏锋,出其不意,哪怕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儿,他也照干不误。
霍定恺凝神盯着棋盘,忽然笑起来:“真能赢么?”
接下来,霍定恺飞快用了几步,就把那个缺口给补齐了。
容晨愕然望着棋盘:“你到底是怎么下的?”
霍定恺忍俊不禁:“我可没作弊,在你眼皮子底下落的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容晨追问,“你好像预先就知道我会这么干……”
“我不知道。”霍定恺安详地说,“我只是不着急,慢慢打基础,有些东西碰巧用得着,有些也许到最后也用不着,可是我这样做,保险。小晨,是你太着急了。太急了漏洞多,就容易输。”
“胡说!没输!才没有!”容晨还兀自强辩,指着棋盘,“明明走哪一步都是细棋!”
霍定恺忍笑道:“好好,是细棋,你慢慢下。”
午后薄云流转,天色更清朗,阳光如瀑奔泻,晒得人身上暖融融的,有一种浑不着力的绵绵之感。
容晨把一枚黑子按在下巴上,白皙修长的手指按着纯黑玉石,指尖滑润如那黑玉棋子,霍定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觉得身上那股绵软之意,更加强烈,他的喉头开始发干,小腹那儿,像有一千只蚂蚁在乱爬,一时间他心猿意马,几乎无法再专注于棋盘。
救了他俩的是护士,她走过来提醒容晨,该去打针了。
容晨不情不愿起身,还指着棋盘嚷嚷:“其实我就要赢了!喏,这还差两个子……顶多再有五个子!今天我一定赢!”
霍定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