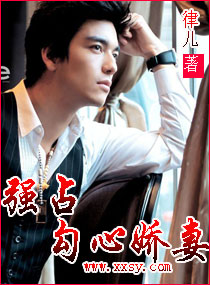厨娘当自强-第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前还真没想到是刘成干的;虽说结下了梁子,也不过是厨行之争;这纵火害人性命;着实太过了,且,上回梁子生进京;还曾特意拜会了师傅;言谈之间颇有讨好攀附之意;这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着实耐人寻味。
听说富春居如今的东家是曾为帝师的梅先生;这位哪是好惹的;且,富春居纵火一案可是前儿的事;当时并未报官;却等到把放火的找出来;再报官;这就是想揪出后头的指使之人;;此等纵火之事若把师傅牵扯进去;却大大不妙;还是先回京再做计较,都没敢在齐州停留;直接出城回京了;。
狗子瞧着他出了城,莫转头回梅园送信儿。
富春居正在紧锣密鼓的整修;安然也只能暂时在梅园住下;倒难得清闲了下来;每天除了给先生做些吃食;就是跟梅大腻在一起。
先生的梅园颇为别致;因进园的时候那两株老梅而得名;可惜如今开了春,梅花就别想了;光秃秃的树干上抽出了嫩嫩的绿芽;映着潺潺流经的一弯清泉;也别有一番景致,让人一进梅园就觉春意盎然。
梅园之美;美在精致上;比起富春居更得南边园林的精髓,也难怪先生会选在这里隐居了;不过,这满园□□落在安然眼里;却有些说不出的伤情。
一想到罗胜竟然就是纵火之人;安然就觉倍受打击;在她眼里,富春居的人都是难得的好人;从厨子到伙计;各司其职;在富春居最难的时候;都没想过离开;却又怎会纵火 ?
梅大一进小院就见这丫头坐在水边儿,拖着下巴发呆;脸上颇有些郁郁之色;梅大目光闪了闪;这丫头什么都好;就一样儿心太善;太容易轻信于人。
有时,梅大都觉或许在这丫头心里;除了安府的大老爷是个不可救药的大坏蛋;其他都是好人;殊不知,人的心有多阴暗复杂;为了名利;可以泯灭人性;什么事干不出来。
便是罗胜;即便有苦衷也不可饶恕;若不是自己及时赶到;她……梅大如今都不敢想那天的事儿;从没有一刻,让他觉得那么害怕失去一个人;哪怕他的势力再大;财产再多;若是没有这个心坎里的丫头;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不知不觉中这丫头早已入心入肺;只要有他一天;就不会让这丫头有丝毫闪失;他会用自己的一切能力紧紧护着她。
可自己这番心意;却不敢跟她说明;他怕;他竟然怕;便他自己都觉可笑;这么多年;什么事没遇上过;哪怕再难的时候;何曾怕过?可遇上这丫头;他真怕了;怕她爱钻牛角尖的小脑袋;死也不接受自己;怕她一走了之;让自己找不着人;怕她被那些躲在阴暗之处的小人谋算;吃亏受罪;甚至丢了小命。
他怕的太多;所以,他才这么瞒着她;所以,才迫不及待的想成亲;用一纸婚书拴住她;这份苦心,不知她将来知道会如何;以她的性子;真难说。
见她抱了抱胳膊,不禁皱了皱眉;把身上的斗篷卸下来走过去;披在她肩上;从后头抱住她;揽在自己怀里:“刚开春风凉;自己一个人在水边儿想什么呢?看着了寒气。”
安然摇摇头:“我只是想不明白罗胜为什么会纵火;他那么一个老实人;怎会做这样的事儿?”
梅大抓住她的手;感觉有些凉;不禁皱了皱眉;揽着她进了屋,才在她手上写:“越是老实人越会做出人意料的事儿;更何况,若有人威逼利诱;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安然愣了愣:“指使?你是说有人指使罗胜放火?”
梅大点了点头。
安然想了想:“是韩子章吗?”
梅大摇头:“即便韩子章想挑起南北厨子之争;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想对付你;有的是招儿;放火不是等于把小辫子送到咱们手上吗;只要韩子章不傻,断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是燕和堂的刘成。”
安然叹了口气:“我是不想眼看着厨行争的你死我活才出手帮忙;都是同行,何必自己难为自己;便燕和堂,当日也叫狗子送了菜谱过去;不想,他竟如此恨我。”
梅大:“刘成本就是个小人;最见不得别人好;当初之所以撺掇梁子生挤兑富春居;就是因为看上了富春居这块风水宝地;想谋在手里;若不是先生出头;还有你这个厉害的大厨;富春居早成了刘成的囊中之物;你坏了他的事儿,他能不恨你吗?”
安然:“原来如此;我还说自己没怎么得罪过他;做什么要烧死我……”话未说完就被梅大捂住了嘴:“不许说这个字。”
安然愣了愣;他是怕了吗?在她眼里;梅大一直是个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怎会怕?想仰头看他的眼睛;却被他紧紧箍在怀里;感觉他温热的气息贴近自己的耳畔;用嘶哑难听的声音道:“我已经请先生择吉日为我们主婚。”
感觉安然身体一僵;梅大放开她;却捏住她的下巴;让安然不得不跟他对视;端详她良久,不瞒的道:“你答应我了。”
是答应了;可也没想到这么快啊;见他又要急;忙道:“你别乱想;我只是觉得有些太快了;还有,就我们两个怎么成亲?”
梅大目光闪了闪;拉过她的手写:“你想让谁来吗?你师傅?”
安然没说话;虽说她并不注重形式;到底成亲是一辈子的事儿;至少,她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在场;这是最基本的吧;可她的情况有些特殊;师傅师兄还好说;干爹干娘两个干哥哥都是安府的人;让他们大老远来齐州;怎么可能?
而且,安然心里也总说不上有种莫名的感觉;这难道是婚前恐惧症;又觉自己实在矫情;既然答应了;再这么推三阻四;算什么、
想到此,下定决心的点点头:“我听你的。”
梅大顿时欢喜上来;伸手把她揽在怀里;低声说了句:“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嘶哑难听的声音;听在安然耳朵里却觉比天籁都动听;果然,自己也是个俗气的女人;喜欢听男人的甜言蜜语。
感觉他要亲自己,安然脸红的闭上眼;即便都亲了好多次;她依然忍不住脸红心跳;真是挺没用的。
梅大刚亲上;就听外头狗子的声音:“师公,师公……”
安然猛然惊醒;急忙推开梅大跳下炕;整理好自己的衣裳头发;狗子已经窜了进来;眼睛溜了一圈;感觉梅大身上散发出格外阴沉的气息;再瞧自家师傅;脸色通红;浑身不自在;暗暗叫糟;一定是坏了梅大的好事;以后真的小心些;这位马上就是他们的师公了;师公这手段;他可是亲眼见了的;真要是想收拾谁;想死都不易。
见梅大瞪他,忙道:“那个,我是来跟师公说;那个从京里来的白脸汉子刚出城了;瞧方向是回京城去了。”
梅大点点头;安然都没来得及问他什么;这小子一溜烟就跑没影儿了;开玩笑,再待下去;回头师公记了仇;有自己的好儿吗;狗子如今算是知道了;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梅大;这位可不是善茬儿。
安然不禁道:“这小子长了一岁倒越发毛躁起来,怎么也不说清楚就跑了。”说着,看向梅大:“狗子说的白脸汉子是谁?”
梅大在她手上写:“如果没猜错的话,是韩子章的三徒弟顾永成。”
安然愣了愣:“你是说那个蜀地的厨子?”
梅大点点头:“你别小看他,他的手艺比崔庆不差,却因一直低调;故此在韩子章三个徒弟里;不大出名;且,此人颇为精明;从他跟刘成撇清就可见一斑。”
“那你可知他擅长什么菜?”
梅大似笑非笑的看着她;把她的小手在掌心揉了揉:“我也不是厨子;哪知道这些?”说着笑了一声:“以我们家小宝贝的厨艺;还怕他不成?”
小宝贝?感觉他写出这个三个字,安然脸腾一下红了起来;捏了他的手背一下:“瞎叫什么?”
梅大却低低笑了起来;在她手上写:“不叫宝贝那叫娘子如何?”
安然脸更红;怎么都没想到;一向老实的梅大;也会这些;真有些不适应;猛然想起刚才狗子叫他师公;小脸更红;心说,回头真的好好教训教训那小子;哪儿跟哪儿啊;就乱叫。
梅大却爱极小丫头此时的样子;有些羞涩;还有些小心思;一双明眸忽闪忽闪的,仿佛一双翅膀在他心里不停的扇;把他心里压制已久的那把火;越扇越旺。
火起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她;把她揽在怀里就亲了起来……不是还有一丝理智;这把火烧起来;今儿就把她变成自己的了,不过,到了这会儿梅大反而不着急了;人就在怀里;肉就在嘴边儿;还怕小丫头再跑了吗,倒是该想想怎么收拾两人的新房了?
这丫头稀罕水边的房子;至于布置;想起她在冀州府的小院;梅大不禁暗暗点头;小丫头喜欢自己收拾呢;自己只要找好了房子就不用管了;也给小丫头找点儿事干;省的她成天想罗胜的事儿。
罗胜纵火行凶;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了;如果命好赶上朝廷特赦,或许能提前放出来;这已经是自己手下留情;若不是小丫头没事儿;他罗家的祖宗八代都别想消停。
至于刘成;不用自己出手;自会有人收拾他;这厮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落到这种境地;眼看回天乏术;肯定就变成了疯狗;逮谁咬谁;咬别人还罢了;他若说咬梁子生;就是活到头了;梁子生这人聪明着呢;断不会让这么个小人捏住把柄,到了这份上;不把刘成弄死;有他的好儿吗。
果然,没几天就传来刘成病死在大牢里的信儿;刘成没儿子;就一个丫头也早嫁了人;燕和堂一封;刘成那几房小妾;一见势头不好;卷着金银跑了;丢下刘成原配的婆娘;一气之下;投了井,前些日子还风光非常的刘家,不过几天就家破人亡,整个兖州府没一个可怜刘家的,可见刘成此人干了多少坏事。
知府大人念在燕和堂也是百年的老字号;并未充公;发还本家;落到了刘成一个远方侄儿手里;这个远房的侄儿倒是个有心路的;知道借着富春居的东风;南菜受欢迎;特意从南边请了两位大厨来掌灶。
一来二去;倒是把燕和堂经营了起来;最后堪堪跟聚丰楼汇泉阁齐名;后来在齐州府;一提南菜馆子;除了富春居;就数燕和堂了;想来刘成泉下有知也该闭眼了;至少他老刘家的字号还挂在齐州府;且越来越红火。
此是后话不提;却说安然,这几天没怎么见梅大;心里难免胡思乱想;这男人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大早就出去;老晚才回来;自己想见他一面都难;问他吱吱呜呜也不说;不止他,连狗子都跟着他来回跑;安然如今都怀疑狗子不是自己的小徒弟;是梅大的跟班了。
心里有事儿连整理菜谱的心思都没有;写了几个字就放下了;看了看窗外;日头落下去了;看来今儿梅大又不回来了。
眼看到了晚饭的时辰,安然便去了灶房给先生做菜;梅先生晚上吃的不多;且喜欢清淡;却极挑嘴。
安然本来还不知道给他做什么;却一眼瞥见旁边小筐里有半筐苜蓿芽,一时倒勾起些许旧事来;这一晃自己离开冀州都大半年了;不知师傅师兄怎么样了;干娘一家子过得如何?
想着不禁叹了口气;也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他们;自己都要嫁人了呢。
先生的家厨是个极老实的汉子;也算个南派厨子;手艺没有先生说的那么差;颇有几个拿手菜;尤其最善做小食;点心做的尤其精致;只不过人有些执拗;不知变通。
见安然竟要拿喂牲口的苜蓿芽给先生做菜;吓的脸都变了;忙拦她:“姑娘;这是喂牲口的;哪能做菜。”
安然笑了:“我师傅常说万物皆可入药;也皆可入菜;尤其,这些天生地长的东西,更是老天给我们的馈赠;大叔是南边人;你们那儿到春天不是有许多野菜时鲜吗;比如水边的蒲菜;还有荠菜;马兰头;茨菇;水芹……挑回来;做菜做汤都是最新鲜美味的。”
那厨子听了不禁笑了起来:“姑娘说的是;我们那儿暖和;一开春不光野菜时鲜;水里的鱼也最是肥美。”
安然点点头:“这苜蓿就是北边的时鲜;挑了最嫩的芽;兑上肥肥的五花肉做馅儿最香;不过,我还是喜欢跟面搅合在一起烙成饼。”
厨子吃了一块;摇摇头:“先生自来挑嘴;怕不会喜欢。”
安然笑了:“大叔就放心吧;先生一定喜欢。”
厨子半信半疑;所以,安然才说他不知变通;对于梅先生的性子了解的也不够透彻;梅先生虽挑嘴;本质上还是个文人;文人吃东西大都讲究个出处;这苜蓿盘的出处可大大有名;哪怕味道并不至美;想着当年清苦的前人;也不免自比;这就是文人风骨。
果然,梅先生一看盘里的苜蓿饼,眼睛就是一亮,摇头晃脑的念了两句:“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难为你这丫头倒知道这个。”就着粥吃了好几块;看的一边儿的厨子大叔一脸迷茫;安然不禁好笑。
陪先生吃了饭;安然回了自己的小院;刚进屋就见梅大坐在炕上,安然愣了一下;不免有些怨气:“今儿回来的倒是早。”
梅大低笑了一声;拉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