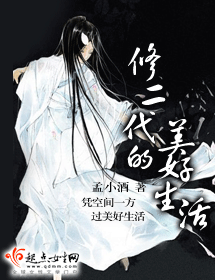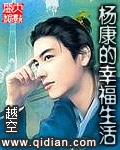明朝生活面面观-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侄儿定献王从北京回来,也不说他啥。可是他老人家不买帐,你不说我,我有得说。他就给朱棣偷偷地写了个密折,说什么呢;说的是定献王对皇上颇有怨恨,私下里谩骂,诋毁皇室,当然也可能是。写个密折,就得做点污七八糟的事儿吧,他就作了些伪证交了上去。
这还了得,朱棣自己是怎么上台的,他最怕人家说帝位来不正,如今要是有侄孙要如此这样遣责自己,说不定背后还有可能是图谋不轨,密谋大明天下,怎么能饶得了?有背景的可查的,因为封在荆州和长沙的两个兄弟王都是被人诬讦,吓得全家自禁的。
一道诏令,把定献王叫到北京。可是还没得及处置,朱棣驾崩了。华阳王这个恨啊,怎么朱棣突然就死了?他最恨藩王谋逆的,想着定献王去北京十足十地死翘翘。可是没想到可爱的胖子仁宗即位了,如何?人家火眼金睛,看出这中间有猫腻,于是查了查,发现定献王根本没有谋逆的可能,放了回去。把华阳王给叫到了北京。华阳王坚持原来的说法,就是定献王有诋毁天子之事。仁宗气极,掷了他的奏折,把他罚到了湖广的武冈,没让他站稳,又迁到澧州。
都说恶有恶报,可是他的执著却让他至死不悔地惦念着这件大事。当然,小事也不能放过。谁得罪了他,对不起,他本来就不是个君子,自然哪里会轻易放过。
周大人年正好到武冈,任了一个七品县令,与他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期间还发生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周家人都不提这事,文箐开始的两年更是没法知道这些了。
可是华阳王被迁到了澧州,怀疑是周大人能掺了一脚告过状,当然没有证据了。实际上,倒是有可能,因为华阳王那么张狂地一个想谋那个王位的人,那时到了武冈肯定有种“虎落平阳”的感觉。要是谁不小心就是没碰到他,可是远远地见了他的车骑就拐了弯那也得被记恨,这不是典型的不来拜见自己不给自己面子嘛。横行乡里,那也无须去多想有多少次,这让一个小小的县官如何来维持秩序?肯定是想赶走他啊,华阳王至少是这么断定的,而且谁也会这么想让这恶魔快走,能多远就多远。所以,周县令一定告过状——这就是他的总结。
没三年,他在澧州听到周大人核为优,又迁到四川成都府下,这不是投奔到定献王旗下了么?于是开始查一查这周大人景。周大人年就定居北京城,必和定献王认识;当然熟悉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不过对于偏执狂来说,只要丁点儿怀疑就会让这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所以嘛,看到周大人到成都府下,去年又升任了从五品同知,那八成是这两人有所勾结,所以周大人成了他要去定献王之后的唯二的目标了。
至于有人后来也说,周大人定献王有点相像,所以定献王恨屋及乌也是可能的。当然,这都是传说之一。
不过陈大福管事没说上面这么多内容,就是偶尔说一两句介绍,这以上都是文箐后来扒出来的,陈大福就说的关键句是“问你师傅去。”
文箐当时愣了,自己有个师傅?这中间还有个人恩怨?难怪这华阳王对周大人念念于兹”。于是傻愣愣地问了。
陈大福道:“我也是糊涂了,你都是不记得好些事了,不过没想到你把你师傅也忘了。当然,小姐现在身体缓转了,也不练武了。你师傅,吴先生啊,过些日子也该来了吧。到时你就知道了。”
等到文箐最后知道吴先生的时候,才隐约知道些周大人华阳王,吴先生之间可能有的那么几丝瓜葛,当然也是如云似雾,看不清。
不论如何,对于华阳王来说,周大人个梁子结大了。
于是,不能拿下嫡王的位置,就先给定献王一个敲山震虎,我视他为你的人所以我就敲打敲打你的这个人。华阳王就让人密了一个折子,说周大人反太祖所制律条,尤其是游妓,还娶了个乐伎为小老婆,又八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问题,反正风化罪在明朝是个大问题,不说全家论斩,至少官位不保,永不启用。
好了,果然华阳王得逞,这厮干坏事干得真是得心应手啊。
停职查办,论罚,周大人挨了八十棍。虽然后来交了不少钱打点,落了四十棍。可是一个文人,也经不起半真半打的皮开肉绽,这无妄之灾,便使得他发了一场病。待屁股上的伤好转了些,一家灰溜溜地从成都打点好家底,购了八万贯钞的货物,满满一船,到江南或者北京,怎么也得赚上三万贯钞。可是有人不想轻松放过啊。
大家以为此事已了结的时候,华阳王却想着如此收手是否太便宜了,“斩草不锄根”,不是他的作风。我是流氓我怕谁——当然,这里就变成了盗匪的话是:我是流民我是盗匪,我有人在背后撑腰,打着流民旗号,我怕WHO?
可怜的周大人带着一家大小,在巫峡过后,和女儿讲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真是泪满襟啊。被人等在四川和湖广交界地带,那里正是风平浪静,船速也不快的好地方啊,抢了。
抢了一船货,到了载周大人眷的船上,道一声:“周大人有位大人物让某来找你算算帐的。你让他儿子没了,他便让你也断子绝孙。”一刀劈过去,周大人地。
当时的文箐小姐,作童儿状打扮,给惹急了,叫一声:“休得欺负我爹爹!”拿了随身的匕首,很是英勇地给匪首手上留下了痕迹。
这还了得?!
对方手一抖,把个文箐朝甲板上一摔,可能是手受伤,这使的力道和准头都误差大,把文箐摔在了甲板边沿,碰了下,掉下江里了。
这上边对打着,下头早有人在开洞沉船,一家子乱成一团,船夫们顾此失彼,匪徒们只听人叫的叫“老爷”,叫的叫“少爷”,叫的叫“夫人”、“姨娘”、“箐儿”,以为那文箐就是独苗呢,想来这老少爷们也活不成了。跑到舱里又抱了些钱物出来,其他匪徒也不想多伤人命,得了钱财,调戏了姨娘给跳下水去,于是押了那船货扬长往下流而去。船上的李诚护了小少爷在一边,没让人多注意这个男儿才是真正的少爷,在小姐被当作少爷给扔下去的时候,交了少爷给阿素,自己则跳下水去救小姐,陈大福也受了些伤,抱了老爷往旁边躲,大喊“卫所巡逻来了!”
文箐在几年后,悲催地作此段说书。当时总结的是华阳王乃这样一条蛇,定献王是个十足的农夫。从自身来看,想着自己果然没有那个小文箐般英烈,自己是怕死得要命,可人家六龄童,那真是不怕天,不怕地,敢于为救父拼死于长江,何等的胆气。
第十五章 小绿要谈婚论嫁了
周夫人一看该清的债全清了,看看帐面,头痛。钱拿过来就是不经用,没个营生。船这东西,不是说能找到买主就能马上找到,毕竟要是庶民之家,哪里有这个钱?有钱的,想买船的,又想便宜的,才会买这条船。自己拖上来,无非是想花点儿小钱,总是在以后还能多收回一些。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文箐在旁边练字,看在眼里,无计可出。偷偷地翻了翻周夫人的帐本,算了算现在这个二进的小院,挤挤地住了十四口人,除了周家五口,陈嫂四口,李诚三口,加上小绿和当地雇的厨娘,小孩吃的不多,奈何吃的是些果子类的,尤其是小文简,从小给养的刁嘴只吃好的。周大人病加重,常常用的药也明贵起来,这个归州不如成都府,物价虽然也相对来说便宜些,可是买点儿东西也不方便,药钱可就不便宜了,得求了人从成都府或者荆州一带捎过来。
一家的吃食加看病诊费,算起来,一个月也得花掉一千多贯。而从开销来说,显然是陈嫂三口六百贯,李诚二口四百贯,小绿是一百二十贯,厨娘是一百八十贯,这么下来也得一千三百贯。
不过陈嫂和李诚家的一千贯,两家都是这几个月没给月例了,等回了苏州再算,厨娘却是要给的。船在五月底修好了,花的费用是一千五百六十八贯。
陈嫂也算过帐,最后和周夫人道:“厨房的活计奴婢和阿静,阿素,有足够的时间,厨娘还是不要了吧。”阿静和阿素也来说,省一点就是一点。
周夫人想想也是,厨娘毕竟不太熟悉周家的饮食,很多时候都是陈嫂和阿静下厨来给周家大小做饭,厨娘就管着他们几个人的吃食。于是也就让陈嫂把厨娘打发了。
其实是陈嫂发现这厨娘手脚不干净不说,平时贪点便宜可以装作不看见,可是给少爷小姐的好吃的她必然吃一小半,或者偷到自家去,最主要是干活有些不讲究,给夫人小姐的吃食要是在府里都是精致的,可落在眼里的不是碗不洗净便是菜案上有污迹可察。陈嫂怕把一家子吃出病来,只得赶快撵人。盯着她干活,还不如自己几个动手。
文箐想,小绿虽然能干,可是17岁的小绿在这府里到底没能有多大表现的机会,又无宴客的机会,放在这里除了这儿帮帮忙那儿搭帮手,还真是有点儿浪费。可惜她无依无靠,而周夫人的意思是好歹是在身边用惯了的,只能带到苏州后再给安排人家了。
船还在修,需重新买楠木,然后再拆卸掉,重新换掉,再重新加固,上漆,等等一系列改造工程,耗时耗工。所以,一时也卖 不出去。据说前段时间江南大雨,长江上通行的船只都少了。有天陈大福管事闷闷地道了声:“江南要发大水的话,那可大麻烦了。”
事实上,当初他回来时,已预料到了。可是能预料到,又能怎么样?人力在上天面前,只有悲叹。
这话说完,几个大人都一凛。李诚道:“应该没事。”
这事也就过去了。眼前的最主要的是老爷到底能不能快点好起来,行船的话能否坚持到北京,哪怕是苏州地界都是好的。最最主要的是耗下去,人能耗着,钱耗着就会光的。
陈大福和李诚来找周夫人商量,以免这样坐吃山空,是不是两大男人出去忙点儿啥?
周夫人道:“这也就是在这儿呆一两个月等老爷的身体能坐船才是。去京城的话,反正归州方面已经给北京发了文书说老爷在这里病困无法动弹。不是没想过要手里的钱只出不进的情况……这地方,太小了,买卖 东西只能靠码头的船上的商家,本地人是难……”
三人都知道,短时间的呆在这儿,确实不能置办产。,要说短期的几个月,也就是从成都府贩点儿物事到荆江宜昌岳州三府,可是这一家大小毕竟要留一两个成年男口在这候着,所以这经营也只能放弃。
果不出所料,码头上传来消息,好些流民开始沿江而上了,荆州府岳州府都有大批流民,显然江南的情况不容乐观。今年,收成是问题。粮食要是差了,众多商铺的生意可就难了,除非是经营粮店的。要是再有个瘟疫,只怕不好。
在这坏消息接连不断的情况下,终于有点好消息。就是小绿经常去取药,来回有两个月了,和医士的小弟看对眼了。可是碍于自己是奴籍,而不敢说出来。那边郭三郎却对小绿说:如今是法律也放宽了,只要邻里相处好了,不去专门告发此事,也无人管这事。自是无碍。
陈嫂一从小绿嘴里得到这点儿信息,马上开始想到冲冲喜,就把老爷的病冲好了。又得听“良贱”不通婚这一条,大笑。带了小绿去给周夫人通报喜事。周夫人很是高兴。
小绿道:“这万一要是有人告发了……”
周夫人道:“这是好事。你无须为此担心。”
陈嫂也乐着,打开了一个匣子,取出来一张纸道:“喽,看看这是什么?”
小绿一看,这不是当年自己的卖 身契吗?而且还是白契?!夫人一直没去换红契?!小绿明白过来,忙跪下来磕头,眼泪直流。
陈嫂待她行了礼,拉了起来,拍拍她的裙子,安慰道:“夫人在你当初投卖 时早就给你设想好了。你跟了咱们夫人,真是三生修来的福分呢。”
小绿抹了把泪,眼眶里泪还是停不住,声音哑哑地:“夫人,原来您……”
周夫人点点头,面色有些微凝:“当初你来府上,那时都十三岁上了,这要是你家情况好,不就是两年后出嫁吗?你家没有亲人了,你和我也是缘份。我当时不收你的契,你会以为我肯定不要你,怕你想不开,只得收了。一个好好的良家女,为了奴,可如何是好?我也就一直压着,只等你出嫁了,好给你。如今正是时候。”
小绿嘴里只有:“多谢夫人,奴婢……”别的再也说不出来了,泪水流涟。
陈嫂在一边看了,笑道:“还叫‘奴婢’?没听夫人一直不让你这样称呼自己嘛。你快去和郭家三郎说清了,你还是良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