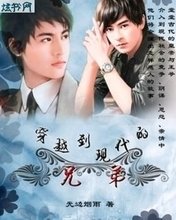这一代-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向露出了“别哭”的口型!
这场批斗一直进行到了傍晚放学后,等学生们都嘻嘻哈哈的散了,老师们才拿下胸牌,神情麻木地朝校门外走去。施军赶紧上来搀住冯宁,掏出手绢摁住了他的伤口,冯宁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互相依靠地朝庄里走去。
这天晚上,施军没有回自己的屋子,黑暗中冯宁紧紧抱住了她,如果放纵也是一种沉沦,这次他决定再不放手!热吻从眼睛一路而下,施军发出似欢愉似幽怨的叹息,她感觉自己浑身软的像在云端,又带着秋天风吹麦浪拂过的轻痒,只能任那火辣辣地热情趟过醉人的高地最终汇聚到神秘的谷溪,当终于云破月出,满室只剩喟叹萦绕……
第21章 志在必得
74年是教育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的一年,年初整个机关又兴起一股“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不过很快这些都被淹没在5月份大港油田建立的喜讯中,此时整个石油系统统一的“革命思想”就是:“这乱、那乱、唯有油田开采不能乱”,与其对应的“革命行动”就是:“始终坚持生产一天都不停”。
虽然是零下几度的天气,但在野外却感觉异常寒冷,空旷的场地上飘扬着的“打井不停钻”的红旗被风吹的飒飒作响,让人看一眼就想打个哆嗦。与之不同的是固井施工现场,水泥散漫一地,泥灰漫天飞扬,上百个钻井队队员、后勤职工、职工家属都在用人工搬运、装卸固定油井时所要用到的近百吨水泥,现场干劲十足,热火朝天,有的队员大冬天就脱得只剩件线衣!等到收工号响起,人们才三三两两的向会站基地方向走去。
会战基地基本是由野外帐篷组成,生产、生活、供应一体,光野外食堂就有3个,一年来所有职工抗严寒、斗酷暑,目前已经完成了会站要求的开发井和钻井进尺的任务,做到了当年钻井,当年收益,现下工作基本进入收尾阶段,看来今年过年职工有望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张磊正掀起篷布走进自己的作业帐篷,帐篷是棉布做的,可以拆卸,一顶能睡十几个人,夏天揭开四周的篷布可以通风纳凉,冬天的帐篷中间就像现在一样烧着个铁皮炉,让大家可以取取暖做点热水喝。屋子里,工友邵国良正拿着厚厚一沓信发愣,听到动静抬头一看是张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张磊一见他这样就知道肯定有心事,就询问怎么了?他们干野外勘探的,可以说常年和工友同吃同睡,时时刻刻都在一起,谁家里有什么事那不说一清二楚,也是知之甚深的,同为知青同病相怜,真有家庭困难谁都不会坐视不理的!
邵国良苦涩的一笑:“这次不是家里的事,是我妹妹他们连的连长动员她嫁给‘新生人员’,①说只要同意领证就给解决农场户口!那个‘新生人员’是连队里放羊的,说是特别显老。”
“你妹妹同意了?”
“一开始看到人就不同意,站在一块像父女。后来指导员和连长轮番上来劝,不答应不行!信里说,证后来就领了,仪式都没有。我想给她汇点嫁妆过去,张磊,回头找来木材你帮我打点箱子家什。”
“没问题,钱上有不凑手的直说。”张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要说邵国良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弟弟、妹妹有个好去处,自己才选择了条件比较差的安徽,哪里想到事情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现在弟弟、妹妹都过的不好,他反而在这里工资也高,吃住不愁,这让他作为长兄非常愧疚,认为当初都是他的原因才造成妹妹最终迫嫁这样的局面。
当年,邵国良带着比自己低一级的弟弟、妹妹和所有69届毕业生一起来到泰山电影院听取各大生产建设兵团做的动员报告。报告开始就是看云南、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等地的记录片,影片中少数民族载歌载舞、原始森林的神秘魅力、草原上万马奔腾的风光、还有饱满如油画般色彩的喀纳斯让同学们如痴如醉。轮到各团上台报告,现役军人穿着一身神气的绿军装把兵团生活描述的让人热血沸腾!
“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一屁股坐下三颗草药,双手一把抓到的都是花生”这是云南兵团讲述自己的连队风光,富饶的物产让上海同学目瞪口呆;
“来我们连队每人都有枪!”黑龙江建设兵团如是鼓动,引来底下一片轰动;
“我们每个月给知青40斤大米补助。”新疆生产兵团也不落其后。
回到家中邵国良决定弟弟和妹妹分别去云南、新疆,自己来安徽。
谁成想过了半年弟弟来信就告知兄长,到了连队以后发现是在原始森林里找了处有水源的地方就地搭了房子,“芭蕉树叶当屋顶、野餐露宿为革命”,当时说的戍边为主,雨季就休息,旱季屯垦已经成为了一句空话。新建连队的任务就是开垦原始森林,伐掉当地的树木枯枝再种植橡胶树,口号变成了“先生产再生活”、“活着干,死了算”……
而妹妹去了新疆头几个月确实能领到40斤大米,可渐渐地变成30斤大米加10斤苞谷,后来大米的数量就越变越少。冬季的新疆,井台边的冰垛结的比井沿还高,一个不留神就会摔下去,女同志很多利用各种机会都嫁出去了,乌鲁木齐、库尔勒、尉犁县,只要能搭上的都走了,这导致兵团的女人越来越少。
现在兵团对于下放的女知青嫁人都是有限制的,原则就是必须内部消化,只要你嫁给内部人员,一律到农场录用为正式职工。邵国良的妹妹熬到现在拿着三十块五的工资,部队里百分之八十都是光棍汉,尤其是畜牧连更是常年在戈壁不见人,你说不嫁,考虑一下政治后果再决定!
炉子上的热水咕咕地冒着热气,帐篷里很安静,这几年来,每个春节钻井队员基本都是在旷野上度过的,他们在繁重地体力劳动之余有许多充裕的思想时间和天地,时至今日,更多的知青认清了现实不再盲从轻信,封闭的环境、传统文化的弥漫和一次次的运动也使他们以往奉若神明的一些东西、一贯恪守的准则都受到了冲击和质疑,家庭生活的压力和生存的本能让他们逐渐成为了沉默的群体,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因此觉悟,独立思考,终将发出真理的呐喊!
篷布又一次被掀开,同屋的工友吃完饭一拨拨的涌入,勾肩搭背互相开着玩笑进来,一屋子大老爷们,荒郊野地哪有什么娱乐?卧谈会内容自然离不开女人,说说后勤发劳保用品的漂亮物管员,讨论下哪家的媳妇肥硕的臀部,外号叫“小擦板”的赌咒发誓这次过完年一定要让工会赵大姐帮忙解决他的人生问题,让大家集中火线攻击。
“就你长那磕碜样,小鸡仔子毛都没有还想老婆了!”
“小擦板你个小赤佬摸没摸过女人的手啊!赵大姐回头给你介绍了,你别馋唾水嗒嗒滴啊!”(上海话口水的意思)
哈哈哈哈……
张磊也笑着枕着双臂躺在床上,搞野外勘探的找女朋友其实难也不难,不难是指他们因为是一线作业队,补贴和收入相对较高,所以当地周边的农民和机关的职工家属都热衷把他们作为女婿的首选,要是也是本地青年还好说,但像他们上海知青真的愿意和当地人结合的却也不多。
难是指他们一年之中在单位的时间并不多,要是有做半年歇半年那是烧高香了,自然就谈不上照顾家里,有这个人几乎可以算做没有,有的女青年搞对象便更乐意青睐做后勤或者机关的技术人员,条件好一点的一般挑挑拣拣也不大愿意找他们搞勘探的,除了不着家还嫌弃他们脏乎乎一身油,他们中间要是有成家的,配偶是坐机关的,大家伙嘴上不提,心理也是很羡慕的。
想到这个,张磊就想起第一次见到的卢秀贞,小小的院子到处都有让孤身在外的自己渴望中的温馨。也许寂寞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望靠近,自打那次敞开心扉的谈话后,两人要比一般知青亲厚点,经常交换一些书籍看,有时一些需要缝补的衣服他也故意谎称不会,借机让她帮忙好多看她一眼。
张磊心理有些热呼呼地想着她肯定是不讨厌自己的,如果主动些会有机会么?要怎么说她才会考虑呢!说自己会对她好,不让她受委屈,好像太干巴巴了……
这一晚辗转反侧,不时自我否定,他发现自己拿得出手的优势几乎没有,但他仍然打算先下手为强,害怕卢秀贞的好被发现以后,工会要是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必须在这之前让有心人知难而退……
第22章 花开两朵
和尚坐在土堆后,望着湖面的水生植物随着风的吹动上下颠伏,心情也随着颠伏不能平静,今天是他父亲的生日,他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想他,想要亲口告诉他——爸爸,我错了!
和尚的父亲曾任《文汇报》的记者,53年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蹲过一次监狱,平反后于57年反右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他只记得有一天一群人冲到家里把父亲带走了,很晚父亲才回来,换衣服时他偷偷看见父亲身上伤痕累累,而这样的事情隔不久就会发生。
从那以后,他在学校就成了黑崽子。以前弄堂里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开始回避他,在学校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孩子们之间总会发生点摩擦、矛盾,可只要轮到他,不管谁对谁错,只须关键时刻骂一声黑崽子,他就得灰溜溜地败下阵,以防别人骂出更难以招架的话来。
年少气盛,他也曾经反抗过,有一天他们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所有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角落,勒令他们低下头后,他们则在一边跺脚一边大声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泼墨水在他们身上。唱完歌,那些同学就要求满脸满身都是墨水的黑五类表态要与家庭一刀两断,和尚脾气上头,瞪着眼睛就是不说话,那群被激怒的红五类像发疯的狮子一样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
那天回家以后,和尚对上前欲帮他清理伤口的父亲恶语相向:“都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投生在你家!”从父亲眼中的难以置信和伤痛中,他感到一丝前所未有的快感,自此,他在外受的气便百分百地回报给了他的父亲。
就是这样,黑崽子也成了他的短儿,让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低人一等,根本不能跟别人较真。有时有人故意挑衅:“哎!我们批斗你爸爸,你心理难道就没有一点不高兴么?”明知是个套儿,也得顺着回答:“谁让他有罪呢?就该批他!”可是他的命运仍是没有一丝改变,处境没有一点儿好转,父亲在家里也越来越近乎透明,有时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难得的一丝融洽和乐,他都要远远地避开。
再到后来,他怎么做的呢?和尚想了想,噢!他开始带头批斗黑五类,跟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他写大字报揭发自己的父亲,晚上回到家更是要求母亲把父亲赶出去,而母亲只是悲伤地看着他。
终于有机会上山下乡,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上海,他对人热情开朗,处事圆滑玲珑,在上海的那些岁月似乎都离他越来越远!当他以为一切都已有所不同时,一场招工就又把他打回了原形,他想起那天去公社询问时,那个年轻的干部把他从头到脚的一通打量,然后嘴里轻飘飘地吐出一句:“黑五类子女还想走招工,赶车都没人要的。”
心上顿时像被插了一刀,一阵头晕窒息!是啊!此时他才明白自己有多幼稚!就算他政治运动搞得再轰轰烈烈,再以好勇斗狠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身份仍然是人人唾弃的黑五类子女。血缘关系又怎么会是嘴上说划清就真的能肃清的呢!以往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顿时就像影片倒带一样将他淹没,他觉得自己就是藏在水沟里的臭老鼠,只敢藏头缩脑地伸伸爪子,卑鄙、阴暗!
哎,父母怎么样了?插队到现在他只回去过一次,为了躲避父亲也是住在舅舅家,没脸写信回去,自从招工后,他便除了干活再也不关心其他事,每天把自己累的像狗一样,身体的劳累能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农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他觉出土地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风吹过,土壤似乎也飘出一股香气,天空清亮透明,田野池塘传出一阵鸣叫,多美丽啊!
“和尚!在哪里啊!快过来下!”赵佳扯着嗓子在喊!
沈杰站了起来,抬头看着那只落单的大雁,他将在此地用汗水洗刷他的一切污秽和耻辱!
——————————————————————————————————————————
卢秀鸿正从冲压车间回自己办公室,两年多来他跟着师傅把车间每台冲床的工艺原理都摸了个透,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