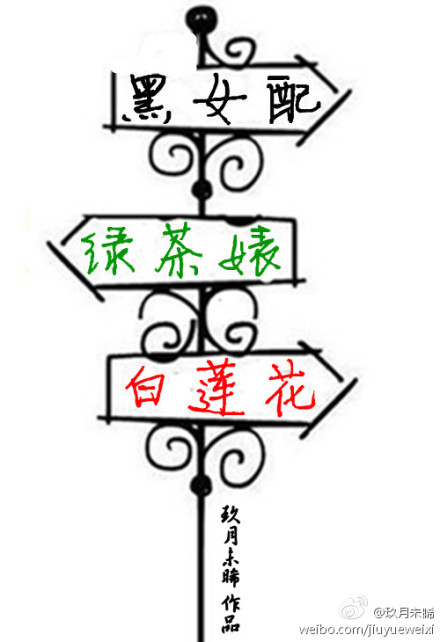�̲財����ϴ��-��11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ٿ�����������ʱ�����е����������ʺ�̰��ȴ��ôҲ���Ʋ�ס��������Ҳ�ز�����ȥ�ˣ���ȴֹ����ǰ��ƴ������Ҫ��ס���վ������е���ֶ�������ָ�䡣
��������Ⱳ��Ψһֵ�����ҵ��£�������û��һ���ٴ���������ʲô�˺������������¡�
�����ڹؼ�ʱ��ѧ��̯�����ģ����������ƿյ����Լ���һ˿�վ����Բд����������¡�
�������˿̽�̸�ij����������Σ����ǽ���Զ��������Զ�ľ��롣
����Թ��С����������������������Ϊ��1��Ψ����٣�һ��������á�
����ɤ����·���ʲô�������ܾ����ؿڷ��ơ�
������յ�����������θϻ�������������μ��DZߵ���Ϣ���Ѿ���̽���ˣ�����Ŀǰ����������ġ���
�����������
����������������Ŀǰ�ܶ�����������ˣ�������Ҳû��ʮ�־���ļƻ����ӻ����ϻ���������ֱ��ǰ��ƽ�ޣ���Ϊ����ȫ����������̽����һ�µ��µ������Ҳ���������ˡ���
������յ��������������ڻ�Ҫȥƽ�ޣ���
�����������������ǡ��Ҵ������������ݣ���취�˽���������հ֮��ĺ������������������ܱ��������ƣ�������õĽ����ͬʱҲҪ�������취Ū�����������������˽���٣�������١���
������յ���������������Ҳ�����˻��ԣ�������͡�������ͬȥ����
�����������侲����������Ҳ����ƽ�ޣ���հ��������±�ֻ�ЭZ��һ�˿���������˳�ؽ�����Ϊ�ҳ������ˡ����Z��������Ǽ��Զ�ڱߵء���
������ÿ�ζ����������Ҫ���Ի��߶����ʱ��������һ���ˮ�������ú��侲������
�����е�ʱ�����Ҳ���̲�ס����ĥ����ǧ����ô������Ϊ���ˣ���������ô���������ദ�ġ�
����һ���侲�Գֵ��˼��£�һ�������������˼��¡�
�������ðգ���֪���ˡ��һ����ھ����ȶ����ƣ���ʱ����㣬����Ҳһ��Ҫ���С�ġ���
�������������Э��˵�������Ͼ�������Z������л���������Ļ����������������ϣ�����۫��������֮��Ĺ�ϵ������Ҫ����ʲô���⣬���´��ȫ��Ҫһ����ɢ����
�����ϱ���Ҳ������ˡ�
�����������е㾪���˵���������������ҿ����Ǻ���Ҫ�ˡ���л��λ̧������
������ղ���ʧЦ��
��������һ�����⣬��ʱҹ��������������Ҫ�����϶�Ҳ������һ���ˣ����������һ·��������ЪЪ�ˡ�����ֻ��һ���ϣ�Ҳ�ò����������ڣ���ȥ������������齣������������Ϣ�գ�Ҳ����Щ����
���������Լ������г�����ȴû��ȥ�鷿�����dz���ҹɫ������������վ��һ�ᡣ
����������������ദ�ĺܺ������������������������ֺ�������Ϊ����֮��ľ���Խ��Խ�١�
����������֮�����ֱ���������ǿ�аĹ�ϵ���߽�֮������Ľ���Ҳ�վ�����������̫ƽ��ʧ��
����������ҹ������������ɫ���������������
��������Ҫ���������Ϻ��ϵ�ʱ�������𣬲Ż��Ȼ������ʱ������������
�����Լ������й�һ���ܰ��ܰ��������ˣ���һ��������ͷ���������¹���
��������dz�����ҹ��Ϊ˭��¶��������
��������֪������վ����ҹ��ֱ���������ף�������Ҳ�����ˡ�
����*
������������հ�ͺ���������������յ������п����dz����֣�����ʵ����ƽ���DZ߶��ԣ��������о���Ҳ��ͬ������һĨ�ڡ�
���������֮�£���Ȼ����Ҫ�췴����������ӽ���һЩ��
��������յ�������ʲô��Ϸ����
������հ����ؽ�һ���������˳�ȥ���߷ߺdz⣺����ô�����ȥ�ˣ����е��鱨��ֻ����һ�䡮̫�����˻��ԡ��������������˻�����װ����������Щ���������¶���̽���������
������������ú�������ֿ��ܣ�Ҫô�������ʵ�Ѿ����ز��ζ����������������������ң�����������Ҫô������ո�����û��ʲô�����ڼƻ���������ı��
������������һ���ܸ��и���������Dz��ܽ�����һ�����ж���
����ı���������鱾�������ľ����������У����ݵ��飬����Ⱦ�ǧ����л��Ȫ����Ǽ�����۷���һ�оͶ�ûϷ�ˡ�
�����úõ�һ����ɱ��Ū�������������Ľ�֣��������˵��ڰ����������������ܲ����˽����أ�
������հ�⻰�Ǹ�����˵�ģ�����Ҳ�ڳ���������ԶԶ����һ�ߣ����Ÿ���յ�������ţ�����ͷ�ĽǶ�ǡ����ס�˴���һĨ��Ц��
������������Ѿ����������İ�ʾ������Ȼ��һ���ͶԶԷ���֮��ǣ�����֮��ĵ�һ���¾ͺ�����ɱ֮����죬��ĿǰҲֻ����ʱ������
�����ô����ѵ�ʱ��Ҳ����հ��ˡ��̿͡�һ���������Խ�����Թŭ��
��100�¡����������
�������Ѻ���հ��û��ע������ı��飻������ü������Ҫ����ʱ�䣬Ŀǰֻʣ��һ�����ӣ��Ǿ��ǽ����������ܱ����ǵijdzؽṹ�Լ��������¶����Ǽ�DZ�֪���������Ļ����Z����л��Ȫ�Ͳ�����ô���������ˡ���
������հ�͵ص�������˵���������Dz��Ƿ��ˣ�������ô�����Ҹɴ��۫������Ǽ���ˣ���
������ʵ�Դ�¡ԣ������������ʼ������������˲�����ʵ���벻��������Ȼ�ܷ������ز���
������հ����������Ū����գ��ٲ�������ǧ��������վ��Ҳ��۫�����������������뵱�ʵۣ�Ҳ����Ϊ�˵��ϻ�λ�Լ��������ɣ�
���������κ������εļƻ�����һ����ô��˵���ϻ�λ����������������ס�ˡ���
�������Ѳ���ΪȻ��������Ǽ����������Ҳû�취�ɽ�������³���������ռ��۫��������������Ǽ�������Ρ����������Ȼ��С�����ܰѭZ���ȷ�������˽�����Ǽ��ȥ�����һ�����ã���
������հ������һ���������������Ѳ������������ģ�����Ψ�����²��ң�һ�����۫���������ġ�
�������̲�ס˵������֮ǰ���������ǰ�嶯��ɱ���ȵۣ���ʱ��ȫ�������ȵ���گָ��̫��רȨı����������ƽ������������Ҳ��������ް취���㾹Ȼ�����ҽ���ڽ�ɽ����Ǽ���ַ��ϣ���
������հ�Ͳ�û���������Dz�����Ǽ�ļ�ϸ�ˡ���
�����������������ж��Լ�����֮�⣬����Ҳ�䵭������
������˵������κ�����£�������֮�����ܹ�����Щ����ȫ������ѹ��ȥ���ȶ�ס����ƽ�ľ��ƣ�ȫ������Ϊ�ҵ�֧�֡���Ҳ��ϣ���Լ�һ�����࣬��Ϊ�������Ѷ�η��ηβ������ˮƯ����˵��Щ��������ָ���Ҳ��ð������𣿡�
������հ�������Ҳ����⡣��Ϊ�ҳ��������Ժ�Ҳ�Ե����𣬵�������۫��������δ������վ�������ҵ����飬�ܲ����������˰�Ū����
�����ۿ����˶�����Щ����������Ҫ��ִ������һ�������ͺ�������˵��������λ���£����������ꡣ��
��������������²�յ�������̵�վ��������
�������ۺ�ʱ�������϶���һ���Ƶ����ᣬ���Ķ��ŵĺͻ�̬�ȣ�����ֻҪ�Ƽ������;��÷·�ʲô�¶������ڴɸꡣ
��������Ҳ�·��Ȼ������ʱ�Ľ������գ����ǫǫЦ�⣬���������طֱ������������
����ֱ��������Щ������ŵ�����κ�����£�ˡ��ֱ�ԣ����´�Ҷ���ͬһ�����ϵ��ˣ�˭Ҳ�������á���Ȼ������ȫһ�£��ֺα���Ϊʹ���ֶ��ϵķ�����ִ����������أ���
������հ��Ц�������������㻹�Dz��ǵ��Լ���������һ�����ˣ�����ӵ���Ҳδ��̫Ͷ���˰ɣ��ѵ���Ҳͬ�⽫۫�����鱨������Ǽ����
�����������������벻����������Ҫ�����ǵ�Ŀ�IJ�����Ϊ����ȡʱ�䣬��ֹ�Z���ڴ���δ��֮ǰ�ص����ǡ���ô��������һ�����⡣��
�������ѵ�����ʲô����
����������ʮ��Ѱ��������˵������������κ���������ھͳƵ۰ա���
������հ�����㣡��
����������һ�仰������ʮ�ֻ�����ȴ˵����������Ŀ���������һʱ�ij����ȣ�����֪��˵��ʲô�źá�
�����侲Ƭ�̣���հ��˵����ʱ����δ���죬��ʱ�Ƶۣ���η��ڣ���
��������˵��������������һ�������ȵ��Ѿ������ˣ��������Ӳ�������̫�Ӽ�ȻҪ�����Բ��ѡ�����ô������٣��������������Ѱա����³Ƶۣ�������������ˣ���Ȼ����������Ӧ������װ�ģ���ô����վ���������±����ÿ�������̫�ӣ����ű��¼ݱ������ϱ�ɥ���Ǻξ��ģ���
������հ��˵�䡰�����������ֲ��ò����ϣ������Ļ������Ķ��ˡ�
����û�뵽���˿���˹�����ţ����������˷������⣬������������������ֵ��µ��ˡ�
����Ȼ����֪Ϊ�Σ�����������������֮�����ѵı���Ҳ������ͬ��ϲ��ϸ�����������Ե���Щ��ɬ���ʵ�����������������飬κ��������Σ���
������հ���˶���Ŭ�����Լ���Ҫ��һ�ǵ����Ŀ��������ͷ�ԣ���������Ҫ�úÿ���һ�¡���
����������ͬ���������������ǣ��ִ�֮��ֻ���뵽������⣬��óóȻ������ˡ������������Ӧ�ÿ�������Ŷԡ���
�������⻰˵�ġ�����ֱ���������Ϊ�Լ�����һ����
������հ�����������Ի����ã��ǾͶ�л�մ����ײ��ˡ���
�����ȵ����Ѻ���������հ��������������������������㵱��������հ�Ƶۣ���
�������������룬�������̫���ƻ���û���������õķ����ˡ���
�������������������ϵ����������ϻ����Ѫ������������κ����۫���鱨һ��������Ǽ�����϶��ǽ��ܲ��˵ġ������Ժ���Ҫκ�����������ֺο���Ϊ����¸����ַ����أ���
��������Ц������֮ǰ�����������˵�˲��ٻ��ϵIJ��ǣ��������ҿ�����һʱ���ߣ�ʧ��ɱ�ˣ�������������հ�Ƶۡ���Ҫ����հ����Ӧ�úú�лл������ˡ���
��������Ҳ��Ц������ô����Ҳ�������˵��ʵ�ڻ�����������հ�Ƶۣ����������Ǻ�����ϵ������������˵���ܱ�¡ԣ����λҪ���������¹�����������ˣ����־���������������ǡ�����۫���أ���
�������ѳ�ĬƬ�̣����ش���һ�ɣ���Ц������������ָ���˵���������ʮ�����ε��������������ˣ�����������ʵ�ڲ�������֮�٣�ֻ��������Ҳû��������˵��Ӯ�㡣��
����������˵������ȷʵ����հ��һЩ��������̫����ִ�ˣ�ֻ���ҵķ���������һ�����ݵġ�ֻ������Ǽ���������������羸ǧ������յ��˵�������Ȼ�����������ȥ�Ը�����հ���ܱ���Ѫ�е�����Ǽ�������Σ���������ʡ������
���������������ЭZ������̫ʦ���⣬ֻ����Ǽû����ô�����������֮ǰ�Ķ����Ѿ��������ˣ���������¶ս����ֻ�·��⻳�ɡ���
�������ѵ������μҵļҾ��Ѿ��������������ˣ�������ϧ�Z��û���������ˣ�����ץס�������ߡ���
��������ҡͷ��Ŀ�ⲻ����ɫ�س���Ժ�ӵ��еļ���÷������һɨ���������Ѿ��ǿտյ���������������Ӱ��
�������ջ�Ŀ�⣬˵����������Ҳ�ȷſ��ģ��ҿ�κ����ξ���ա��ҷ����Ƿ�������������ϣ���������Ƶۣ���������˼��ˣ�ֻ������������㡣��
��������ȴ��֪��������ʲô���IJ����ɵ�˵����Ҳֻ������ˡ���
�������˳��˹��õĴ��š�
�������������ѷֿ�֮��ص����Լ���ס�������������ƺ�˿��û���ܵ��������µ�Ӱ�죬�����������ù����ţ�����ʻ���һ����ʱ���Ļ�����ų���ȥ��Щ�µı�ī��
���������Ǽ����ӵij��ͣ��ƹ���ʶ��������������������Ц�ؽ����뵽���ҵ��䣬�������յ�����Ʒ��
����������һ��ȥ������������ӭ�������������������մ��ˣ���
������ɤ����ϸ�������Ǹ�̫�ࡣ
����������������������������
���������Լ��ʹ����������ڣ����������ݶ�����������ִӻ���С�������ͳ�����������һ��������
�������ұ������ԣ�������صģ�����Ȼ�Ǵ���������
����������ɫ���ӹ�һ˿���ɲ�����ɣ�˵������̫���ˡ�������Ȼ���������ô������ﱣ�£�Ҳ������ı�������˼ɡ�ֻ�����۷�������˭�����϶�����ȫ��һ��С�ľ���ɱ��֮������
�����Է����ѻ��������������Ǹ�����Ǻã���
������������������������������˵һ������ĺõط����ȵ��㽫�������úã���Ȼ���������磬������ǡ���
�����ȵ���������ϣ����������ӵ��ƹ������������������������ˣ��ƿ��Ѿ��뿪�����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