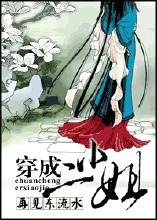С���Ѽ�-��3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С�㡭����
������������
�����������ţ���
�������������Щ���Կ��ڡ�������֮�䣬������Ҫһ��һԸ�ġ����Դӹ�үȥ���Ժ�С�����û���ἰ�����ڹ�ү��һ�仰����������˭Ҳ��Ȱ��������һ�����ү��С��������������
��������������ߣ�����ջ��ǰ�̾��һ�������ѻ�������ȥ��
����������С�㣬�Ұ����ͷ��������ɡ���
�����������š���
�����������³�ʮ�ߵ�ʱ����ֵ���ĺ�ʱ�⡣
������������ܶ�Ѿͷһ����������ˣ�����������Ž��������ţ�ȴ����ߵ����ӻ����ţ�����С�㻹û�ѡ�
�����������⼸�������ӣ�һ����Ҳ��֪���ܵ�����ȥ���ˡ���
���������ܶ����ֹ������Լ�ֻ������һ�������ӳ�ȥ��ˮ��
��������������ʯ�ף��ų���Ժ�ţ��������˰���������Ժǽ�DZ߹�����
��������������Ѿͷ�����������ʲô�����������ָ���������
���������ܶ�վס���������������ʲô���������ȥ�����أ���
��������������һ����ס���������ȸ����ң��������ﵽ������ô���£��������ֹ�ȥ�������ˣ���ô�����»�û����������
���������ܶ�����������������ڸ����������µ��˶����������˼ң���IJ�Ҳ�Ҷ�˵��Ҫ���ʣ���˵����Ҫ����Ų����������ʲôʱ��Ҳ˵����
���������������˼�Ҳ��������Ҳ�и����磬��Ͱ��ĵ��ž��ǡ���
���������������ﰲ�����ģ�������һ����Ҳ˵���������������ô˵�ƺ���ƺ����˴����ˣ�����˵Ҳ�ð����ˡ���
���������ܶ�������˸����ۣ��������أ�Ҫ�Ǹ����������ֻ࣬�������˼һ��ʹ�ȥ��
�����������ҵĺ����֣����ڶ�ʲôʱ���ˣ�˭��������Щ�ϻ������¡�������˴�������ʽ���õ�����Ҳ����������ʱ����Ҫ�ǽ��첻�о����죬���첻�оͺ��졣����С���ֲ��dz�ļ���ȥ����һ�쵽��Ϲ����ʲô�����ǻʵ۲���̫�༱����
47�ҿ�����ү��
��ʲô���첻�о����죻����ǰ�����Ӷ����ѵ����ǻƵ����գ���������߶�˼��䣻�����������ү��ôҲû���ţ����ܶ�ȴһ���̾���Զ�ˡ�
��������������һ����վ���������κΣ�������Ѿͷ������
������������Щ����������Ǹ���������û�˿����滰��������
��������������Ҫ�����ۼ������������ף��Ҿ�������������Ҳ�Ų�����ȥ�ġ���
��������������ҡҡͷ�������������ȥԺ���ˡ�
�������������Ƽ�����������ת�ۼ�������¹�ȥ�ˡ�
�������������X�����˼����£���һ���˴��ŵ�ʱ�����������ġ�������ż���������ģ������Ǹ�������ү��������û�˱��ˡ�
����������Щ�����Ѿ���������վ�����ˣ�������dz���ûվ����Ե�ʣ����ոշ���ǽ����ʱ�����ûһ�µ�����ȥ�������������ࡣ������һ���㿪ʼ�ۡ��������Ǽ����վ��һ�ᣬ��С��������ȥ���ָ������ף���һֱ������º����X�ſ����ܹ��µ���·��
���������ؼҵ���û���������������һֱû���������XΪ���Լ�����˼���룬����ʼ�����������Щ����վ��������Ͼ������زؾ���ֻҪ�����ǵ�һЩ�ģ����㶼������һ�顣Ҳ����������ȥ����һ�����뿪�ˣ����dz���������ҵ���Ҳ������
�������������dz��������ųԹ��緹���ã�������㻩��������һ�����죬�������˴������ţ������������˼���ǽ��������ιι����������
�������������X����������
���������������ء������˲��ͷ�����������������
������������λ��ү�����ʣ����ǣ����������X�ɲ�����Ϊ�����Ҹ������ķ����ھͷ�������
��������������ô������������ͳ����������˼����ͷ�������ĥĥ���ģ���ү������ʲôʱ�������㡣��
�������������X����һ�ᣬ˵������ү���Ե�һ�¡���
���������������ӱ�����������һ������������˳�ֱ�ӱ������������һ��糤����Ƭ����Ƭ��һ�ˣ��Ѿ���ĥ�ķ�����
�����������ͼݹ�ү�ˣ��߰ɡ���
�������������X��Ѻ������ʱ�����Ǹո����ĵ����£��������Ž����߳������ټ����ʱ�������Ѿ��ǽ��������ˣ�һ�����ɪɪ���������ϻ��˵�Ҷ�ӱ����תƮ������
�������������X����������ͷ�ϵĹ⣬��ǰ���˼�������Ϊ�ڲ������յĵ����д����ˣ������˺�һ���������Ӧ������Ĺ��ߡ�
��������������㣬������ȥ�ӱߣ����һ������Ϻ�һ���أ���
������������һ������ģ������м����ˡ�
��������ȥ�ӱߣ�
�������������X�����������ˣ����������Ӻ�ˮ���̣�Ϊ�˼ӿ���ˮ�Ĺ�ˮ���ȣ�ٚ�ݳ����ű㿪ʼ�ںӰ�һ������������̰�����Ȼ��ٚ�ݳǵĺӵ������ܳ��������������Ҳ����С�������ݸ�������˵������Щ��Ѻ�ķ��������ٺò�����������
�������������죬�͵�ǰ���ˡ���
���������Ǹ�Ѻ�͵Ĺٲ����һ����˵���������Ǵ��DZߺӵ�����ȥ������ʵ�ŵ㣬�����ˣ����������
��������һ�����ϵķ������ֽ�����һ�㣬���ǹٲ�������ʹ��˼�����ͣ��������ҿ��ŵ㣬��ô�������������أ���
�������������X�����ڵ��ں�����ţ����˻�������������Ҫ��������������ʱȴ�����ϳ����X������������Ŀ�⡣
��������������һ���������ʹ���������
��������������ģ��㻹�м���û���أ�Ҫ����������Ƕ��㿪������ˣ�ȥ�����˺ӵ�����ȥ�����������ࡣ��
��������������Ѻ���ķ����ߵ��������������ɲ��ǵ���Ѫù�ˡ�������û�뵽���˴��������㣬���ھ���Ҫ���������
�������������X�������˺ӵ����Ǻӵ�����ֻʣ��һЩ���ǵ���ˮ����ߵĺӵ��£�һЩ�������Ÿ첲�������������ࡣ
����������ȥ��������Щ��ͷ���������������ֽŶ����������ŵ㣬�ɲ�������һ�����ͱ���Է�����
���������ӵ��£��м�������������ת�˹�������˫Ŀ��ͬʱ�����˳����X�����ϡ�
�������������X���ޱ�������˹�ȥ��
���������ǣ�ԭ���������������Ȳ����ˡ�
�������������������ϳ�ͷȥ�DZߡ���һ����Ĺٲ�е���
�������������X����ͷ�����ֱ�������һ�ѳ�ͷ���˹�ȥ��
��������һ����������������
���������Ǹ���ļ����ø���ͷ�������ڣ�����Ҳ�ڲ��ϼ����࣬һʱ������Ҫ��ǰ�dz⣬ֻ���Ա�һ�������һ�Ѿ���ס������������ȥ����
��������������ȥ����
���������Ǵ������Ц��Ц�������˶�û������ˣ��㻹������������
�����������ٚ�ݳ���Ĵ�������ﳤ����һ��֧����ˮ���������ɽ������ɽ���ڶ��µ���Ȼ�ӵ�����;�����ɽʱ����������֧����Ľ�ˮ���롣��ˮ�ں��ٚ�ݳǺ����Ѷ��£�Ҫ���ڷ����˳�ĺ��꾰ʱ����Ӻ�ˮˮ��ƽ�����ӵ����Եķ������ؿ��ԴӴ����������ȡ�����Ҫ���ϲ��õ�ʱ����Ƶ����ˮ�����������ʧ��������˵���ͻ������������ߵĵ̰������������ˮ����ʴ��ˢ����κ�ˮһ�����Ǵֺӵ̱㿪ʼ��ٱ���������
�����������Ҫ����������������Ҫ����ӵ�����Ҫ��ʯ�������̣���Ȼ����̸�����ر��������������û�и�һ��ʱ����Բ��ɡ�
������������һ�����ȥ�������X�������⼸�죬��ʵ˵�ò��ã�˵��Ҳ������
���������õ����Լ����������������������ʪ�ĵ������ˡ������ǣ�����ż����ע��ʱ�����м�����������Ŀ�⳯���������
��������������������������ʵ�ʱ����ͷ����С������һ���������������ڿ���������ЪЪ���ˣ�˵��ЪϢ����ʵҲ��������ҿ�ƽ��ϯ�ض������ȿ�ˮ�����Χ��һ��˵Щ�л���
�������������X��������Ķ��ң�����һ�������ĵ�����������
������������������������˵ʲô��˵����ô���֡���
��������������ʲô����֮ǰ����˵��˵������ٚ�ݳ��ؼ�����ү��ʼ�ڳ��������ˡ���
�����������ؼң��ĸ��ؼң���
���������������ĸ��ؼң��ͳ������ٍ�����ү���ϡ���
�����������ԶԶԣ���Ҳ����˵�ˣ����Dz�֪�������Ǽ٣���
������������м٣��˼�ý�Ŷ��Ѿ������ˡ�����
����������Զ���ij����Xվ�������������ϵ����ڣ�����һ�ڲ趼û�ȹ���
��������������Ŀ��ˡ�
�����������������źӵ���һ·�߹�ȥ��ԭ��һ���г�Ƭ���ֵĵ̰�����ʱ����һ��ľ���ӣ�������Ϊ�����������ĵط���
����������ʱ����ûʲô�ˣ�ֻ����һ����ͷ��������������Ų���ӡ�
�������������X�߽�ȥ����һ��ˮ�ȣ�������һת����յ��ݺ���ȥ�ˡ�
�����������治Զ�������ŵ������˼�״æ������ȥ��
���������ݺ������Ӱ˶���һЩľ����Ӳݣ�����������������������������ס���չ⡣��
��������������С������������˼�����߬�������
�������������أ���
���������ողſ���ת�������
������������һ������ϸϸ���Ĵ������ֿ����ָϽ���ͷ���˿�ͷ����Щ�����������մ�����Ƥʱ����Ȼ��������ǰ����һ��������һ��ʯͷ����ij����XһԾ���������䣬һ���ֱ�ɾ�����ظ�������˺��ܡ�
�����������˲������ŵصɴ��۾���˫�ֻ�û���ü����Ϻ�����ֱֱ������ȥ��
����������������һ����ɵ�����ӣ��������ŵ��Ѿ�������ľ����
�������������X��������Ƭ���������������������˳�ȥ��
��������ɱ���Ӻ�������X�ɲ�����ô����������ġ���������Ҫ������û��ô��
����������Ȼ�������ˣ��������Ӳ���Ҳ�ù��ˡ���Ҳ������������Ҳ�����������������º���Ҳһ˲���Ҳ���ˡ�
��������������������
���������ظ�����ǰ��������ʱ��ͣ����һ�����ӣ������η���˰��죬�ſ�����С��������������������ƴ��������˳�����
��������������������磬�����ŵ��˰��³�ͷ�������������ʼ���ˡ�
�����������������ſ�վ��һ�������лܶ�����������������֡���
����������ŶŶŶ�����ˡ����ܶ��Ͻ��ܹ�������С�㣬����һ�㡣��
���������������һ��������������һ���������ƹ�IJ�������������һ�����������������С���ȥ�����ۡ�
�����������߰ɣ����ƹ�õȼ��ˡ���������˵����
�����������Ӵӳ�����������ߣ�����һ���ֽ�ת�������걳��֡��ȹ��˺�������ʯ�ţ������һֱ�������������ˡ�
���������ܶ��Ѿ��þ�û�г����ˣ����һ�������о�ʲô�����������ˡ�
�������������ڽ����ԣ��˷ܵغ�������С��С�㣬�DZߺ���������ˣ������ú��棬����Ҫ��Ҫȥ��������
����������С��С�㣬�һ����������������˶������ǵȻ�����Ҳȥ�������ò��ã���
�������������������������أ��DZ߶����˹ҵ����ˡ���
�������������������۾��������������죬�����ܶ�˵������С�㡣��
�����������ҿ�����ү�ˡ�����
48�������£��ޣ�
����������ү�������ں����ء������ܶ���һ���ڣ������ͺ��ô��Լ�һ��������ˡ���Щ���Ҷ�С������������С����ǰ���ү�����֣������¿ɺã��������ӿɲ��DZ�¿����һ��ô��
����������С�㡭����
����������������
����������ͣ�Ρ���
�������������η����������ӷ��������������ã��������һ˫�˰����ַ����˽�����
��������������������������������˽Ρ�
����������С�㣿��
����������������������߹����������ߵ��ű��ϡ�����������ȥ�����ɺԵĺӵ���վ�˺�Щ������ˮ�Ĺ������ۣ���Щ�������ƾɣ��������������������Ȼ���ذ�ʯ�����ࡣ
����������ʯ�ŵ��£�˫���������ӣ���һ���ɸɾ����ij����Xվ�������üĿ�赭��Ҫ�Ǻ���������������������������������һ��������������һ�Կ��羰��������ʿ��
�������������������űߵʹ���ͷ���������¶����һ�ξ������ɵIJ�����һ˫����һ˲��˲���������������ˡ�
����������������һ���Ƶ������ģ������������������������İ�Ĵ�ʹ����Щѹ�����Ŀڵ�ʹ�������̽�������������֮ǰ����������������ʹ�ֿ�ʼϯ����������ʹ������������������ʹ�������鳦�ϡ���һ��ѹ���Լ����ؿڣ������۾�ȴ�������������ˡ���������������Щ�����������ۣ��������ѱ�������ı�ʹ���˺;���������һ��������ȫ����ǰ�������ϣ����ǵ�ͷ�����������е���Ͱ��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