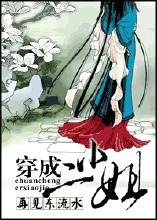穿成娇弱美人后,我嫁人了-第7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云奏伏于叶长遥怀中; 感知着叶长遥轻抚着他背脊的手; 思绪甚是清明。
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正在恶化; 他急需叶长遥的心头血。
过了足有半盏茶,他的咳嗽方才止住。
他将下颌抵于叶长遥肩上,一手圈着叶长遥的腰身,一手把玩着叶长遥的发丝,不发一言。
叶长遥亦不发一言,只不断地轻抚云奏的背脊,云奏又瘦了一些,脊椎骨极为磕手。
打破沉默的是倏然而至的一把嗓音:“客官,你们的菜来了。”
叶长遥下了床榻去,打开房门,从小二哥手中接过食案,将三菜一羹从食案端出,置于桌案上,才将云奏抱到了桌案边。
他先为云奏盛了一碗虾仁蘑菇豆腐羹,又抬手覆上了云奏的喉咙,关切地道:“疼么?”
云奏摇了摇首,并不去吃虾仁蘑菇豆腐羹,而是将双手拢在衣袂当中,状若无事地用丝帕拭去了其上的血污。
咳嗽了这许多的时候,喉咙怎会不疼?
自己显然是明知故问。
叶长遥反省着,见云奏摇首,并未揭穿,只是指了指那碗虾仁蘑菇豆腐羹,道:“吃罢。”
“嗯。”云奏一手端起瓷碗,一手执起调羹。
一口热乎乎的虾仁蘑菇豆腐羹滑过喉咙,让他的喉咙好受了些。
他并未意识到单单一个“嗯”已将他的谎言揭穿了。
叶长遥欲言又止,他想教云奏勿要逞强,但不逞强还能如何?
他分明不久前才渡了内息予云奏,可云奏仍是咳嗽不止。
他索性埋首用膳,但酸甜的糖醋小排入口竟无半分甜味。
片刻后,他终是问道:“我要如何做,才能缓解你的痛楚?”
云奏抿唇笑道:“我又不是一日十二个时辰皆在咳嗽,你毋庸这般忧心忡忡。”
他的嗓子很疼,不长的一段话直教他觉得自己的嗓子已被撕裂了。
他并未表现出任何的痛苦,甚至还夹了一块苦瓜酿肉来吃。
叶长遥阖了阖眼,继而一把扣住云奏执着竹箸的右手手腕子:“我们这便启程去观翠山罢。”
云奏问道:“我们尚未查明真相,此时离开,阮公子会如何?樊公子昏睡不醒,我们要将他丢在这客栈么?”
“与我何干?”叶长遥目中盛满了心疼,“三郎,我一生所愿便是你平平安安的,你勿要以为我并未拆穿你,便不知你咳血了,长此以往,任你是绿孔雀,亦会丧命。”
“哪来的长此以往,待查明真相,我们便能启程去观翠山了。”云奏本想糊弄过去,但一触及叶长遥的双目,不觉心虚了。
“三日,至多三日。”叶长遥正色道,“三日后,不管真相是否水落石出,不管那阮公子会如何,不管樊公子是否能转醒,我们都必须启程去观翠山。”
叶长遥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强硬,逼得云奏无力拒绝。
一日后,九月十六,樊子嘉仍未转醒。
两日后,九月十七,黄昏时分,外头骤然电闪雷鸣,暴雨旋即倾盆而下。
云奏被惊醒了,一坐起身来,便瞧见了守着他的叶长遥。
叶长遥揉了揉他的额发,柔声道:“我去了一趟丹谷寺,寺中的僧人皆道善安出身于丹谷镇阮家村,善安本人亦坚称自己出身于丹谷镇阮家村。”
全无线索。
明日,三日的期限便到了,该如何是好?
云奏苦思冥想着,问道:“那些僧人有何可疑之处?”
“我所见到的僧人并无可疑之处。”叶长遥补充道,“但我并未见到住持大师。”
“仔细想来,我们从未见过住持大师,听闻住持大师便在寺中,那主持大师是故意躲着我们,亦或仅仅是凑巧而已?”云奏蹙眉道,“无论如何,我们须得见一见那住持大师。”
叶长遥瞧了眼窗枢,道:“现下外头狂风暴雨,倘若主持大师是故意躲着我们,他定然料不到我会去而复返。”
“我与你同去。”云奏一把抱住了叶长遥的腰身。
叶长遥不忍拨开云奏的手,为难地道:“你身体不好,以免受寒,还是勿要与我同去了罢。”
“不行。”云奏放心不下,坚持道,“我定要与你同去。”
叶长遥百般无奈地道:“好罢。”
他为云奏穿上蓑衣,戴上斗笠,又蹲下了身去。
云奏会意,爬上了叶长遥的背脊。
不过半刻钟的功夫,俩人便已到了丹谷寺前。
善安正在打扫正殿,见得俩人,忍不住问道:“樊施主可安好?”
云奏满面笑意地道:“你那樊施主自从磕伤了额头后,便再未醒来过,你说他是安好,还是不安好?”
怪不得樊子嘉并未上这丹谷寺来缠着自己。
善安的心脏“咯噔”了一下,不知怎地想起了樊子嘉唤他“阮郎”的模样。
他又问云奏:“樊施主为何昏迷不醒?”
云奏淡淡地道:“不过是郁结在心罢了。”
郁结在心,是由于自己的缘故罢?
善安心生愧疚,又听得云奏道:“住持大师在何处?”
“师父应该已歇息了。”他答罢,还要再问,但云奏与叶长遥竟然在弹指间无影无踪了。
他们恐怕并非凡人。
既是郁结在心,即便樊子嘉转醒,亦不会再来缠着他了罢?
于他而言,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但樊子嘉何时才会转醒?
那厢,云、叶俩人去了寮房,一间一间地搜寻,其中一间寮房最为宽敞整洁,想必便是主持大师的住处了,然而,住持大师却不在里头。
俩人正立于寮房前,云奏鼻尖猝然飘过了一丝气味,他当即拍开了门,细细去嗅。
叶长遥并未发觉这寮房内有甚么异样的气味,却突地听见云奏道:“那主持大师并非凡人,亦非妖怪,应是这丹谷峰的山神。”
话音落地,俩人忽闻一声“阿弥陀佛”,紧接着,那主持大师踏入寮房内,又将房门阖上了。
住持大师不紧不慢地到了俩人面前,慈祥地笑道:“绿孔雀,倒是被你看穿了,不过你母亲本就是上古神兽凤凰,你继承了你母亲的血脉,能看穿贫僧的身份倒也不稀奇。”
云奏未及开口,那住持大师又道:“贫僧全然感受不到你的内息,你是走火入魔了罢?”
叶长遥闻言,顾不得阮星渊与樊子嘉,急声道:“大师可知如何才能助三郎恢复道行?”
主持大师答道:“容易得很,得到他母亲留下的凤凰羽便可,至于那凤凰羽现下在何处,贫僧却是不知,除却凤凰羽,理当还需要一味引子……”
听到此,云奏紧张万分,生怕住持大师说出那味引子便是叶长遥的心头血。
幸而,住持大师接下来说的是:“至于那味引子为何,贫僧亦不知。”
云奏暗暗地松了口气,这是他的秘密,决不能被叶长遥知晓。
叶长遥其实已对凤凰羽起疑了,不然为何从云奏的表现瞧来,云奏根本不想去观翠山,取凤凰羽?他们本该先去取凤凰羽,再下观翠山帮樊子嘉找阮星渊才对。
听得主持大师所言,他登时放心了下来。
云奏窥了眼叶长遥的神情,才直截了当地问道:“大师,善安可是樊公子的阮郎?”
住持大师并不隐瞒:“善安便是樊施主的阮郎。”
云奏又问:“阮家村中的那五人可是你安排的?”
住持大师颔首:“你猜得不错。”
云奏质问道:“你如是做所图为何?”
“世间万事,有失才会有得,善安得到了千年灵芝,失去了记忆,在这丹谷寺中出家为僧,很是公平。”主持大师慈眉善目,拨弄着佛珠,道,“这乃是善安自己的选择。”
云奏了然地道:“难怪他记不得樊公子了,却原来是你取走了他的记忆。”
“此事已尘埃落定,善安已是佛门中人,红尘之事,与善安无关,你们且快些离开罢。”主持大师手指一点,俩人被迫出了寮房。
与此同时,有一把声音乍然钻入了云奏耳中:所谓的引子,便是你身边这位施主的心头血罢?
他霎时如坠冰窖,肌肤寸寸生寒,寒气侵入骨髓,使得他几乎能结出一层霜雪来。
他抿了抿唇瓣,问道:“你要能否放过善安?”
半晌,并无回复。
叶长遥抬掌一拍,那寮房门纹丝不动。
他唤出“除秽”,正要劈去,那寮房门却自行敞开了,主持大师转瞬到了云奏面前,道:“你割下一块孔雀肉来予贫僧,贫僧便将善安的记忆还他。”
云奏还未作答,他身边的叶长遥已执剑护于他面前,厉声道:“你休想伤三郎一分。”
住持大师并不相逼:“绿孔雀,你且慢慢考虑罢。”
云奏在叶长遥身后道:“你已是山神,得了孔雀肉有何好处?”
“山神?”住持大师冷笑道,“贫僧被囚禁在这丹谷峰,若是得了你的孔雀肉,贫僧便能下丹谷峰,出丹谷镇。”
“山神守护着这一方的安宁,乃是你的职责所在,你若是下了丹谷峰,出了丹谷镇,此地该如何是好?”云奏猛地咳嗽了数声,面色涨红,“你既是山神,便不该逃避自己的职责。”
住持大师讥讽地道:“你可知千百年被囚禁于此的滋味?”
“我不知千百年被囚禁于此的滋味,但是我知晓你定然犯了错,不然,即便你乃是山神,亦不会连丹谷峰都下不了。”云奏安抚地抱了抱叶长遥的腰身,而后从叶长遥背后出来了,与叶长遥并肩而立。
住持大师坦白地道:“贫僧的确犯了错,但主要责任并不在贫僧,三百年前,这丹谷峰山洪暴发,是降水过多的缘故。”
“丹谷峰山洪暴发之时,你却不在丹谷峰?”云奏见住持大师变了面色,便知自己猜对了。
他担忧地道:“我若是割下孔雀肉予你,我怎知你不会弃这方圆百里的百姓于不顾?”
未待住持大师答话,他又道:“被困在寺中的凡人除了阮公子还有几人?”
住持大师摇首道:“除了善安,再无一人,世人大多只顾自己,来这丹谷峰求取千年灵芝者甚众,但愿意付出相等代价者,百年间,惟有善安一人。旁的僧人皆是自愿出家为僧的。”
云奏思忖须臾,有了决定,向着住持大师确认道:“我若以孔雀肉交换阮公子的记忆与自由,你可否答应我守护这一方平安?”
于住持大师而言,自己的自由自然较善安要紧多了,立即道:“可。”
“那便好。”云奏变出一把匕首来,正要将自己小臂的肉割下一块,却是被叶长遥制止了。
叶长遥抓着云奏的手腕子,肃然道:“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腥甜直冲喉咙,云奏拼命地压下了,又反过来安慰道:“我无事,不过是割下一块肉来罢了,过几日,便能长齐全。”
言罢,他眼尾余光中映入了一个人,正是樊子嘉,樊子嘉浑身透湿,到了云奏与叶长遥面前,道:“我已向善安师傅道别了,我不要找阮郎了,我明白我的阮郎已不在了,云公子、叶公子,请带我回家罢,我想念阿姊了。”
樊子嘉身后不远处,立着善安,善安同样浑身透湿,僧袍黏在身上,瞧来较樊子嘉更为狼狈。
善安面无表情,扫了眼樊子嘉,便转身离开了。
云奏端详着樊子嘉,承诺道:“我定会将你的阮郎带回来的。”
而后,他又对叶长遥道:“叶长遥,松手。”
叶长遥不肯,俩人僵持不下。
樊子嘉一派天真地道:“我甚么时候能回家?”
云奏劝道:“夫君,左右不过一块孔雀肉罢了,你便忍心见樊公子与阮公子生离么?”
叶长遥被云奏逼得眼眶一红:“但我更不忍心见你从身上生生割下一块肉来。”
“我无事,不会太疼的,你可记得我曾被贯穿心脏,不过割下一块肉罢了,哪里会有心脏被贯穿疼?”云奏以左手掰开叶长遥的手指,一指,二指,三指……
正要去掰第四指,叶长遥竟是将手指从云奏的手腕上撤走了。
云奏仰首去瞧叶长遥,叶长遥立在雨水中,满面痛楚,叶长遥将斗笠让予他了,因而现下并未戴斗笠,雨水冲刷着叶长遥的面孔,叶长遥恍若正在流泪,叶长遥的发丝胡乱地黏在了面上、脖颈上,叶长遥明明生得阴鸷,能止小儿夜啼,但眼前的叶长遥却脆弱得如同三岁的孩童,甚么都做不得,可怜至极。
“抱歉。”他踮起脚尖来,于叶长遥唇上印下一个吻,方才利落地将匕首尖没入了自己的小臂。
叶长遥的唇瓣空前未有的寒冷,与雨水一般。
匕首一动,一小块肉便带着血液脱离了小臂。
他并未感觉到疼痛,因为他脑中挤满了叶长遥唇瓣的寒意。
他定了定神,将那一小块肉交予住持大师,道:“我信大师不会食言,望大师勿要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