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阁寺-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己却马上也碰撞上了。两人拐了个弯,登上台阶就来到了楼上——
①石川五右卫门:日本桃山时代的大盗。
从地窖般狭窄的台阶上来,置身于厂麦的景观,紧张顿时松弛,舒快极了。我们尽情观赏叶樱和松的景致、耸立在对面鳞次栉比的平安神富的郁葱森林的景致、京都市街尽头的朦胧的岚山,以及北方、贵船、卖里、会见罗等群山的姿影,尔后才像个寺庙弟子的样子,脱掉了鞋袜,恭恭敬敬地进太庙堂里。昏暗的佛堂有二十四铺席宽,释边像摆在中央,十六尊罗汉的金眸子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里是五风楼。
南禅寺同属临济宗,但与相国寺派的金阁寺不同,它是南掸守派的总寺院。我们就是在同宗异派的寺庙里。我们两人却像普通中学生一样,手拿说明书,一路观赏着色彩鲜艳的壁顶图案,据说这是出自狩野探幽守信②和土佐法眼德悦③的手笔——
②狩野探幽守信(1602-1674):江户幕府的御用画师。
③土佐法眼德悦:生卒年月不详,据传擅长画墨画观音像。
壁顶的一边,画了飞天弹琵琶和吹笛子,另一边画出了手持白牡丹振翅飞翔的迦陵频枷。它是栖息在天竺雪山的妙音鸟,上半身呈丰满的女子的姿态,下半身成鸟。另外,壁顶中央画了一只凤凰,与金阁顶上的鸟是友鸟,但与那只威严的金鸟毫无相似之处,却像是华丽的彩虹。
在释边像前,我们跪下,双手合十,然后走出佛堂。但是,我们舍不得离开接上,便倚在上来时攀登的台阶旁边朝南的栏杆上。
不知怎的,我感到仿佛有个美丽的小小的彩色旋涡似的东西。我想,它可能是刚才看到的壁项图案的五色斑斓的残影吧。凝聚了丰富色彩的感觉,就像那只迹陵频枷鸟,隐栖在嫩叶丛中和郁葱的松枝上,只让人从缝隙看到它华丽的翅膀的一端。
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眼皮下,隔着马路立着一座天授庵。从简朴地种着许多矮树的寂静的庭院,穿过用四角石角接角地铺成的一条小曲径,通到了敞开着拉门的宽阔的客厅。可以清楚地看见客厅里的壁龛和百宝架。这里似乎经常用作举办供神佛的献茶,以及供人租用举办茶会,所以铺着鲜艳的绯红色地毯。室内跪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这些东西。
战争期间,是不会看到穿着如此华丽的长袖和服的女子身影的。假如身穿这种盛装出门,半路上定会被人指责,不得不折回家中。她的长袖和服就是这样华美。虽然看不见精细的花纹,却能看见绯红腰带上的金丝线闪闪发光,夸张地说,映得四周熠熠生辉。年轻貌美的女子端庄地跪坐着,她那白皙的侧脸被浮雕出来,令人怀疑地是不是真正的活人。我极度口吃地问道:
“她究竟是不是活着呢?”
“刚才我也这样想。真像个偶人啊!”鹤川目不转睛,将胸口紧紧压在栏杆上,回答说。
这时,只见一个身穿陆军军服的年轻上官从里首走了出来。他彬彬有利,正襟危坐在距女子近一米的地方,面对着女子。两人纹丝不动,久久地相对而坐。
女子站起身来,在廊道的昏暗中平静地消失了。良久,女子端着茶碗,折了回来,微风吹拂着她的长和服袖子。她在男子的面前劝茶。按茶道的礼法功过淡菜以后,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跪坐下来。男子似乎说了些什么,却怎么也不呷一口茶。这段时间令人感到异样的长,异样的紧张。女子深深地低下头来……
此后发生的事情实是令人难以置信。女子依然保持着端庄的姿势,冷不防地解开了衣领口。我的耳朵几乎听见了从坚硬的腰带里侧拉出绢带的春市声。莹白的胸脯袒露出来了。我倒抽了一口气。女子公然用自己的手将一只莹白而丰满的乳房托了起来。
主官手里端着一只深黑色的茶碗,膝行到女子的面前。女子用双手操着乳房。
这些情景,不能说我都看到了,但这一切我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呈现在我眼前的,仿佛是温馨的白乳汁喷在黑色茶碗内侧的冒泡的绿茶中,仿佛看见已经济完而残留着奶滴的情形,白乳汁弄混浊了寂静的茶水而起泡沫的情形……
男子端起茶碗,将这奇怪的茶一饮而尽。女子莹白的胸脯也被隐蔽起来了。
我们两人脊梁发硬,看得人神了。后来我们按顺序回忆,觉得可能是怀了上官的孩子的女子,与出征的士官举行诀别仪式吧。然而,这时候的感动,拒绝了做出任何的解释。由于过分注意,反而看不见,过了很久,待意识清醒过来时,才发现这对男女不知什么时候从客厅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块宽阔的绯扛地毯。
我看见了那张洁白的浮雕般的侧脸和那无与伦比的莹白的胸脯。即使女子离去以后,那天剩下的时间,或第二天、第三天,我还执拗地寻思着。的确,那女子就是复活了的有为子啊!
第三章
父亲一周年忌辰到来了。母亲没想了一个难以想像的方案。正逢义务劳动总动员,我不能返回故里,母亲就打算亲自将父亲的牌位送来京都,请求田山道诠和尚为旧友忌辰诵经,哪怕诵上几分钟也好。她压根儿没钱,只好求他看在清分上。于是她给和尚发了一封信。和尚答应了,并且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我。
我并不是带着欣喜的心请听取这个消息的,迄今我故意省笔不提有关母亲的事,这是有其原因的。因为我打心眼里不想触及母亲的事情。
我不曾--一句也不曾就一件事责备过母亲。估计母亲也没有察觉到我烧得那件事。但是,从此以后,我心中就一直不原谅母亲。
事情发生在我上东舞鹤中学,寄居在叔父家中,第一学期放暑假,我初次回故乡省亲的时候。那时母亲的一个名叫仓井的亲戚在大饭的事业失败后回到了成生村,他是人赘女婿否证科学理论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主张用“有用”,“有,他的妻子不让他踏入家门。妻子未消气之前,他无奈只好寄住在我父亲的寺庙里。
我们的寺庙蚊帐很少,估计父亲的结核病不大会传染了,母亲和我就同父亲共用一床帐子,如今再加上仓并。我记得,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深夜里,沿着庭院的树木,我仿佛听见无数的蝉发出了知了知了的短促的悲鸣,飞来又飞去。大概是这种声音把我惊醒了。海潮怒吼,海风掀起了黄绿色的帐子的下角。帐子的飘动异乎寻常。
海风把帐子吹得鼓胀起来。帐子过滤着风,无可奈何地飘动着。所以被风刮成堆的帐子的形状,并不是风的忠实的形状,随着风势渐弱,棱角也消失了。帐子下角摩擦着铺席,发出了像矮竹叶摇曳似的声音。然而传到帐子的不是风吹的动,是比风吹时更轻微的动,是泛起涟漪似地扩展到整床帐子的动。这种动,使粗布帐痉挛,从内侧看见的巨大的帐子的一面,仿佛洋溢着不安的湖面。不知是湖上远方的船激起的浪头,还是已远去的船留下的余波的反映……
我把惶恐的目光投向动的源头。于是我感到好像一把钱子猛扎进了我在黑暗中睁大的眼珠子里。
四人挤在极窄的帐子里,紧贴父亲躺着的我,翻身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父亲挤到一个犄角上。我和我所看到的东西之间,隔着布满皱纹的白床单,我背后就是把身子曲成一团熟睡着的父亲,他的鼾声直接灌进了我的衣领口里。
我所以发现父亲醒了,是因为父亲压住咳嗽以致呼吸不规则,触到了我的后背。这时候,突然间,十三岁的我睁大的眼睛被一个巨大的温吞吞的东西遮挡住,什么也看不见了。旋即我明白了。原来是父亲的双掌从背后仰了过来,遮挡住了我的双眼。
这双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双无与伦比的巨掌。它是从我背后绕过来,突然捂住我的眼睛,把我所看到的地狱遮盖起来了。这是来世的巨掌。不知是出于爱、慈悲还是屈辱,好歹即时中断了我所接触到的可怕的世界,并将它完全埋葬在黑暗之中。
我向这双巨掌微微点了点头。父亲从我小脸的颔首,立即明白我是谅解和同意了。然后父亲将手掌移开……手掌移开以后,我如实地按照手掌的命令,继续坚持闭上眼睛,直到清晨室外令人目眩的阳光透进了我的眼帘。我通宵达旦未能成眠。
……不妨回忆一下,后来父亲出殡,我虽急于要看看父亲的遗容,却没有流一滴眼泪。不妨回忆一下,手掌的羁绊,与父亲的死一起被解开,我通过只顾着父亲的遗容确认了自己的生。对于这手掌,这人世间称为爱情的东西,我如此忘不了要忠实地复仇,而对于母亲则有别于那不可饶恕的记忆,我是从未曾想过要复仇。
……住持写信告诉我:母亲准备在父亲一周年忌辰的前一天来金阁借住一宿,并已得到允许了。住持让我在忌辰当天也向学校请假。我每天都得参加义务劳动,忌辰头一天我想到即将返回鹿苑寺,心情就沉重起来。
鹤川有着一颗透明而单纯的心,他为我将同阔别许久的母亲相会而感到高兴,寺庙的师兄弟对这件事也抱着一种好奇心。我憎恨贫困寒碜的母亲。我苦于向亲切的鹤川说明自己为什么不愿同母亲会面。工厂下班后,鹤川就急忙挽着我的胳膊说:
“喂,咱们跑步回去吧!”
说我压根儿不愿同母亲会面,也未免太夸大了。我并非不想念母亲。我只是讨厌当众公开表露对亲人的爱情,也许只有这种讨厌才促使我设法制造种种的借口。这是我的坏性格。如果以种种借口可以使正直的感情合法化还好,可是有时候,自己的头脑里编出来的无数的理由,把连自己意料不到的感情也强加给我自己。这种感情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光就我来说,某些方面有其正确的成份。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值得嫌恶的人。
“何必跑呢,真没没子啊。太费劲,拖着两腿回去就行了呗。”
“这样,令堂就会同情,你打算撒娇啊!”
鹤川的解释总是这样,充满了对我的误解。然而,他一点也不使我讨厌,并且成了我所必需的人。他的确是我的善意的翻译,把我的语言翻译成现今的语言,他是我难得的朋友。
虽然京都没有遭到空袭,但我却看见了这样一个场面:有一回,奉工厂之命出差,一个职工手拿飞机部件的订货单前去大阪总厂时正好遇上空袭,他的肠子露了出来,被人用担架抬走了。
--母亲来了,正在老师的房间里谈话。我和鹤川跪坐在初夏夕阳映照的走廊上,招呼一声:“我们回来了!”
老师把我一个人叫过屋里,当着母亲的面说了这孩子干得不错之类的话。我低下头来,几乎没有着母亲的脸一眼。我瞥见她穿着褪色的藏青棉布劳动裤的膝以及放在膝上的龌龊的手。
老师告诉我们母子俩可以退出房间了。我们再三施了礼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小书院朝南,面对中院的五铺席宽的储藏室就是我的房间。剩下我们两人在这里的时候,母亲哭了。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所以我能够冷然处之。
“我已经是鹿苑寺的弟子了,我学成之前,请您不要来看我!”
“我知道。我知道。”
我用这种残酷的语言来迎接母亲,心里沾沾自喜。然而母亲却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感受,也没有任何抵触,实是令人心里恼很。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母亲超过门坎来到我的中间,那么连想像我都觉得太可怕了。
母亲晒得黝黑的脸,镶嵌着一双细小、狡黠而深陷的眼睛,只有嘴唇像别的生物,红润光滑,嘴角露出一排乡下人的格外坚固的大牙齿。如果是城里的女人,这般年龄即使浓妆艳抹也不足为奇。母亲的脸似乎尽可能装得丑陋些,我敏感地看出并且憎恨她在什么地方像沉淀似地残存着一种肉感。
从老师眼前退了下来,母亲尽情地痛哭了一场,然后用配给的人造纤维手巾揩了指敞开衣襟露出来的黑乎乎的胸脯。那手巾的质地像动物般地闪亮,被水濡湿,显得更光亮了。
母亲从背囊里将大米掏出来,说:这是送给老师的。我默不作声。母亲取出了用旧灰色丝棉包了好几层的父亲的灵牌,放在我的书架上。
“太感谢了,明儿老师会给念经的,你父亲也会高兴的啊。”
“办完忌辰,您就回成生去吧。”
母亲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她说那寺庙的权利早已转让给别人,仅有的田地也处理了,还清父亲所欠的全部医疗费用,今后她孤身一人,打算投靠京都近郊加佐郡的伯父家,她就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
我没有可回的寺庙了!那荒凉的海角村庄也没有人迎接我了。
这时,我脸上浮现出一种解放感,不知母亲是怎样理解的。她将嘴凑到我的耳边说:
“唉,你没有别的寺庙了。你除了当这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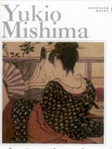
![[花样]凯丽压了道明寺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18/1870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