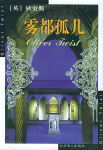雾都孤儿-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邦布尔太大先是迟疑了一下,接着不待对方进一步邀请,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邦布尔先生不好意思或者说是不敢掉在后边,紧跟着进去了,活脱脱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他的主要特征本来是那种引人注目的威风,此时却简直难以找到一星半点。
“真是活见鬼,你怎么淋着雨在那儿逛荡?”孟可司在他们身后闩上门,回过头来,跟邦布尔搭话道。
“我们——我们只是在凉快凉快。”邦布尔结结巴巴地说,一边提心吊胆地四下里乱看。
“凉快凉快?”孟可司把他的话顶了回去。“没听说什么时候落下来的雨,或者将来下的雨,能浇灭人心头的欲望之火,正如浇不灭地狱之火一样。凉快凉快,没那么舒服,想都别想。”
说罢这一番至理名言,孟可司骤然转向女总管,目光逼视着她,连从不轻易屈服的她也只得把眼光缩回去,转向地面。
“就是这位女士了,对吗?”孟可司问道。
“嗯嗯。是这位女士。”邦布尔牢记着太太的告诫,口答说。
“我猜想,你认为女人是绝对保守不住秘密的,是吗?”女总管插了进来,一边说,一边也用锐利的目光回敬孟可司。
“我知道她们只有一件事能保住秘密,直到被人发现为止。”孟可司说。
“那又是什么秘密呢?”女总管问。
“秘密就是她们失去了自个儿的好名声,”孟可司答道,“所以,根据同一条法则,假如一个女人介入了一个会把她送上绞刑架或是流放的秘密,我用不着担心她会告诉任何人,我不怕。你明白吗,夫人?”
“不明白。”女总管说话时脸有点发红。
“你当然不明白。”孟可司说,“你怎么会明白?”
那人投向两个同伴的表情一半像是微笑,一半像是在皱眉头,又一次招手要他们跟上,便匆匆走过这间相当宽敞但屋顶低矮的房间。他正准备登上笔直的楼梯或者梯子什么的,到上边一层库房里去,一道雪亮的闪电从上边的窟窿里钻进来,接着就是一阵隆隆的雷声,这座本来就东倒西歪的大楼整个晃动起来。
“听啊!”他往后一退,嚷了起来。“听啊!轰隆一声就下来了,好像是在大小魔头躲藏的无数个洞窟里齐声响起来的一样。我讨厌这声音。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突然将捂在脸上的双手拿开,邦布尔先生看见他的脸大变样,脸色也变了,自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烦躁。
“我三天两头都要这么抽筋,”孟可司注意到了邦布尔先生惊恐的样子,便说道。“有的时候打雷也会引起。现在不用管我,这一次算是过去了。”
他这么说着,带头登上梯子,来到一个房间。他手忙脚乱地把房间的窗板关上,又把挂在天花板下一根横梁上的滑轮升降灯拉下来,昏暗的灯光落在下边放着的一张旧桌子和三把椅子上。
“眼下,”三个人全都坐下来,孟可司说话了,“我们还是谈正事吧,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位女士是不是知道谈什么?”
问题是冲着邦布尔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夫人却抢先作了回答,说自己完全清楚要谈什么事。
“他可是说了,那个丑八怪死的当晚,你跟她在一块儿,她告诉了你一件事——”
“这事和你提到的那个孩子的母亲有关,”女总管打断了他的话,答道,“是有这么回事。”
“头一个问题是,她谈的事属于什么性质?”孟可司说道。
“这是第二个问题,”女士慎重其事地之说,“头一个问题是,这消息值多少钱?”
“还不清楚是哪一类消息呢,谁他妈说得上来?”孟可司问道。
“我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清楚的了。”邦布尔太太并不缺少魄力,对于这一点她的夫君完全可以证明。
“哼。”孟可司带着一副急于问个究竟的神色,意味深长地说,“该不会很值钱吧,嗯?”
“可能是吧。”回答十分从容。
“有一样从她那儿拿走的东西,”孟可司说道,“她本来戴在身上,后来——”
“你最好出个价,”邦布尔太太没让他说下去,“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我相信你正是想要知道底细的人。”
邦布尔先生至今没有获得他当家人的恩准,对这个秘密了解得比当初多一些,此时他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听着这番对话,满脸掩饰不住的惊愕表情,时而看看老婆,时而又看看孟可司。当孟可司厉声问道,对这个有待透露的秘密得出个多大的数目时,他的惊愕更是有增无已,如果先前还不算达到了顶点的话。
“你看值多少钱?”女士问的时候跟先前一样平静。
“也许一个子不值,也许值二十镑,”孟可司回答,“说出来,让我心里有个数。”
“就依你说的这个数目,再加五镑,给我二十五个金镑,”那女的说道,“我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先说出来可没门。”
“二十五镑!”孟可司大叫一声,仰靠在椅子上。
“我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邦布尔太太回答,“也算不得一个大数。”
“一个微不足道,也许讲出来什么也算不上的秘密,还不算大数?”孟可司猴急地嚷了起来,“加上埋在地下已经十二年还有多的。”
“这类玩意儿保存好了,跟好酒一样,越陈越值钱。”女总管回答说,依旧保持着那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到埋在地下嘛,不是还有些个埋在地下一万二千年,或者一千二百万年的,你我都知道,终归还是要说出些个稀奇古怪的事来。”
“我要是付了钱,却什么也没得到呢?”孟可司犹豫起来,问道。
“你可以轻而易举重新拿回去,”女总管回答,“我不过是个女人,孤身一人呆在这里,没有人保护。”
“不是孤身一人,亲爱的,也不是没人保护,”邦布尔先生用吓得发抖的声音央告说,“有我在这儿呢,亲爱的。再说了,”邦布尔先生说话时牙齿咔哒直响,“孟可司先生实实在在是位绅士,不会对教区人士动武的。孟可司先生知道,我不是年轻人了,也可以说,我已经有一点老不中用了。可他也听说过——我是说,我丝毫也不怀疑孟可司先生已经听说了,我亲爱的——要是惹火了,我可是一个办事果断的人,力气非同一般。只要惹我一下就够了,就是这么回事。”
说着,邦布尔先生装出一副果断得吓人,实则可怜巴巴的样子,紧紧握住他带来的那盏手提灯,可眉梢嘴角那一处处吓慌了的神情清清楚楚地表明,他的确需要惹一下子,而且还不只是惹一下子就够了,才做得出勇猛过人的姿态来。当然,对付贫民或其他专供恐吓的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这个蠢货,”邦布尔太太答道,“还是把嘴闭上为妙。”
“要是他不能用小一点的嗓门说话,那他来以前最好把舌头割掉,”孟可司恶狠狠地说,“别忙。他是你丈夫,嗯?”
“他,我丈夫!”女总管吃吃地笑起来,避而不答。
“你一进来,我就那样想过,”孟可司说道。他已经注意到了,她说话时怒不可遏地朝老公瞪了一眼。“那就更好了。要是发现跟我打交道的两个人其实是一个,我可就干脆多了。我不是说着玩的。瞧吧。”
他把一只手插进侧边衣袋里,掏出一个帆布袋子,点着数把二十五金镑放在桌子上,然后推到那位女士面前。
“喏,”他说道,“把东西收起来。这该死的雷声,我觉得它会把房顶炸塌的,等它过去,我们就来听听你的故事。”
雷声,好像的确近得多了,几乎就在他们头顶上震动、炸响,随后渐渐远去。孟可司从桌边扬起脸,朝前弓着身子,一心想听听那个妇人会说出些什么。两个男人急于听个究竟,一起朝那张小小的桌子俯下来,那女的也把头伸过去,好让她像耳语一般的说话声能听得见,三张脸险些儿碰着了。吊灯微弱的亮光直接落在他们的脸上,使这三张面孔显得越发苍白而又焦急,在一片朦胧昏暗之中,看上去像是三个幽灵。
“那个女人,我们管她叫老沙丽,她死的时候,”女总管开始了,“在场的只有我跟她两个人。”
“旁边没别的人了?”孟可司同样悄没声地问,“别的床上没有害病的家伙,或者说白痴吧?谁也听不见,绝没有人听了去?”
“一个人都没有,”女的回答,“就我们俩。死的功夫,就我一个人守在尸体旁边。”
“好,”孟可司专注地望着她,说道,“讲下去。”
“她谈到有个年轻的人儿,”女总管接着说,“好些年以前生下一个男孩,不单单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而且就在她临死的时候躺的那张床上。”
“啊?”孟可司的嘴唇哆嗦起来,他回头看了一眼,说道,“吓死人了。怎么搞的。”
“那孩子就是你昨天晚上向他提到名字的那一个,”女总管漫不经心地朝自己的丈夫点了点头,“那个看护偷了他母亲的东西。”
“在生前?”孟可司问。
“死的时候,”那女的回答的时候好像打了个寒战,“孩子的母亲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求她替孤儿保存起来,可那个当妈的刚一断气,她就从尸体上把东西偷走了。”
“她把东西卖掉了?”孟可司急不可待地嚷了起来,“她是不是卖了?卖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卖给谁了?多久以前的事?”
“当时,她费了好大劲告诉我,她干了这件事,”女总管说,“倒下去就死了。”
“再没说什么了?”孟可司尽量压低声音嚷道,但却仅仅使他的声音听上去更加暴躁。“撒谎。我不会上当的。她还有话。不把话说清楚,我会要你们俩的老命。”
“别的话她一句也没说,”这个怪人的举动十分狂暴,但妇人显然丝毫也不为所动(相形之下,邦布尔先生就差远了),她说道。“不过,她一只手死死抓住我的上衣,手没有整个攥在一块儿。我见她已经死了,就用力把那只手掰开,发现她手里握着一张破纸片。”
“那上边有——”孟可司伸长脖子,插了一句。
“没什么,”那女的回答,“是一张当票。”
“当的什么?”孟可司追问道。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妇人说道,“我寻思她把那个小东西放了一阵子,满以为能卖个大价钱,后来才送进了当铺,她存了钱,或者说攒了些钱,一年一年付给当铺利息,免得过期。真有什么事情用得着了,还可以赎出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我告诉你吧,她手里捏着那张烂得一塌糊涂的纸片死了。那时还有两天就要过期了,我心想说不定哪天还会用得着呢,就把东西赎了回来。”
“眼下东西在什么地方?”孟可司急切地问。
“在这儿。”妇人回答。她慌里慌张,把一只大小刚够放下一块法国表的小羊皮袋扔在桌上,好像巴不得摆脱它的样子。孟可司猛扑上去,双手颤抖着把袋子撕开。袋子里装着一只小金盒,里边有两绺头发,一个纯金的结婚戒指。
“戒指背面刻着‘艾格尼丝’几个字,”妇人说,“空白是留给姓氏的,接下来是日期。那个日子就在小孩生下来的前一年。我后来才弄清楚了。”
“就这些?”孟可司说,他对小袋子里的东西都仔细而急切地检查过了。
“就这些。”妇人回答。
邦布尔先生长长地倒抽了一口气,仿佛感到欣慰,故事已经讲完了,对方没有重提把那二十五金榜要回去的话,他鼓起勇气,把从刚才那一番对话开始以来就遏止不住地从鼻子上滴下来的汗水抹掉了。
“除了能够猜到的以外,我对这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邦布尔老婆沉默片刻,对孟可司说道,“我也不想打听什么,因为这样最稳当。不过,我总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吧,是吗?”
“你可以问,”孟可司略有几分惊异地说,“但我是否答复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就成了三个了。”邦布尔先生一心要在滑稽取笑方面露一手,便说道。
“这是不是你打算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女总管问道。
“是,”孟可司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呢?”
“你打算用来干什么?会不会用来跟我过不去?”
“绝对不会,”孟可司回答,“也不会跟我自己过不去。瞧这儿。你一步也别往前挪,要不你的性命连一根莎草也不值了。”
随着这番话,他猛地将桌子推到一边,抓住地板上的一只铁环,拉开一大块活板,从紧挨着邦布尔先生脚边的地方掀开一道暗门,吓得这位先生连连后退。
“瞧下边,”孟可司一边说,一边把吊灯伸进洞里,“犯不着怕我。你们坐在上边的功夫,我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打发你们下去,我要是有这个意思的话。”
在这一番鼓励之下,女总管挨近了坑口。连邦布尔先生也在好奇心驱使下大着胆子走上前来。大雨后暴涨的河水在底下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