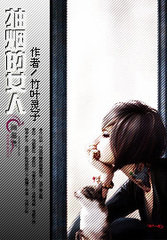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雪的摇篮,崭新、冰冷。黑色的岩石、银白的山峦直绵延向淡蓝的天际。
当他们走出火车站,踏上光露的站台时,只有雪花在四周和头顶上飘飘洒洒。古迪兰颤抖着,似乎心都是凉的。
“上帝,”她突然亲昵地转向杰拉德,“这下你可做到了。”
“什么?”
她微微做了个手势,指指周围雪的世界。
“你瞧啊!”
她仿佛都不敢再继续走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走在山腹地区,从两边的山上,雪纷纷落下,使人在这实实在在的天堂的山谷里显得那么微弱渺小,雪山峡谷,闪耀着奇特的光芒,肃穆、沉静。
“这使人感到渺小和孤独!”欧秀拉转过身去,手抓着伯基的胳膊说道。
“来到这儿你不后悔吧?”杰拉德对古迪兰说。
她看来有些疑惑。他们走出了两边被雪包围的车站。
“啊,”杰拉德兴奋地嗅着空气说道,“太棒了!那是我们的雪橇,我们再走一会儿,然后就赶到大路去。”
古迪兰一贯迟疑不决,这回她却学着杰拉德的样子把沉重的大衣甩到雪橇上,就出发了。她仰起头,开始在雪路上滑了起来,并把她的帽子拉到耳朵上,遮住了它,她的明快的蓝色的外套在风中飘起来,她那看来厚厚的紫色的长筒袜在洁白的雪地里那样耀眼。杰拉德望着她,她仿佛在奔向她的命运,而把他远远地落在后面。他先让她跑出一段路程,然后甩开大步追上去。
到处都是深深的雪,四下里一片沉寂。粗大的冰柱从泰罗利农舍的房檐上垂挂下来。农舍已被雪埋到窗台了。农妇们穿着长裙,裹着披肩,穿着厚厚的靴子走过来,停住脚步。他们看着那个以惊人速度滑行的柔弱却又意志坚强的女孩,她身后那个男人尽管想追上她,却有些力不从心。
他们穿过那百叶窗板和阳台涂过油漆的小饭馆和几间半埋在雪中的农舍,还有桥边那家完全被雪封住的沉寂的锯木厂。那有顶篷的桥横跨隐蔽的小溪。从那冰冻的小溪上,他们滑入了一大片远未被踏过的雪地,周围一片静悄悄的。一望无垠的洁白世界使他们欣喜若狂。但这寂静让人的心灵孤独,冷冻了人的心,太可怕了。
“绝妙的地方,这一切!”古迪兰目光奇特、意味深长地盯着杰拉德的眼睛。他的心颤了一下。
“的确不错。”他说。
仿佛一股可怕强烈的电流穿过他全身,肌肉充了电一般,双手充满了力量。他们沿着雪路快速滑行着。路两边不时可以看到萎缩的树枝垂下来。他和她象是一股强电流的两极分开走着。可他们感到有足够的力量跨越生活的障碍,跳到禁区中再跳回来。
伯基和欧秀拉也在雪地里滑行着。他们已经超过了一些滑雪橇的人。欧秀拉兴高采烈,但她时不时地就会转过身来拉住伯基,以确认他的存在。
“我从来没想到是这样一幅景象,”她说,“这可是另一个世界。”
说话间他们踏上了白雪覆盖的草坪。这时他们被一阵雪橇的铃声吸引住了,那声音打破了四周的平静。他们又走了大约一里路,才在那个粉红色的半没雪中的神庙旁极陡的上坡路上追上了古迪兰和杰拉德。
然后,他们又一道滑入一条溪谷中,这里有黑色的石壁,大雪覆盖的河流,头上是蔚蓝的天空。他们穿过一座落满雪的桥,几个人兴奋地在桥头上乱打乱敲。随后,他们再次穿越雪地,开始继续慢慢向上滑。拉雪橇的马走得很快,车夫在一旁甩动着“嘎嘎”作响的马鞭,嘴里发出奇特的“嚯嚯”声。直到他们再次进入雪谷中,才算看不到石壁了。他们一点点向上走着,这儿的下午很冷,阳光投下一片片阴影。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块白雪覆盖着的高地上。这儿耸立着最高的几座雪峰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的点点花心般伫立着。在那边空无人迹的天堂似的山谷里有一座褐色木墙,白色厚房顶的农舍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凄凉地深陷于雪地中,简直像个梦。它象一块从陡坡上滚下的岩石,只不过外形象房子而已,现在埋在雪中。人可以住在那里,而不被四周可怕苍白寂静凛冽的寒风压垮的话,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这几个新来者跟着一个女佣走上光秃秃的木楼梯。古迪兰和杰拉德要了第一间卧室。进来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间很小的木制房屋,没什么摆没,房间里闪着金色的木质光芒:地板、四壁、房顶、门都是漆油过的松木,金光闪闪,一派暖色调。有一扇窗户正对着入口处,但是很低,因为屋顶是向下倾斜式的,在倾斜的天花板下有一张桌子,上面有洗手盆和水灌。对面还有一张放有镜子的桌子,门两边各有一张床,床上摞着厚厚的绘有绿方格图案的垫枕,这种垫枕非常大。
这就是全部。没有壁橱,没有一点生活奢侈品。在这里他们俩就像被封闭在一个黄色木质的细胞中,只有两张镶蓝边的床。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便大笑起来,为这种与世隔离感的逼近而感到恐惧。
一个男人敲开门送来了行李。这家伙很壮,颧骨宽大,脸色苍白,留着粗粗的黄胡子。古迪兰看着他默默地放下行李包,然后步伐沉重地离去。
卧室里并不是很暖和。古迪兰有点颤抖。
“很好。”她接口道,“瞧这墙板的颜色,很美,我们就像住在一个坚果壳里。”
他站在那里望着她,手摸着他那剪得短短的胡须,身体稍稍向后靠着,敏锐的目光凝视着她,他此时完全被激情驱使着,这激情象一种厄运。
她走过去在窗边蹲了下来,好奇地望着外面。
“噢,可这里——!”她几乎是痛苦、不情愿地叫了起来。
窗外,是一座封闭的山谷,上方是苍穹,巨大的黑岩石山坡上覆盖着白雪。在那尽头,一堵白墙仿佛是大山的肚脐,两座山峰在夕阳的余辉中闪亮。笔直的前方,雪的摇篮,静静地荡漾在两边巨大的峭壁间,在那峭壁的底部有一簇簇的松树,像头发一样。这雪的摇篮一直延伸到那遥远的与世隔绝的世界尽头,在那里有雪山挡住了去路。山峰挺立,高耸入云,这里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的纽结点和肚脐,是天地相接之处,不可接近、无法通过。
这幅图景令古迪兰心驰神往。她静静地蹲在窗前,双手捧着脸颊,恍恍惚惚。她终于到达了,到达了她的世界。她在这儿结束了她的冒险,象一块水晶石没入了白雪中。
杰拉德弯下腰拥着她,从她的肩上向外看去。他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孤独。她远去了,彻底离他而去了。于是他感到心头笼罩着冰冷的霜雾。他看着那闭锁的山谷,那莽莽的积雪和苍穹下的山峰,没有任何出路。可怕的宁静。冰冷、炫目的白色的世界紧裹着他,可她仍旧
蹲在窗前,象圣殿中的幽灵。
“喜欢吗?”他的声音遥远而陌生。她至少还能意识到他的存在。但她只是把她柔和、冷漠的脸扭开一点,避开他的目光。他知道她眼中有泪水,为她的宗教而流泪。她自己的泪水就是那宗教,使他的存在不再重要。
突然,他的手托起她的脸,让她看着他。她睁大了蓝色的眼睛,泪水盈盈地看着他,似乎她受到了惊吓。透过泪帘,她惊恐地看着他。他淡蓝色的眼睛射出锐利的目光,他的瞳孔不大,神情异常。她的双唇微启,困难地喘息着。
一阵激情涌上来,一下子就像铜钟那样强烈、响亮,不可阻挡地敲着。当他俯视着她柔美的脸颊时,他的双腿夹紧了,如铜钟般镇定。她的双唇开启着,双目圆睁着,似乎受到了侵犯。她的下巴在他手中变得极为柔和、光滑。他感到自己象严冬一样强壮,他的手像是有生命的金属,不可战胜,不折不挠。他的心脏如像他体内的悬钟般猛敲着。
他把她拉到怀里。她的身体柔软、没有生气、丝毫没有反抗,但突然,她那泪水尚未干的双眼困惑、无助地睁开。他异常强壮,似乎体内注入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拉起她,紧紧搂住她。她的身子柔软无力,瘫在他身上,这情欲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他铜一样的肢体上,如果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就会被压垮。她强烈地挣扎着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心中一股火窜上来,他又一下子钢铁般坚定地把她搂了过来。他宁愿摧毁她,也不愿被拒绝。
但是,他那强壮的力量是她无法抗拒的。她再次挣脱出来,软软放松地躺在一边,有点兴奋地喘着气。对他来说,她是如此甜美,使他纵情享受无上的幸福。他宁可一辈子受折磨,也不愿放弃一秒钟这样无比美妙的享受。
“上帝,”他对她说。他的脸因为拉长而显得很奇怪,有些扭曲,“接下来是什么呢?”
她安安静静地躺着,睁着一双宁静的顽童似的黑亮的大眼睛望着他。她此刻茫然得很。
“我会永远爱你。”他望着她说。
但她没有听见。她躺着看他,就象看一个她永远也不懂的什么东西:就象一个孩子看一个大人,不希望理解,只是屈从。
他吻着她,吻着她的眼睑,为的是不让她再看他。他现在渴求什么,希望她承认他、对他有所表示、接受他。但她只是安详地躺着,孩童般的,很遥远,仿佛一个被征服却无法理解的孩童,只感到迷失。他又吻了她,算放过她了。
“我们下楼喝点咖啡、吃点点心好吗?”他问。
窗外,落日的余晖已变成灰蓝色。她闭上眼睛,关上了单调幻境的闸门,又睁开眼睛来看日常的世界。
“好的。”她打起精神,简单地回答。然后,再次走向窗户。蓝色的夜晚已经降临在窗外雪的摇篮和那巨大的斜坡。但是那耸入天际的峰巅却是玫瑰色的,像花蕊似的闪烁、炫目,盛开在天堂的顶端,超乎一切,那么可爱又那么遥远。
古迪兰看着所有这些可爱之处。她知道,蓝色的天光下这一朵朵玫瑰样的雪中花朵是永恒的,永远这么美。在夕阳蓝色的斜晖中,玫瑰色的花蕊,积雪发出的火花,她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可她不属于这美景。她与这无关,她的心被排除在这美景之外。
她伤感地又望了一眼窗外,才转过身来,梳理头发。他已经打开行李等着她,看着她。她知道他在看她,这弄得她手忙脚乱的,很不那么从容。
他们一起走下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怪的表情。他们看见伯基和欧秀拉正坐在角落里的一张长桌前等他们。
“他们在一起看起来是多么简单而又协调。”古迪兰心里不禁生气一丝妒意。她羡慕他
们那自然的举止,像孩子一样满足,但是她就达不到这一点。在她看来,他们就像小孩子。
“嘿,多好的点心。”欧秀拉贪婪地叫道,“太棒了!”
“是啊。”古迪兰说,“我们要点咖啡和点心吧!”她对侍者说了一句。
然后她坐在了杰拉德的身边。
“我认为这地方真的不错,杰拉德。”伯基说,“棒极了、美妙、不可思议,所有形容词都用得上。”
杰拉德也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我喜欢这儿。”
厅里三面都摆着桌子。伯基和欧秀拉背靠着墙面,杰拉德和古迪兰则挨着他们坐在角落里靠着火炉。餐厅还算不小,有一个小酒柜,就象
在乡间酒馆中一样。不过,这儿设施很简陋,房间显得空旷。仅有的家具就是桌子和椅子,环绕着餐厅的三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绿色的炉子,酒柜和门在另一面墙上,窗户是双层的,没有任何窗帘。现在已是傍晚了。
咖啡来了——热气腾腾——还有一块蛋糕。
“一整块点心!”欧秀拉叫道,“他们给你的比我的多,我得瓜分一点儿你的。”
周围还有其他人,大约共有十个。伯基很快便知道了,其中有两个艺术家,三个学生,一对夫妇,还有一个教授带着两个女儿——都是德国人。而他们四个英国人是新来的,坐得
高高的,可以俯视一切。那些德国人站在门口向里探头望了望,对那侍者说了几句话,便又离开了。现在不是吃饭时间,所以他们没到厅里来,而是换了靴子参加联谊会去了。
四个英国人可以听到不时传来的齐特拉琴的演奏声,钢琴的弹奏声,还伴随着阵阵的笑声,吵闹和歌声。四周有些轻微的声音的震动。由于整个房子是木制的,因此,它像是一个容纳了各种声音在里面的大鼓。不过声音扩散以后倒没有增大,而是减小了。所以齐特拉琴声听起来很弱,像是在远方微弱地响着。钢琴声也不大,没准儿是一架极小的古钢琴吧。
当他们喝完咖啡时,老板走进来。他是个泰罗人,膀大腰圆,面部扁平,苍白的脸上长满了麻子,胡须很重。
“愿意到联谊会去结识别的女士和先生吗?”他弯下腰来,笑容可掬地问道,露出一口大白牙。他那蓝色的眼睛把这几个人扫视了一圈——他不太有把握怎么和这几个英国人打招呼。由于不会说英语,他感到不太自在。
“我们要不要去联谊会,跟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