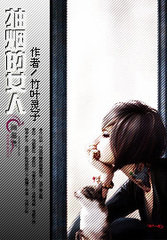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当她和伯基的女房东在门口打招呼的时候,她掩饰了自己的悲哀,声音里又透出平时的欢乐、。
“晚上好!伯基先生在家吗?我可以见他吗?”
“是的,他在书房里。”
欧秀拉很快从女房东身边擦身而过。他的门已经开了,他听到了她的声音。
“你好!”他有些惊奇地打着招呼,他看到了她手中提着旅行袋,脸上还有泪痕。她象个孩子,脸都没擦干净。
“我是不是显得很丢人?”她退缩着说。
“不。到底怎么了?快进来。”他接过皮箱,两人走进了书房。
一到屋里,她就象一个想起伤心事的孩子一样,嘴唇开始哆嗦起来,泪水也一下子又涌上来了。
“出什么事了?” 他搂住她问。她伏在他肩上啜泣得很厉害。
“到底怎么了?”等她稍微平静一点后,他又问,但她并不说话,只是很痛苦地把头伏在他的肩上。
“怎么了?”他又问了一遍。
她突然挣开他,把眼泪擦干,走过去坐在了椅子上。
“爸爸打我了。”她泪眼中闪着光,弯腰坐着,好像一只把羽毛竖了起来的小鸟。
“为什么?”他说。
她看着别处,不说话。她那细小的鼻尖儿和颤抖着的嘴唇有些微红,样子很让人心疼。
“为什么?”他声音和蔼,柔和得让人心动。
她扭过头看着他。
“因为我说我明天就结婚,他就欺负我。”
“他为什么这样?”
她的嘴巴又抽动了一下。想起刚才的情景,眼泪又涌了出来。
“因为我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我——这把他给刺痛了,他是个霸道的人——”她边说边哭,哭得嘴都歪了,一副孩子的样子。这差点儿把他给逗笑了。可这并不是孩子气,这是个致命的冲突,一个很深的伤口。
“这也不完全正确。”他说,“即使这样,你也不应该那样讲。”
“这是真的——是真的。”她抽泣着,“他只不过是假装爱我,想要控制我——这不叫爱——他根本不关心我,他怎么能——”
他沉默着。
“如果你没惹他生气,他是不可能这样对你的。”伯基平静地说。
“可是我曾爱过他,爱过他。”她哭着,“我一直都爱着他,可他却这样对我,他——”
“那是不相同的爱。”他说,“别在意——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大不了。”
“不!”她哭着说,“这非常严重。”
“为什么?”
“我以后再也不见他了——”
“这只是暂时的——不要哭,你迟早都会离开他的——别哭了。”
他走过去,吻她娇好、细细的头发,轻轻地抚摸着那满含泪水的脸。
“不要哭了。”他重复说,“别再哭了。”
他把她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默默地一言不发。
最后她平静下来了,然后抬起头,睁大恐惧的眼睛问:“你不需要我了吗?”。
“需要你?”他的眼神暗淡,让她迷惑。
“你不希望我来你这儿?”她焦急地问道。
“不,”他说,“我只是不希望发生这一场冲突——这太糟糕了。”
她默默地看着他。
“那我现在住在哪儿?”她觉得有些丢人。
他想了一下,说:
“和我住在一起。今天结婚和明天结婚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
“我会告诉瓦莉夫人的。”他说,“别担心。”
他坐在那儿,看着她。她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在凝视她。这让她有点不安。她下意识地摆弄了一下额头上的刘海。
“我看起来很难看吧?”她说。
接着她又擤了一下鼻子。
他微笑道:
“不丑”,他说,“感谢上帝。”
接着他走过去抱住她。她显得那么柔弱,让他都不忍心再去看她,只是紧紧地把她藏在怀里。现在,她已被泪水清洗得洁白、新鲜、娇嫩,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花朵,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她那么新鲜,那么洁净,没有一丝阴影。而他则是那么古老、沉浸在沉重的记忆中。她的灵魂是清新的,与未知世界一起闪烁光芒。而他的灵魂则是晦黯的,只有一丝生命的希望,好像一粒种子。但是这仅有的一粒生命的种子却正点燃了她的青春。
“我爱你。”他边吻她边低语道,他因着希望而颤抖,就象一个复活的人获得了超越死亡的希望。
她不知道这句话对他而言包含着多深的情意,不知道他这几个字到底有多大分量。在她看来,一切都还是那么不确定。
但是她绝对不能够理解,他崇拜她,就像老年人崇拜年青人,他以她为骄傲,因为他心中那颗希望的种子,让他的青春和她一样拥有活力。作为她的伴侣,他丝毫不悔,和她结合意味着他生命的复活。
所有这些她都不明白。她只想得到关心、宠爱。他们中间隔着无限的沉寂距离。他怎么能告诉她,她内在的美不是形体、重量和色彩,而是一种奇怪的金光!他怎么才能讲得清楚她的美是来自什么?
第二天,他们正式结婚了。依从他的要求,她给父母写了信。她的母亲回了信,而父亲没有。
她没有回学校了。她和伯基住在他的房子里,有时住在磨坊。他俩形影相随。除了古迪兰和杰拉德以外,她谁都不见。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有些陌生和迷惑,但心情渐渐好多了。
一天下午,在磨坊那间暖和的书房里,杰拉德和她聊着天。鲁帕特还没回来。
“你感觉很幸福吧?”杰拉德笑着问她。
“很幸福!”她大声说。
“是啊,看得出来。”
“是吗?”欧秀拉吃惊地问。
他看着她,露出十分坦诚的笑。
“是的,很明显。”
她很高兴。她想了一下问道:
“你可以看出鲁帕特也很幸福吗?”
他垂下眼皮,朝一边看去。
“是的。”他说。
“真的吗?”
“是的。”
他突然安静下来,好像他不愿意提及伯基,他看起来有些难过。
她十分敏感。
“那么你呢?”她说,“你也应该一样幸福。”
他不说话了。
“和古迪兰在一起?”他间。
“是的!”她大声说。
“你认为古迪兰将会嫁给我,而且我们会很幸福?”他问。
“是的,我敢肯定。”她说。
她的眼中闪着喜悦,但她心里其实很紧张,因为她知道她只是在坚持自己的说法。
“噢,我特别高兴。”她又加了一句。
他微笑着。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他说。
“为了她。”她回答说,“我敢肯定,你是最适合她的男人。”
“是吗?”他说,“你认为她也会这么想吗?”
“噢,当然。”她马上说。但她考虑了一下后,又不安地说,“当然古迪兰并不是那么单纯,是吗?她并不那么容易让人懂,对吗?在这一点上她跟我可不一样。”她向他笑笑,神情有些特别。
“她不像你?”杰拉德问道。
她皱起了眉头。
“噢,很多方面相像——但是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新生事物。”
“是吗?”杰拉德说。他好半天没有说话。随后他动动身子说:“我打算叫她在圣诞节的时候和我一起出去玩。”他说得很谨慎。
“和你一起出去?多长时间?”
“她想多久就多久。”他说。
两人都又沉默了。
“当然,她也许还会匆匆地结婚呢。”
“是的。”杰拉德笑了笑说,“我明白,可就怕她不乐意。你觉得她会跟我出国几天或两周
吗?”
“会的,我去问问她。”欧秀拉说。
“你觉得咱们都去怎么样?”
“我们大家?”欧秀拉的脸又露出了笑容,“那将会很有意思,是吗?”
“是的。”他说。
“然后,你就可以清楚了。”欧秀拉说。
“清楚什么?”
“清楚事情的进展,我想最好在婚礼前度蜜月,你说呢?”
她对自己的妙语感到满意。他笑了。
“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他说,“我希望我就这样做。”
“你能这样!”欧秀拉叫道,“你是对的,一个人应该学会自得其乐。”
过了一会儿,伯基回来了。欧秀拉告诉他刚才他们谈论的内容。
“古迪兰?”伯基说道,“她是个天生的情妇,就像杰拉德天生是个情夫一样——绝妙的情人。女人要么做妻子,要么做情妇。古迪兰便是情妇。”
“男人不是做情夫,就是做丈夫!”欧秀拉说道,“但是,为什么不能都做到呢?”
“它们是互相排斥的。”他笑着说。
“那我需要情夫。”欧秀拉大声说。
“不,你不需要。”他说。
“可我需要!”她大叫。
他吻了她,笑了。
过了两天,欧秀拉回贝尔多弗的家中取自己的东西。家已经搬走了,人都离开了。古迪兰现在也住在了威利·格林。
自从结婚以后,欧秀拉从来没见到过父母,因为这个,她哭了。但是和他们重新和好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不管怎样,她是不能去见他们的。
她的东西都还留在那里。她和古迪兰约好那一起去取东西。
一个冬日下午,她们回到家中时,夕阳已落山。窗户黑洞洞的,这地方有点吓人。一迈进黑乎乎空荡荡的前厅,两个姑娘就感到不寒而栗。
“我自己是绝对不敢来的。”欧秀拉说,“真够吓人的。”
“欧秀拉,”古迪兰大声说,“真是不可想象,我们以前住在这儿,却没有感到害怕。”
她们看了看空荡荡的饭厅。饭厅原本十分宽敞。而现在窗户光秃秃的,地板已脱了漆,浅浅的地板上涂有一圈黑漆线。褪色的墙纸上有一块块的暗迹,那儿是原先靠放家具和挂着画框的地方。那个墙壁让人有一种干瘪好象要坠落一样的感觉,地板也岌岌可危,颜色四周深,中间浅,好像是给涂上了一层色,没有给人一点亲切感。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索然无味。墙纸也干巴巴的,整个房子就如一个空盒子。
“不敢想象我们曾经住在这里!”欧秀拉说。
“是的,”古迪兰也喊出来,“太可怕了。”
“讨厌!”欧秀拉说,“这儿真让人讨厌。”
她们来到客厅。这里也是空空的,没有重量、没有实体,只有一种被纸张包围在虚无之中的感觉。厨房看上去还实在,因为里面铺着红砖地面,还有炉子,可一切都显得、冷清。
两姐妹沿着吱吱响的楼梯上了楼,每踩一级心里都会跳一下。随后她们又走上空荡荡的走廊。欧秀拉的卧室里靠墙的地方堆着她自己的东西:一只皮箱,一只针线筐,一些书本,衣物,一只帽箱。暮色中,这些东西在空屋子里显得孤孤零零的。
姐妹俩很快把东西搬到前门口。她们来回搬了好几趟。整座房屋似乎都回荡着空旷的、虚无的声音。那空旷的房屋在身后发生可憎的颤音,搬最后几样东西的时候,她们几乎是逃
出来的。
外面很冷。她们又回到屋里,等着伯基开车过来。她们上楼来到原来父母的卧室中。那卧室的窗子正冲着大路,顺着乡村田间看去,太阳正在西落,已经看不见了光芒,只剩下红的和黑的晚霞。
她们坐在窗台边等着伯基。她们环视着屋里,空旷的屋子,空得让人害怕。
“真的,”欧秀拉说,“这屋子真没法让人喜欢,是吗?”
古迪兰缓缓地用环视这屋子说:
“不能。”
“我常想起爸爸和妈妈的生活,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
“不愿意,欧秀拉。”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没意义——他们的生命,没一点意义。真的,如果他们没有相遇,没有结婚,没有一起生活——一切都无所谓,是吗?”
“当然,——这很难讲。”古迪兰说。
“是啊,但是,如果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会和他们一样,”她抓着古迪兰的胳膊说,“我会逃走的。”
古迪兰沉默了。
“其实,一个人很难思索普通的生活。”古迪兰回答,“对你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和伯基在一起就能脱离这一切。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一个人必须生活得自在,这是最重要的,必须自由自在,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可他必须自由。要结婚,就得找一个自由行动的人,一个战友,一个幸福的骑士。”
“啊,多可爱的名字——幸福的骑士。”欧秀拉说。
“难道不是吗?”古迪兰说,“我要和一个无忧无虑的冒险家一起漫游世界。一个安乐的家又算什么呢!”
“我明白,”欧秀拉说,“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个家——对我来讲,那就足够了。”
“完全够了。”古迪兰说。
他们的谈话被一阵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伯基来了。欧秀拉马上显得高兴起来。
她们听到楼下他皮鞋的咯吱声。
“你们好。”他打招呼说,屋子里回响着他的声音。
“你好,我们在这儿。”她冲着楼下叫道,随后她们听到他快步跑上来。
“这里简直可以隐居幽灵。”他说。
“这里没有幽灵——这儿从来没有名人,只有有名人的地方才会有幽灵。”古迪兰说。
“我想是的,你们正在为过去感伤吗?”
“是的。”古迪兰阴郁地说。
欧秀拉笑了。
“不是哀悼它的逝去,而是哀悼它的存在。”她说。
“噢。”他松了一口气。
他坐下了。欧秀拉感到在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