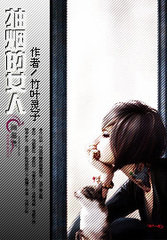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在这儿吧,”他说,“关上灯。”
他接着把灯关上了。四下里一片漆黑,树影婆娑,像是在晚上出没的鸟兽。他在草地上铺了条毯子。然后他们就默默地坐在上面。林中传来了微弱的声响,但并没有打扰他俩,也不可能打扰,整个世界受着某种奇怪的约束,一种很新奇的神秘笼罩着一切。他们俩很快地脱掉衣服,他把她楼了过来,摸着她,抚摸着她那从未暴露过的柔软的肉体。他压抑着欲望,手指触在她未曾展示过的裸体,沉寂压在沉寂上,神秘夜晚的肉体紧挨着神秘夜晚的肉体。这是男人和女人的黑夜,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心灵也无从知晓,只能透过触摸才能知道这是活生生的异体被展示着。
她渴望着,触摸着,在无言的触摸中,与他进行着巨大的感情交流。这活生生的肉欲真实永远也不能转换成意识,只停驻在意识之外,这是黑暗、沉寂和微妙之活生生的肉体,是神秘而实在的肉体。她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他的欲望也一样得到满足。他们在各自对方的眼中是一样的——都是远古的神秘、真实的异体。
他们在车篷底下度过了寒冷的一夜。醒来时天已大亮了。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大笑起来,然后他们互相别开眼光,心中藏着阴晦和秘密。然后他们相互吻着,回忆着昨天快乐的夜晚。多么美妙啊!这是黑暗真实的世界的馈赠。他们似乎害怕提及这深刻的感受,而将这种记忆和体验隐匿心中。
第二十四章 死亡与爱情
托马斯·克瑞奇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这个生命之缕如此之细却并没有断裂,这真令人无法想象。病人躺在那里,极度虚弱,精衰力竭,只靠吗啡和慢慢地啜一点点饮料来维持生命。他处于半昏迷状态,只剩下一丝意识把死亡的黑暗与生活的光明联系着。可是,他的意志却并没有破碎,只是他需要绝对的安静。
除了护士外,屋里的任何人对他而言都是一种负担。每天早晨杰拉德走进房间时,心里
总在想父亲该寿终正寝了,可迎接他的仍是那张熟悉的、毫无血色的脸,蜡黄的额头上仍旧覆盖着令人敬畏的黑发,还有那双令人畏惧、半开半闭的黑眼睛似乎只有一点点视力,里面是不成形的漆黑一团。
每当那双黑色无神的眼睛转向他时,杰拉德的内心深处就会涌上一股强烈的厌恶感。这种感觉似乎立刻燃遍全身,恶狠狠地威胁着他,令他发疯。
每天一早,金发碧眼的儿子站在那里,腰板挺直,浑身充满了活力。杰拉德这副样子实在令父亲气恼。他没有勇气正视杰拉德那双蓝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秘莫测的目光。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父子俩只是稍稍互相看上几眼,然后杰拉德就会离去。
很久以来,杰拉德一直保持着镇静,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但最终,恐惧终于打破了他的平静。他担心自己会支持不住,垮下来。可是他必须留下来等待结果。某种怪诞的意志迫使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慢慢走向死亡的边缘。然而现在,那种强烈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就好像有一把达摩克里斯的剑头①悬在他的脖颈之上。
①此处源出于希腊民间传说,意为“临头的危险”。
他无处可逃,他必须陪伴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这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他不知怎么地竟盼望这死亡的到来,甚至还促使它加快到来。
但是在这严峻考验的重压下,杰拉德也同样失去对外界日常生活的控制。那些曾经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工作、娱乐都被抛在脑后。他机械地处理着自己的生意,生活成了套在他身上的一个空壳,象大海一样咆哮着。可是在这空壳的内部却是黑洞洞的一片,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他十分清楚,一定要寻找东西来加固生活,将它填满,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这个巨大的黑暗空穴中去。他用意志支撑着他的外部生活和思想。从外表看他一点没变,可是内心的压力太大了,他必须找到什么东西来求维持良好的平衡。
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他本能地想到了古迪兰。现在他已经不顾一切,只想同她建立起关系来。他要跟着她去画室,接近她,和她说话。他要呆在房间里,盲目地拿起雕塑工具,粘土块和她塑的小人像——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她意识到他在追求她,像死神一样缠着她。她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她心里明白,他每向她发动一次进攻,就向前进了一步,更加亲近她了。
“我说,”一天晚上他不假思考、犹豫地对她说,“留下一起吃晚饭好吗?我希望你能答应。”
她有点吃惊。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一个男人在对另一个男人发出邀请。
“他们等着我回家呢。”她说。
“唉,他们不会介意的,对吧,”他说,“要是你能留下,我会十分高兴的。”
她沉默了好久,算是默许了。
“我去告诉托马斯好吗?”他问。
“吃完饭我就得回去。”她告诉他。
那是一个阴沉、寒冷的夜晚。他们坐在书房里。他默默寡语,显得心不在焉,而温妮弗雷德的话也不多。杰拉德会突然兴致上来,又说又笑,变得令人愉快,而且待她也很好。随后他又会变得茫然若失。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被他深深地迷住了。他看上去是那样全神贯注,他那种长久奇怪的沉默让她无法理解,心里不禁动了情,萌发出了要了解他的愿望。
他对她极尽殷勤,招待她吃最好的东西。他知道她爱喝一种甜酒,于是特意拿来了一瓶这种金黄色的带点甜味的美酒。盛情的款待使她感到受宠若惊。
这时,门上传来一声很轻微的叩击声。他站起来叫道:“请进。”身着白衣的护士走了进来,在门口徘徊着。她长得很美,却相当腼腆。
“克瑞奇先生,医生想和你谈谈。”她小声说道。
“医生!”他说着就朝外走,“在哪儿?”
“在餐厅。”
“告诉他我就来。”
说完他喝完杯中的咖啡,跟着护士走了出去。
“那个护士是谁?”古迪兰问道。
“英格利斯小姐。我最喜欢她了。”温妮弗雷德说。
过了一会儿,杰拉德回来了。他心事重重,像个微醉的人,有点神情紧张。他没提医生叫他去干什么,只是站在壁炉前,双手倒背,一脸茫然。
“我得去看妈妈了。”温妮弗雷德说,“趁爸爸还没睡着,再去看看他。”
她向他们俩道了晚安。
古迪兰也站起来告别。
“你不必这么着急着走,对吗?”杰拉德迅速瞥了一眼钟表,“还早呢。到时候我送你回去。坐下,别急着走嘛。”
古迪兰重新坐下。似乎他的意志能摆布她。她感到自己几乎被他迷住了。对她来说,他是一种奇怪而陌生的东西。当他出神地站在那里,一语不发。他心里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呢?她感觉出他是有意在留她,她感到是他让她动弹不得。
“医生有什么新情况要告诉你吗?”最后,她终于轻声地吐出了几个字。那温柔、羞怯的关心触及了他的心弦。他扬一扬眉毛,显出无关紧要的样子。
“没,没什么。”他回答,好像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他只说脉搏很弱,断断续续,但那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低头看着她,她目光温柔,清澈见底,令他心动不已。
“不。”她最后喃喃地说,“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还是不知道的好,”他说,“怎么,不想抽根烟吗?来一根吧!”他很快拿来了烟盒,又递上了打火机。然后,走到壁炉前站在她的面前。
“我们家人都没象父亲这样生过病,”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指的是这不可救药的疾病,这种缓慢的死亡。”
他的脚在壁炉前的大理石地板上不安地搓来搓去,嘴里叼着烟,眼睛朝上看着天花板。
“我知道,”古迪兰轻语道,“是很可怕。”
他呆呆地吸着烟,然后拿下烟,稍稍侧过身去,象一个孤独的人在思考着。
“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说完,他又朝她看了一眼。“我已经不像从前了。过去的全过去了,希望你能听懂我的话。就好像一个人抓住了空虚,可同时他本人也是空虚的。于是,就手足无措了。”
“那该怎么办呢?”她问道。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回答,“但一个人必须想法儿摆脱眼前的困境,否则你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自己,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而你却用手撑住了它。唉,这样显然无法再支撑下去。谁也不能永远用双手托举着屋顶,迟早有一天你非得松手不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必须想办法,否则整个宇宙就会崩溃下来。”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温顺地问道,“要是我能做些什么,你只管吩咐我好啦,只不过我也没什么用处。我不知道能帮你点什么。”
他打量了她一下。
“我并不想要你来帮忙,”他有些气恼地说,“因为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我需要的只是同情,你知道吗?我需要有人能和我说说心里话,那会使我好受些。可奇怪的是,没有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鲁帕特·伯基算一个,但他没有同情心,而且他只想让别人听他一个人唠叨。”
她仿佛陷进了一个奇怪的罗网里。她只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突然,传来了轻轻的推门声。杰拉德吃了一惊,感到十分懊恼。然后他向前走去,举止一下变得温文尔雅起来。
“哦,是妈妈。”他说,“您能下来太好了。身体怎么样?”
这位年迈的妇人裹着一件宽松肥大的紫色长袍,默默不语地走上前来,像往常一样,步履笨重。儿子站在她身旁,拿过一把椅子让她坐下,说:“您认识布朗文小姐吧?”
母亲漠然地看了看古迪兰。
“认识。”她说。然后把蓝眼睛转向儿子,慢慢地坐在椅子上。
“我过来问问你爸爸的情况。”她飞快地说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不知道你这儿有客人。”
“不知道?温妮弗雷德没有告诉您吗?布朗文小姐在这儿吃的晚饭,让我们这儿的气氛欢快了许多。”
克瑞奇太太缓缓转过身看着古迪兰,却仿佛视而不见。
“恐怕她并没有感到快乐吧。”说罢,她又转向儿子,“温妮弗雷德告诉我,医生要对你谈你父亲的情况。是什么事?”
“只是说脉搏太微弱,有好多次简直就摸不出来,他可能过不去今晚了。”杰拉德回答。
克瑞奇太太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似的。她坐在那儿,双手交叉着。这双手相当漂亮,充满了活力,只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这种活力都被她那沉默、笨重的身躯给吞没了。
她抬头望着站在身旁的长相英俊、行动敏捷的儿子。她的眼睛很蓝,很蓝,比勿忘我草还要蓝。她似乎对杰拉德很有信心,却又感到有些不放心。
“你怎么样?”她用轻得出奇的声音问道,好像只是说给他一个人听,“你不会很紧张吧?”
“不,妈妈。”他带着冷笑回答,“你很明白,总要有人陪到最后的。”
“是吗?是吗?”母亲急促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揽在自己身上呢?你能做些什么?事情总会有结局的,不用你操这份心。”
“是的,我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多大用处。”他回答,“可是,我们总感到有点于心不安。”
“你就是心太软,不是吗?这事你觉得不好对付吧?你生就要做大人物的,别在家里埋没了你的才能。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家呢?”
显然,这些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杰拉德颇感惊讶。
“妈妈,在这种关键时候,我认为一走了之是没什么好处的。”他冷冷地说。
“自己拿主意吧。”母亲说,“照顾好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你的负担太重了。一定要注意,否则你就会陷入困境。”
“我很好,妈妈。”他说,“不用为我担心,你放心好了。”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不要把你自己也赔进去——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我很了解你。”
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没有回答她的话。母亲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里,那双好看的白皙的手紧握着安乐椅的扶把。
“你不能这么做。”她的语调简直有点尖刻,“你没那个胆量,你弱小得像只猫,真的,一直这个样子。这位年轻的小姐今天住这儿吗?”
“不,”杰拉德回答,“她今晚要回家的。”
“那她可以坐单匹马车。家离这儿远吗?”
“就在贝尔多佛。”
“啊!”老妇人从未正眼瞧过古迪兰一眼,不过她此时似乎感到了她的存在。
“杰拉德,你总想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身上。”母亲说着,颇为费力地站了起来。
“要走吗,妈妈?”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我得回楼上去了。”她说着转向古迪兰,向她道了晚安,然后缓缓地向门口挪去,仿佛已经不会走路一样。走到门口时,她默默地把脸朝杰拉德凑过去,他吻了她。
“不要再送了。”她的声音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