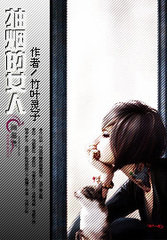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俩又都追随着人群,与这些丑陋的矿工们溶为一体。这一秘密似乎在所有的年轻人身上起作用。古迪兰、帕尔莫和所有的放荡的年轻人以及憔悴的中年人,他们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无法表达出来的消极情绪,一种致命的敷衍感,和一种意志的消沉感。
有时候,古迪兰真想跳到一边,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些,看看她自己如何沉沦的。这时她就会感到无比的气愤和羞耻,她觉得她陷入芸芸众生之中,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无法呼吸。这太可怕了,她感到窒息,她想逃离这里,疯狂地埋头干自己的工作。但是不久,她就又无所谓了。于是再次回到乡村——黑暗却富有魅力的乡村。于是,这种魅力又开始诱惑她了。
第十章 写生簿
一天早晨,姐妹俩来到威利沃特湖的偏远处写生。古迪兰一个人蹚水来到一处布满砾石的浅滩,像个佛教徒那样盘腿坐下来,凝视着那些从浅湖里的软泥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她看到的尽是软软的稀泥,软泥中长出的粗壮的水生植物来,主干挺拔饱满,向四周伸展出叶子,叶色墨绿,还夹杂着紫黑色和古铜色的斑点。借助想象,古迪兰能感觉到它们那饱满的肉质结构,她想象着这些叶子是如何拱出湿泥,如何在空中顽强而充满活力地挺立。
欧秀拉在另一边,看着一群蝴蝶在湖边飞舞。蓝色的小蝴蝶不知从哪里突然飞出来,一只黑红两色的大蝴蝶停在一朵花上,休息着它那柔软的翅膀,沉迷地呼吸着纯静阳光。两只白色蝴蝶也在低空中互相追逐,它们周身笼罩着一层光环。她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像那些蝴蝶一样无意识地跑开了。
古迪兰完全沉迷于那些亭亭玉立的水生植物。她蹲在浅滩上,很长时间不抬头地画着,时而又出神地盯着前方,彻底地被那些硬挺、光滑、饱满的茎叶所吸引。她光脚蹲在水中,帽子放在眼前的岸上。
桨拍水的声音,把她从沉醉中惊醒。她向四周望了望,她看见一只船上撑着一把十分鲜艳的日本伞,一个白色衣着的男人在划桨,那女士是赫曼尼,而那男子正是杰拉德。她突然意识到这一刻的刹那间,她几乎在一阵深切期待的颤抖中无法自拔,她的血管像过电般颤抖,比在贝多弗见到杰拉德时强烈多了,那时不过是一种低弱的电流罢了。
杰拉德是她的避难所,指使她躲开那些疲惫机械的低层矿工。尽管他也出自泥土,但他却是领导者。她看着他的背影,那运动着的白色的腰身,可又有些不像—当他弓身向前时像是围起的一块白色的东西。他像在俯身去做什么,他有点发白的头发在闪光,就象天上的电光一样。
“古迪兰在那儿呢。”赫曼尼的声音远远地从水面上飘来,“我们过去和她打个招呼吧,你不介意吧?”
杰拉德看见那姑娘站在湖边正在看他,他连想都没想就朝她那边划过去。在他的意识世界里,这姑娘还算不上什么,他只知道赫曼尼热衷于打破阶级界线,至少表面上看去是这样,而他也就悉听尊便。
“你好,古迪兰。”赫曼尼慢悠悠地唤着她的教名,“你在做什么呢?”
“你好,赫曼尼,我在写生。”
“是吗?”船摇近了,一头已经触了岸。“可以让我看看吗?我非常想看。”
古迪兰知道拒绝赫曼尼想做的事是没有用的。
“噢,”古迪兰从不喜欢把未完成的作品拿给别人看,因此语气很勉强,“没有什么意思的玩艺儿。”
“不会吧?还是让我看看吧,行吗?”
古迪兰把写生簿递过去,杰拉德从船上伸手去接了过来。这时他想起上次见面时,当他坐在马车上转过身来的时候,古迪兰仰起脸对他说的那句话。刹时,一阵强烈的自豪感涌遍他的全身,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被他征服了,除去他们的意识,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强烈的。
仿佛着了魔一样,古迪兰觉得他的身体像沼泽之火似的起伏汹涌着向她扑展过来。他的手臂像茎杆一样直伸着,她感到一种肉体上强烈的恐惧,几乎昏厥过去,头脑一片昏暗,变得不再清醒起来。她在水面上晃动着,就像一闪一闪的磷火。他向船四周看了看,发现它漂开了一些,于是又操起桨把船拉回来。在这深厚柔和的湖水里,慢慢把船拉回来,那种美妙感觉真是令人心醉。
“你画的就是这些,”赫曼尼对着写生簿,一边审视着岸边的植物说。古迪兰顺着她细长的手指望过去。“是那个,对吗?”赫曼尼非要弄清楚似地想得到证实。
“是的。”古迪兰不假思索地回答。
“让我看看。”杰拉德说着就伸手要拿。但赫曼尼没有理睬他。在她看完之前,她没看完之前他别想看。但杰拉德也有着同样不可抗拒的意志,因此他仍向前伸手去拿那写生簿。赫曼尼有些吃惊,同时心中不由地一震动,涌上来一阵对他的反感。还没等他拿稳,她就松了手,夹子掉下去碰了一下船帮又弹入水中。
“噢!”赫曼尼以一种奇怪、恶意又胜利者的口气大声叫,“对不起,实对不起,你能把它捞起来吗?杰拉德。”
她的话语中既透着焦虑又显出对杰拉德的嘲弄,杰拉德被一阵憎恶的感情刺痛了,他使劲探出身子捞那本子,他的腰部暴露出来,使他感到自己的样子很滑稽可笑。
“没什么的。”古迪兰那有力的声音传过来似乎震动了杰拉德。但他还是努力向前伸,小船开始剧烈晃动起来,而赫曼尼却一点也不着急。他的手在水下抓住了那本子拎了上来,水淋淋的。
“噢,我太抱歉了,太对不起了。”赫曼尼一个劲地重复着,“恐怕全是我的责任。”
“这没什么,真的。放心好了,一点都没关系的。”古迪兰大声地强调说,脸色通红地去接那写生簿,有些不耐烦地想急速结束这场面。杰拉德把本子递给她,样子颇有些激动。
“我太抱歉了,”赫曼尼还在重复,使得古迪兰和杰拉德都开始感到厌恶了。“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吗?”
“怎么办?”古迪兰泛泛地讽刺道。
“我们难道无法挽救这些画了吗?”
一阵沉默,显示了古迪兰和杰拉德对赫曼尼的建议的拒绝。
“放心好了。”古迪兰干脆地说,“对我来说,这些画还是完好无损的,我不过是用来当个参考
罢了。”
“但是,我给你个新本子好吗?我希望你别拒绝我。我太抱歉了,我知道那是我的错。”
“就我所见,”古迪兰说,“那根本不是你的错。如果说错,那也是克瑞奇先生的错,不过,这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么计较它就太没必要了。”
当她拒绝赫曼尼时,杰拉德紧紧地盯了她一眼,她身上有一股冷酷的力量。他带着近乎超人的洞察力注视着她,他看到她身上那种危险的带着敌意的劲头,那么不可磨灭,什么也无法战胜她。
“我真太高兴了。”他说,“如果真的没什么损失的话。”
她用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回视着他,那目光直刺入他的灵魂。同时她用一种亲密的近乎是充满爱意的声音对他说:
“当然,一点没事。”
一个眼神,一声话语,两人之间就产生了默契。她的语气明确地表明了她对他的理解——他们是一类人,他和她。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共鸣,从此,她明白,她对他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都能秘密地结成同盟,而他无法摆脱这种联系。她内心一阵狂喜。
“再见了,你原谅了我,我真太高兴了,再会!”
赫曼尼挥动着她的手道别。杰拉德身不由己地拿起桨将小船撑开,但他却不停地用那双闪烁着的充满笑意的眼睛注视着在岸边挥动着那本湿淋淋的写生簿的古迪兰。她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划走了的小船,可杰拉德却边划船边回头看她,早忘了自己手中的桨。
“我们是否划得太偏左了?”坐在花伞下的赫曼尼觉得受了冷落。
杰拉德不作声地四下观望一下,船于是恢复了平衡。
“我看没什么。”他愉快地说,同时又开始没头没脑地划起船来。赫曼尼非常不满他这种欢快而神态游离的态度。也是,她对他不再有效力,她无法再恢复自己的倨傲地位。
第十一章 小岛
此时,欧秀拉已离开威利沃特湖,沿着一条闪亮的小溪漫无目的地缓缓前行。四下里回荡着云雀的鸣啭。山坡上阳光明媚,盛开着的金雀花像燃烧的火焰。小溪畔,一些勿忘我竞相开放。到处是撩人的灿烂景色。
她在这一切中留连忘返。她又想到上游的磨坊贮水池去。那个大磨坊除了有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住在其中的厨房里外就空无一人了。她穿过空旷的农家院子,又走过荒芜的花园,登
上了水闸边的堤岸。当她站在岸顶俯视她面前那古老的天鹅绒般光滑的湖面时,她看到岸边有一个人在修补一只平底船,又敲又打。那是伯基。
她站在水闸顶上注视着他。他一点都意识不到有人来了。他看起来非常忙,像只野兽似的充满精力又专心致志。她觉得她应该走开。他也许不愿她在这儿。他看起来那样全神贯注。但她却不愿走,于是她就在岸上踱着步,想等他能抬头看到她。
很快他果然抬起头了。他一看到她立刻就放下手中的工具,并走上前来招呼道:
“嗨,你好,我正在给这条平底船补漏呢。你觉得怎么样?”
她朝他走过去。
“你是木匠的女儿,你可以告诉我补得怎样。”
她弯下腰去看修补过的船。
“没错儿,我是木匠的女儿,”她说着,却很怕要做出什么判断。“但是我对木匠活一窍不通。它看起来还不错,你说呢?”
“是的。我希望这船不沉就够了,就算沉了也没什么,我还能够上来的。来,帮我一把,把它弄到水里去好吗?”
两个人合力把把船推下了水。
“现在我上去试试,你看着,如果它可以的话,我带你去那个小岛。”
“好!”她边说边紧张地看着。
水塘很大,也非常安静,水面深暗的光泽让人觉得它很深,中间凸起两座覆盖着灌木与树木的小岛。伯基操纵着桨,笨拙地在塘中转向,很幸运,小船漂了过去,他抓住一根柳枝,把船靠上小岛。
“真是草木丛生啊,”他说着向小岛中心望去,“太美了!我就去接你来。这船有些倾斜。”
片刻之后,他们又在一起了。她踏进湿漉漉的小船中。
“这船还行。”他说着,又向小岛划去。
船停泊在一棵柳树下。面对着一片茂盛的气味难闻的无花果和无花果树。她躲闪着,但他却径直往前走。
“我应该把这些都砍掉。”他说,“那就更浪漫了,像《保罗和维吉妮》里的那样。”
“是啊,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华多式①的野餐了。”欧秀拉兴奋地叫着。
①让·安东尼·华多(1684—1727),以描绘牧歌式作品而著名。
“我可不想举行什么华托式的野餐。”
“你只想着你的维吉妮。”她大笑。
“维吉妮就足够了。”他苦笑着说,“甚至连她都不想要。”
欧秀拉紧紧地盯着他,自从布雷德利分别以来,她没有再见过他。他很瘦削,面呈病态。
“你病了,对吗?”她说,感到很受打击。
“是的。”他冷漠地回答说。
他们坐在岛上的僻静处,在柳荫下看着水面。
“你害怕吗?”她说。
“怕什么?”他边问边转过身来望着她。他有一种非人的倔犟,令她不安,令她不能自己。
“生病不是很可怕吗?”她说。
“生病当然不舒服,”他说,“至于人是否真怕死,我还说不准。有时一点也不害怕,有时又非常怕。”
“但它不让你觉得可耻吗?我想生病会使人感到羞耻,病是那样让人感到丢脸。你不这样认为吗?”
他沉思了一会儿。
“也许吧。”他说,“不过人们知道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不那么正确,这才是羞辱。跟这个相比,生病就不算什么了。人生病是因为活得不合适。人活不好就要生病,生病就要受辱。”
“你过得不好吗?”她几乎嘲笑地说。
“噢,是的。我这辈子没取得什么成就。人长鼻子仿佛就是在前进路上用来碰壁的。”
欧秀拉笑起来。她很有些害怕,而当她害怕时,她总是笑,总是做出得意轻松的样子。
“你那可怜的鼻子。”她说着,注视他那轮廓分明的脸。
“怪不得它那么难看。”他回答说。
她沉默了片刻,努力伪装着自己,隐瞒自己的感情。
“可我很幸福——我认为生活充满快乐!〃她说。
“不错。”他冷漠地说。
她伸手在口袋里摸到一小张包巧克力的纸,开始叠小船。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她。她翻动的手指带着一种奇怪的伤感、楚楚动人。
“我真地生活得不错,你呢?”她问。
“噢,是的。可我会因为做不好事情而生气,真的发怒。手忙脚乱时候,就会怎么也做不好事。我不知如何去做。人总得在某些方面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