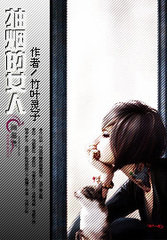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别这样!放开它,让它走,你这个傻瓜!”欧秀拉尖声叫道,完全失去了控制。古迪兰对她这样丧失理智感到讨厌,那声音如此强烈,刺耳,让人无法忍受。
杰拉德的表情坚毅,他利刃般地紧贴住马背,并迫使它原地打转。马喘着粗气咆哮着,鼻孔像两个冒着热气的洞,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圆睁。但杰拉德不为所动,依旧是毫不手软地控制着它,就象一把剑刺入了它的胸膛。人和马都因对抗而大汗淋漓,但他看上去仍然很泰然自若,就象一束冷漠的阳光一样。
与此同时,那火车还在没完没了地隆隆向前驶去,一节又一节,像没有尽头的恶梦,连接车轮的铁链辗过,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枣红马已不再反抗,只是机械地不时扬起前蹄,它已经被征服了,不再恐惧。杰拉德拽着它,把它按下来,就仿佛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流血了!它在流血!”欧秀拉叫着,对杰拉德充满了敌视和憎恨。
当古迪兰看见马的腹部淌下的血时,她的脸变得煞白。她看到,就在伤口处,亮闪闪的
马刺残酷地扎了进去。眼前的世界在旋转,古迪兰一阵眩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她醒过来时,她清醒而平静,没有任何表情。火车的轰轰声仍在,人和马仍在搏斗着,但她却不再紧张激动,她已经对他们毫无感觉了,她的心变得漠然而坚硬。
她们看到列车车厢的末尾正在靠近,煤车的轰鸣声已渐渐远去了,大家终于可以从那难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脱出来了。那马重重地喘息着,马背上的男人松了口气,充满自信,他容光焕发,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列车车厢缓慢地驶过,列车员从他的座位上向外望着路边发生的一切。从那列车员的眼中,古迪兰感觉现在的情景是壮观的、孤立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就象永恒世界中的一个幻觉一样。
列车远去了,四下里变得寂静起来。噢,这平静有多好!欧秀拉愤愤地望着远去的敞篷货车的缓冲器,守闸人已经走出茅屋,过来开门。可不等门打开,欧秀拉就突然一步上前拨开插销,用力推开门,一扇门被推向看门人,而她自己却随着另一扇门跑过去。杰拉德突然间松开马,差点让马的前蹄踏到古迪兰,但她一点都不害怕。当他把马头推向旁边时,古迪兰像一个巫婆似的,用一种奇怪的极高的声音大叫了一声:
“我觉得你也太傲慢了!”
她的话很清晰,骑在马背上的男人禁不住转过身来,惊奇地望了望她。马的前蹄像打鼓般地在道口枕木上敲了三下,人和马便弹簧似的向前跑去,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两个姑娘看着他骑马走远了。看门人一拐一拐地拖着他的那条木腿,踏上枕木,关上了门,然后也回过身来对姑娘们说:“瞧——一个年轻傲慢的骑士,他应该有自己的骑法儿。”
“是的,”欧秀拉大声、专横地说,“可煤车开过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马拉开呢?他是个大傻瓜,一个虐待狂,他以为他那样折磨一匹马,就能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吗?它是
个活生生的东西,他凭什么要欺负、折磨它呢?”
守门人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是啊,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匹好马,一个可爱的小东西。你们永远不会看到他的父亲会那样对待动物。杰拉德·克里奇跟他爸爸一点都不一样,不同,绝对不同。”
又是一阵沉默。
“但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欧秀拉喊,“为什么?他觉得当他虐待一匹比他还敏感十倍的小生物的时候,他很了不起吗?”
又接着一阵沉默,而守门人摇了摇头,似乎他不想说什么,而是要再想一想。
“我猜想他大概是想训练他的马能忍受任何事情,”他回答说:“那是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跟咱们这的马不同。据说这马是从君士坦丁堡①那边弄来的。”
①今名伊斯坦布尔,1923年前的土耳其首都。
“他会这样干的。”欧秀拉说:“我想他最好还是把它留给土耳其人,他们会更好地对待它。”
看门人进屋继续喝他的茶,两个姑娘走上一条被柔柔的一层煤灰覆盖着的乡间小路,古迪兰被杰拉德横暴地骑在马上的景象惊呆了,那男人不可征服般骑在那马的身上,强有力的大腿紧紧夹住那受惊的马,完全控制了它,那胯部、大腿和小腿肚,似乎有种白色的柔和的磁力,左右着它,使它完全屈服。
两位姑娘无声地走着。在左边,煤矿堆得高高的,黑色的铁轨和停着的货车,这里看上去就象一座巨大的港湾。
就在那个很多闪亮的铁轨交错的第二条铁道口旁边,有一个属于煤矿的农场,矿石堆中放着一只废弃的大锅,锅已经生满了锈,静静地立在路边。母鸡们围在四周找食吃,一些小鸡排在水槽前饮水,几只鹡鸰从水中飞到车厢里。
叉路口的另一边,堆着一堆用来修路的灰石头,旁边停着一辆车,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子靠着他的铁锹,正在和另外一个套着绑腿的小伙子交谈,那小伙子站在马头前,他们两人都面对叉路口看着。
他们看见两个姑娘走了过来。在下午强烈的阳光下,那是两个耀眼的身影。两个姑娘都身着浅色的轻松活泼的夏装:欧秀拉穿一件桔黄色的上衣,古迪兰是一件淡黄色的;欧秀拉脚穿嫩黄色的长筒袜,而吉德兰的是亮丽的玫瑰色,两个姑娘走在宽阔的交叉道上,她们身上白的桔黄的浅黄的玫瑰色的亮色,在布满煤灰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两个男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站着观望,那个老一点的,是个矮个子,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严肃的脸孔,年轻一点的工人,大约二十三岁左右。他们静悄悄地站在那儿看两个姑娘走过来,走近了,又走过去,直到她俩在满是煤灰的路上消失了。
这时,那个年长的男人一脸馋相地对年轻人说:
“那个值多少钱?她会做的,是吗?”
“哪个?”年轻人笑着急切地问。
“那个穿着红色袜子的,你说呢?我愿意付我一星期的工钱,就五分钟,嗯?只要五分钟!”
年轻人大笑起来。
“你老婆会找你算账的。”他说。
古迪兰转过身来,瞪着那两个男子,他俩站在灰白的煤渣堆旁紧盯着她看,象两个凶恶的怪物。她讨厌那个满脸络腮胡的人。
“你真是第一流的。”那人远远地冲她喊。
“你觉得她值一星期的工钱吗?”年轻人打趣说。
“我吗?我愿意马上就付钱……”
那年轻人目送着欧秀拉和古迪兰,似乎想计算一下,她们哪里值他一星期的工钱。他摇了摇头,还是不明白。
“不,”他说“不值那么多。”
“不值?”年长者说:“我的天,对我来说可是太值了。”
说完他又开始铲石头。
姐妹俩下到矿区街上,从斜顶黑砖墙的房子中穿过。浓重的金色夕阳笼罩着整个煤区,丑陋的矿区上涂抹着一层美丽的夕阳。在铺满煤灰的路面上,阳光显得越发温暖、厚重,这给这片乱七八糟、肮脏不堪的矿区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真是个美丽又可恶的地方。”古迪兰说虽然不太喜欢这些神奇的景色,“你是否觉得这景色很迷人?它雄浑,火热。我可以感觉出来这一点。这真令我吃惊。”
从一排排的矿工的居所间经过时,她们不时会看到一些矿工在后院的露天地里洗身子。矿工们上身赤裸,厚厚的大裤子几乎要滑下去,已经洗过澡的矿工们背靠站墙蹲着聊天,他们身体都很健壮,劳累了一天,正好歇口气。他们的声音很粗,浓重的方言虽奇怪,却令人感到亲切。古迪兰像是置身于劳动者的怀抱中,到处都是一种深沉的男子的气息,空气中有一种浓厚的劳动者的味道,但这些在这一带是司空见惯的,因此没人去注意它。
可对古迪兰来说,这种气味却太强烈了,甚至有些令她反感。她也无法说出为什么贝尔多弗同伦敦或者更南部有那么大的差别,在这里,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现在她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男人们很强盛,他们大多时间里都生活在地下黑暗的世界里。从他们的话语里,她可以分辨出那来自黑暗的银荡的声音,没有人性、无所顾及,他们说话像上了油的笨重而奇怪的机器,那银荡的音调也象机器声,冰冷,残酷。
每天晚上回家她都遇到同样的景象,她像是从一股巨大的分裂波中穿过,它来自千万个精力旺盛的半自动化的低层矿工,直钻入她的大脑、她的心脏,唤醒她那致命的欲望和冷漠心情。
一股怀旧之情涌上来。她恨这个地方,她知道这里是多么的闭塞、多么的落后、多么的麻木无情。不过,她还是深深眷恋这个地方。她努力使自己变得与这个地方和谐,渴望从中
获得满足。
一到晚上,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来到镇上的大道上。这里也同样丑陋,同样充满了那种浓烈的阴暗冷漠的氛围,周围有很多矿工,他们带着一种奇怪的扭曲的威严,一种特殊的美丽行走着,透着一般不自然的宁静,一种木然顺从的神情挂在他们苍白而憔悴的脸上,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们有着奇特的迷人之处,声音浑厚洪亮,象机器轰鸣,象音乐,比远古时的汽笛声更迷人。
她发现自己也和其她的普通妇女一样,每个周五晚上都会来到小市场。星期五是矿工们发工资的日子,晚上就成了逛市场的时候了。每个妇女都走出来,矿工们也跟着妻子一起出来,或是跟跟朋友们聚聚。黑压压的人行道有几里长,都挤满了人,在半山腰上的小市场和贝尔多弗的大路上,挤满了男人和女人们。
天己黑了,可市场上的煤油灯却燃得热乎乎的,摇曳的灯光照着每个主妇阴沉沉的脸和男人们苍白木讷的脸,空气中弥漫着人们大喊大叫的声音,密密的人流在小市场的人行道上涌动,商店里边挤满了妇女,路中间站着的则几乎都是男子,是各种年龄的矿工。
开过来的马车无法从这拥挤的路上开过去,车夫们只好停下来又叫又喊,直到密密的人群闪出一条道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见远处来的年轻小伙子站在路上或角落里跟姑娘们聊着天。小酒店的门全都开着,灯火通明。男人们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到处可见男人们打招呼,或走来走去,或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没完没了地讨论,刺耳的说话声,无休止的采矿声和政治性的争吵声混杂在一起,在室中像一部不协调的机器发出的轰鸣声。可就是这些人的声音令古迪兰神魂颠倒。这声音令她眷恋,令她渴望的心儿发痛、发疯、令她感到难以自己,这感觉真是莫明其妙。
像其她的普通女孩子一样,古迪兰也在这段小市场附近的不足两百步的人行道上来回地踱着步。她知道这样做很庸俗,她父母无法忍受她的这种行为,可她眷恋这里,她必须置身于这些人们之中。有时候她会在电影院里,坐在一群粗俗的年轻人当中,一群放荡、毫无吸引力的大老粗当中。可她一定要坐在他们中间。
也像其她普通姑娘一样,她也找到了她的“小伙子”。他是个电工,一个由杰拉德的新计划招来的电工,他是个上进、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对社会学怀着极大热情的科学家。他在威利·格林租了间农舍,独自居住。他很有风度,也非常有钱。他的女房东到处吹嘘他,说他有个大木澡盆安在他的房间里,每天他上完班回来,他都会打一桶桶的水来洗澡,然后换上干净的衬衫和内衣,还有干净的丝质袜子。在这些方面他似乎过分挑剔、苛求,但在别的方面他则再普通不过了,一点都不装腔作势。
古迪兰很了解这一切,这些闲言碎语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传到布朗文家中来。帕尔莫和欧秀拉更要好些,但是他那苍白、英俊、严肃的脸上流露出和古迪兰一样的怀旧情绪。他每个周五晚上也一样要去大街上走走,所以他和古迪兰走到了一起。但他无法爱古迪兰,他真正爱的是欧秀拉,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跟欧秀拉就是没缘分。他喜欢古迪兰在她身边,作为一个交流思想的伙伴——那就是全部。她对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他是个科学工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女人支持他,但他实际却是个不动感情的人,就象一架高雅漂亮的机器。他太冷漠、太消极,从不会去真正关心女人,是一个完全的自我主义者。他从那些男人中分化出来,就个别来说,他讨厌痛恨他们,就整体而言,他又很迷恋他们,就像迷恋机器那样,他们对他来说像一台新型机器。
古迪兰就这样跟帕尔莫一起散步,一起去电影院,他那长长的苍白而又相当英俊的脸,每当他发表嘲讽性言论时,就会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个都很清高;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俩又都追随着人群,与这些丑陋的矿工们溶为一体。这一秘密似乎在所有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