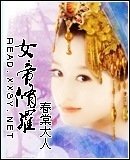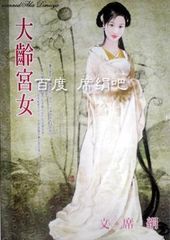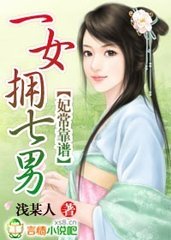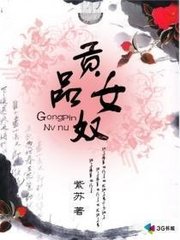茶花女-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和话剧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表现手法自然就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很难对二者进行比较。小说《茶花女》是一气呵成的,看得出作者在情节的布局和剪裁方面并没有下很大的功夫,作者似乎是凭着一股激情,挥手之间便完成了这部作品。因此小说写得朴实动人,充满着一腔怨愤,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小说《茶花女》问世的时候,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经渐趋式微,但是这部小说仍然散发着一股颇为强烈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遗书一篇比一篇更加动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这批遗书读起来声声哀怨,字字血泪,回肠荡气,酣畅淋漓,致使整篇小说在感情奔放的高潮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而话剧《茶花女》固然也是一气呵成,但它毕竟是作者自己的再创造。小仲马不必再为构思故事情节而苦思冥想,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剧情的安排和场次的衔接方面,即如何使戏剧冲突更加强烈,更加动人。这个目的小仲马显然是达到了。而且做得相当成功。话剧《茶花女》的第三幕演出了阿尔芒的父亲威胁利诱玛格丽特,迫使她同阿尔芒断绝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情节在小说里却没有直接的描写,它是通过玛格丽特的日记和书信间接加以说明的。话剧的这一处理是必要的,因而也是高明的,因为它把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直接揭示出来。其戏剧效果之强烈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没有必要据此断言话剧《茶花女》的思想意义更深刻,对不平等的社会道德观念的批判更激烈。因为把阿尔芒的父亲粗暴干涉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爱情的无耻行为在舞台上直接表现出来,这是话剧在艺术处理上的需要。可以设想,倘若由阿尔芒本人在话剧结束之前涕泪交流地一封一封念出玛格丽特书信的内容,其艺术魅力肯定要大大地打折扣的。因此,从作品的风格来看,我以为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说《茶花女》流畅而自然,但却略显松散,而话剧《茶花女》则更加强烈、紧凑,但不免微露斧凿的痕迹;两者可以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至于歌剧《茶花女》的成就,那就请音乐界的专家们来做评价吧!不过我想,无论小说《茶花女》、话剧《茶花女》还是歌剧《茶花女》,它们都是成功的佳作。小说《茶花女》风靡整个世界,话剧《茶花女》历演不衰,而歌剧《茶花女》一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值得一提的还有,自一九○九年以来,《茶花女》已经被搬上银幕多达二十余次,其中最著名的则是格丽泰·嘉宝主演的影片《茶花女》,它已经成为世界电影艺术宝库中的一部珍品。
而在中国,《茶花女》则可以说是读者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便用文言体翻译、出版了小说《茶花女》(中文译本的书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的译文虽然未必完全忠实于法文本原著,但他那生动传神、极富形象化的语言使小说《茶花女》的第一部中译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Quine,1908—)为代表。继承逻辑实证主义,把语言分析作,人们又陆陆续续读到了刘半农等人翻译的话剧《茶花女》和夏康农等人翻译的小说《茶花女》。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爱情故事能够在中国的读者群中迅速流传,深入人心,外国文学翻译界的这些前辈们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九四九年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这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内,《茶花女》却经历了一番曲曲折折的遭遇。这样一部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居然没有新译本奉献给新中国的读者,而旧译本的再版为数也极为有限,到了后来,《茶花女》干脆销声匿迹了,以至于在年轻一代的读者心目中,《茶花女》不仅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甚至还顶着种种不应该有的恶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终于重见天日,振孙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着手翻译小说《茶花女》的,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的新译本《茶花女》不仅忠实于法文原著,而且生动地表达了原作的感情色彩,因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小说《茶花女》新译本自一九八○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至今累计印数已达百万余册,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部中译本。
在中国的读者中间,读过小说《茶花女》的很多,而看过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的却较少,对三部《茶花女》之间的差异所知则更少。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将三种体裁的《茶花女》合在一起的译本,其中小说《茶花女》是一九八○年的译文,此次出版,译者又进行了精心的修改;而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则是译者的新译作。值得一提的是歌剧《茶花女》是用诗体译出的,译文大体整齐,而且精练匀称,富有节奏感,很好地表现了原作的韵味。我以为,三部《茶花女》的合译本首次在我国出版,也算得上是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件大好事,想必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欢迎。
一九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夕,寒流侵袭巴黎。我和妻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又走进了蒙马特公墓,想在这万家欢乐的节日期间再一次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和葬在距她不远处的小仲马的墓前凭吊一番。空荡荡的墓园萧索凄冷,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光裸的树枝在朔风中瑟瑟颤抖。但是积极的批判,而不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或历史决定论。以匈牙,当我走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墓前时,我惊异地发现,她的墓上放着一束茶花,花很新鲜,显然有人刚刚来过这里。再仔细一瞧,我更加大吃一惊,因为我分明看见在这束茶花旁边还放着一支口红。我想,也许这位凭吊者是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不要辜负自己的花容月貌吧!尽管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与茶花女玛格丽特绝非一人,但是前来敬献茶花的人显然还是把阿尔丰西娜当成了茶花女。看来茶花女果真没有死,她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
我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和小仲马的墓前盘桓了一阵,心里默默地想着:茶花女玛格丽特不朽,《茶花女》不朽,《茶花女》的作者不朽!
王聿蔚
一九九三年元旦于巴黎
第01节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如果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出面证实。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列宁指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因为唯独我洞悉这件事情的始末,除了我谁也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来。
下面就来讲讲我是怎样知道这些详情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拍卖家具和大量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我心想,这一回可不能坐失良机,即使不买,也要去看看。
第二天,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时间还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却都带着惊讶、甚至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不久,我就懂得了她们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我也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很快就看出了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①的房间里。然而上流社会的女人——这里正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想看看的也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这种女人的穿着打扮往往使这些贵妇人相形见绌;这种女人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人歌剧院里,也像她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和她们并肩而坐;这种女人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播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①原文是指“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这个住宅里的妓女已经死了,因此现在连最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的空气。再说,如果有必要,她们可以推托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见识一下广告上介绍的东西,预先挑选一番,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这一切精致的陈设里面去探索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有关妓女的非常离奇的故事。
不幸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
消逝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里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能对着死者身后要拍卖的东西啧啧称羡,却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房客在世时所操的神女生涯的痕迹。
不过,可以买的东西还真不少。房间陈设富丽堂皇,布尔①雕刻的和玫瑰木②的家具、塞弗尔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真是目不暇接,应有尽有。
我跟着那些比我先来的好奇的名媛淑女在住宅里漫步溜达。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的当儿,她们却几乎马上笑着退了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害臊,我倒反而更想进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梳妆间,里面摆满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里似乎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造的各种各样的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上千件小玩意儿对于我们来参观的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而且没有一件不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制成的。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逐件收罗起来的,而且也不可能是某个情夫一人所能办齐的——
①布尔(1642—1732):法国有名的乌木雕刻家,擅长在木制家具上精工镶嵌。
②玫瑰木产于巴西,因有玫瑰香味而得名。
③塞弗尔:法国城市,有名的瓷器工业中心。
④萨克森:德国一地区,瓷器工业中心。
⑤奥科克和奥迪奥:十八、十九世纪时巴黎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奥科克擅长帝国风格,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法国银行的茶炊和罗马王的摇篮。
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梳妆间倒没有厌恶的心情,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趣地细细鉴赏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各种不同的人名首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①标记——
①当时的贵族,多将其纹章镌刻于家用器物上,作为标记。
我瞧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肉体买卖。我心想,天主对她尚算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晚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之中。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的确,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晚年——更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没有一点点尊严,引不起别人的丝毫同情,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因为她们并不是追悔过去的失足,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样美丽。她母亲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从小养到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旨意,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就像是有人想要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时期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是从早年就开始了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来孱弱多病,抑制了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这种才智天主可能也曾赋予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去让它得到施展。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