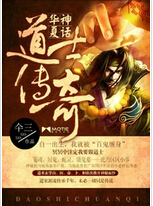安徒生童话-第1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怎么喜欢一个男人那样喜欢你,我却从未做到过!——这一点你必须忍受!——再会了,安东!”
安东也道了别!他的眼中没有一滴泪水。他感到,他再不是莫莉的朋友了。一根炽热的铁棍和一根冰冻的铁棍在我们亲吻它们的时候,引起我们嘴唇皮的感觉是相同的,它们咬噬着我们的嘴皮。他用同样的力度吻着爱,也吻着恨。不到一个昼夜他便又回到了艾森纳赫,可是他的乘骑却也就毁了。
“有什么说的!”他说道,“我也毁了,我要把能令我想起她来的一切东西都摧毁掉:霍勒夫人、维纳斯夫人,不信仰基督的女人!——我要把苹果树折断,把它连根刨起!它绝不能再开花,再结果!”
可是,苹果树并没有被毁掉,他自身却被毁了,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什么能再救助他呢?送来了一种能救他的药,能找到的最苦的药,在他的有病的身躯里,在他的那萎缩的灵魂里翻腾的那种药:安东的父亲再不是那富有的商贾了。沉重的日子,考验的日子来到了家门前。不幸冲了进来,像汹涌的巨浪一下子击进了那富有的家庭。父亲穷了,悲伤和不幸击瘫了他。这时安东不能再浸在爱情的苦痛里,再想着怨恨莫莉,他有别的东西要想了。现在他要在家中又当父亲又当母亲了,他必须安顿家,必须料理家,必须真正动起手来,自己走进那大千世界,挣钱糊口。
他来到了不来梅,尝尽了艰辛和度着困难的日子。这难熬的岁月令他心肠变硬,令他心肠变软,常常是过于软弱。世界和人与他在孩提时代所想是多么的不一样啊!咏唱诗人的诗现在对他如何:叮噹一阵响声罢了!一阵饶舌罢了!是啊,有时他就是这样想的。不过在另外的时候,那些诗歌又在他的心灵中鸣唱起来,他的思想又虔诚起来。
“上帝的旨意是最恰当不过的!”他于是说道,“上帝没有让莫莉的心总是眷恋着我,这是件好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幸福现在不是离我而去了吗!在她知道或者想到我那富裕的生活会出现这样的巨变之前就离我而去。这是上帝对我的仁慈,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妥善的!一切正在发生的都是明智的!都不是她力所能及的,而我却这么尖刻地对她怀着敌意!”岁月流逝。安东的父亲溘然离世,祖房里住进了外人。然而安东很想再看看它,他的富有的东家派他出差,他顺路经过他的出生城市艾森纳赫。老瓦特堡依然矗立在山上,那“修士和修女⑩”山崖依旧和往日一个样子;巨大的橡树仍像他儿童时代那样,显露出同样的轮廓。维纳斯山在山谷里兀立着,光秃秃地,发着灰色的光。他真想说:“霍勒夫人,霍勒夫人!把山打开,我便可以在家园故士安眠!”
这是有罪的想法,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这时一只小鸟在矮丛里歌唱,他的脑中又浮现了那古老的短歌:
从树林那边,在静静的山谷中,
坦达拉莱依!
传来了夜莺的歌声!
他透过泪珠观看自己这孩提时代的城市,回忆起许多往事。祖房犹如昔日,只是花园改变了,一条田间小道穿过了昔日花园的一角。那棵他没有毁掉的苹果树还在,不过已经被隔在花园外面小道的另外一侧了。只不过阳光仍和往日一样照晒着它,露水依旧滋润着它,它结着满树的果实,枝子都被压弯垂向地面。
“它很茂盛!”他说道,“它会的!”
有一根大枝则被折断了,是一双讨厌的手干的,你们知道,这树离开公用的道路太近了。
“他们摘它的花,连谢都不道一声,他们偷果实,折树枝。可以说,我们谈论一棵树,就和谈论一个人是一样的:一棵树在自己的摇篮里,哪里想得到它会像今天这样。一段经历开始得那么美好,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被丢弃,被遗忘,成了沟边的一棵普通树,站到了田头路边!它长在那里得不到一点保护,任人肆虐攀折!尽管它并没有因此而枯萎,但是一年年它的花越来越少,不再结实,直到最后——是啊,这一段经历便这样结束了!”
安东在那棵树下想着这些,在孤寂的小屋里,在木房子里,在异乡,在哥本哈根的小屋街里,他在无数的夜晚想着这些。是他的富有的东家,不来梅的商人派他来的,条件是,他不可以结婚。
“结婚!哈哈!”他深沉奇怪地大笑。
冬天来得早,寒气刺人。屋外有暴风雪,所以只要可能便总是躲在家里。这样,安东对面居住的人就没有注意到安东的屋子整整两天没有开门了,他自己根本没有露面,只要能够不出门,谁愿在这样的天气跑到外面去?
天日灰暗,你知道对那些窗子上装的不是玻璃的住家来说,时时都是乌黑的夜。老安东有整整两天根本没有下床,他没有气力这么做;外面那恶劣的天气他的躯体早感觉到了。这老胡椒汉子躺在床上无人照料,自己又没法照料自己,他连伸手去够水罐的力气都没有了。而那水罐,他把它就放在床边,里面的最后一滴水也被喝光了。他没有发烧,他没有病,是衰迈的年龄打击了他。在他躺着的地方的四周几乎就是永无止境的夜。一只小蜘蛛,那他看不见的蜘蛛,满意地,忙碌地在他的身子上方织着网,就好像老人在阖上自己眼睛的时候,依然有一丝清新的悲纱在飘扬一样。
时间是这么长,死一般地空洞;泪已干,痛楚也已消失;莫莉根本不存在他的思想里。他有一种感觉,世界和世上的喧嚣已不再是他的,他躺在那一切之外,没有人想着他。在短暂的一瞬间,他感觉到了饥饿,也感到了渴,——是的,他感到了!可是没有谁来喂他,谁也不会来。他想起那些生活艰难的人来,他想起那圣洁的伊丽莎白还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她,他家乡和自己孩童时代的圣女,图林根高贵的王子夫人,高贵的夫人,是怎么样亲自走进最贫困的环境里给病人带去了希望和食物。她的虔诚的善行在他的思想中发光,他记得,她是怎么样走去对遭受苦难的人吐露安慰之词的,怎么样给受伤的人医治创伤,给挨饥受饿的人送去食物,尽管她的严厉的丈夫对于这些很恼怒。他记得关于她的传说,在她提着满装着酒和食品的篮子出门的时候,他的丈夫怎么样监视着她,突然闯出来气愤地问她,她提着的是什么。她在恐慌中回答说是她从花园里摘的玫瑰。他把盖布揭开,为这位虔诚的妇女而出现了奇迹,酒和面包、篮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玫瑰。
这位女圣人就是这样活在老安东的思想中,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疲惫的眼神里,出现在丹麦国家他那简陋的木棚里他的床前。他伸出他的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四周都是光彩和玫瑰,是啊,这些色彩和花自己又展开成为一片,气味好闻极了。他感觉到一种特别美的苹果香味,他看见那是一棵盛开花朵的苹果树,他和莫莉用种籽种下的。树将自己芳香的花瓣散落到他的发烧的脸上,使它冷却下来;叶子垂落到他的渴涸的嘴唇上,就像是使人神智焕发的酒和面包;它们落在他的胸口上,他感到很轻松,很安详,催人欲睡。
“现在我要睡了!”他静静地细声说道,“睡眠使人精神!明天我便痊愈了,便会好了起来!真好啊!真好啊!怀着爱心种下那棵苹果树,我看见它繁荣密茂!”
他睡去了。
第二天,那是这屋子的门关上的第三天,雪停了,对面的人家来探望压根就没有露面的老安东。他平躺着死去了,那顶老睡帽被他捏在手中。入殓时他没有戴这一顶,他还有一顶,干净洁白的。
他落下的那些泪都到哪里去了?那些珍珠哪里去了?它们在睡帽里,——真正的泪是洗不掉的——它们留在睡帽里,被人遗忘了,——老的思想,老的梦,是啊,它们依旧在胡椒汉子的睡帽里。别想要它!它会让你的脸烧得绯红,它会让你的脉博加快,会叫你做梦,就像真的一样。第一个人试了试它,那个把它戴上的人,不过那是安东死后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是市长本人。这位市长夫人有十一个孩子,家里日子很好;他一下子就梦见了婚变,破产和无衣无食。
“嗬!这睡帽真让人发热!”他说道,扯下了睡帽,一滴珍珠,又一滴珍珠滚了出来落地有声有光。“我关节炎发了!”市长说道,“它很刺我的眼!”
那是泪,半个世纪以前哭出的泪,艾森纳赫的老安东哭出的泪。
不论谁后来戴上这顶睡帽,他都真的坠入幻境,做起梦来,他自己的故事变成安东的,成了一个完整的童话,很多的童话,别人可以来讲。现在我们讲了第一篇,我们这一篇的最后的话是:永远也不要想戴上胡椒汉子的睡帽。
题注:这里的光棍汉的丹麦文原文的原意是“胡椒汉子”。为什么这样叫,安徒生在故事中有详细的叙述。
①在丹麦文中“赫斯肯”一字只见于哥本哈根的赫斯肯街街名中。赫斯肯是丹麦人对德语HaAusehen(小屋)的讹读。这条街之所以有个德语名字,安徒生在此篇故事中的叙述很详尽。
②德国中北部的两个城市。
③即哥本哈根的皇宫岛。
④据中古时期德国流传的说法,瓦特堡附近有维纳斯山,是维纳斯女神设神廷的地方。凡被诱误入这座山的人均要交付巨额赎金才得获释。把维纳斯称为维纳斯夫人则又建立在更古的传说,说这山中藏着一位霍勒夫人。
⑤奥地利13世纪民歌手。据传说,他曾一度居住在维纳斯山中。关于汤豪舍和瓦特堡赛歌会的事请见《凤凰鸟》注8。
⑥匈牙利公主(1207—1231),图林根王子路德维希四世的王后。⑦克尔特人的传说中的人物。马尔克斯派遣他的侄子特里斯坦到爱尔兰代表他向公主伊索尔德求婚。马尔克斯的求婚得到接受。特里斯坦陪同伊索尔德返回的途中,两人误饮了伊索尔德的母亲赠送给伊索尔德和马尔克斯的魔酒。这种酒有魔力能使夫妇永远相爱。回到马尔克斯身旁后,三人之间发生了多次冲突,最后马尔克斯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赶出了森林。两人在分手前,曾在这森林中共同艰苦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特里斯坦后来和另一个也叫伊索尔德的女子结婚。但特里斯坦始终未忘记前一个伊索尔德的旧情。后来特里斯坦在一次斗殴中受重伤;这伤只有第一位伊索尔德能治疗。她赶来救治特里斯坦但却为时已晚,特里斯坦已死去。
卡尔·因默曼曾写过一部题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41年)的小说。安徒生有此书。
⑧特里斯坦这个字与丹麦文的悽怆同音。
⑨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1168—1228),德国咏唱诗人,于1205—1211年间附从于图林根赫尔曼王室。
⑩瓦特堡宫北500米的一段山。
===================
()
做出点样子来
“我要做出点样子来!”五兄弟中最年长的那位说,“我要对世界有用处,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地位,只要有好处就行,我干一样,就会干出点样子来。我要烧砖,这东西人是不能少的,这样我总算做出点样子来了!”
“可是你做的那点样子太不足道了!”二弟这么说,“你那点样子几乎等于零;那是打下手的活,可以用机器做。不行,最好还是当泥水匠,那总算有点样子,我要做泥水匠。这是一种地位!当上了泥水匠,就可以进入行会,成市民,可以挂起自己的幡子,进自家本行的小酒馆。是的,要是干得不错,我还可以雇学徒工,被人称做师傅①,我的妻子也就成了师母。这才像做出了点样子!”
“那根本不算什么!”老三说道,“那是排在等级之外的,城市里等级多着呢,师傅上面一大串,你可以是个忠诚的老好人,可是即使当上了师傅,你还只不过是大家说的‘普通人’!
不行,我知道一种更好一点的!我要去做建筑师,踏进艺术界、思想界,在精神世界里上到高一些的层次里去。诚然我得从下面开始,是的子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后代思想家多主张“正,我可以直说:我开始可以干木匠小工,戴顶便帽,虽然我习惯戴丝帽,为那些普通学徒跑腿拿啤酒、拿烧酒,他们会直呼我为你②,这很不体面!但是我可以把这一切当成一场化装表演,是一张带脸谱的执照!转天——也就是说,我正式成了学徒之后,我便会走我自己的路,别人跟我没关系!我进艺术学院、学绘画,别人称我为建筑设计师——这才算做出了点样子!这是了不起的!我可以跻身‘高贵的、尊敬先生’的级别里③。是啊,名字前、名字后都加上了这么点头衔,我不停地建,不断地建,就像我前面的那些人一样!总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