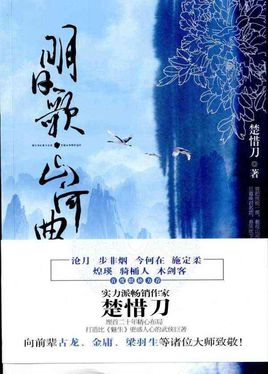山路·山妞和光棍-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刀不断江流水,
风雪难摧腊梅魂,
多少痴情农家女,
千古情话说到今。
欲知茉莉和柳叶谁能接到惠民,且往下看。
第九回 久别重逢情人相会 狭路相遇魔鬼缠身
茉莉走了三十华里土路,先于柳叶到达车站。班车到站了,接站送站和下车上车的人都很多。一个满面红光,身材魁伟的武警战士下了车。
“惠民哥,快把提包给我。”茉莉说。
“没带多少东西,我自己拿吧。”惠民说。
一对情侣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四目对视。泪珠从茉莉的眼角滚下来。
她从头到脚把他看了一遍。他没啥大的变化,看上去比一年前变老成些了。
这小伙子的确出类拔萃,浓眉大眼,身强体键,一米八的大个,往人群里一站,特别显眼。不怨头道沟的人都夸他要人样有人样,要文化有文化,要心计有心计,要活计有活计,要口才有口才。难怪每当惠民走在路上时,相遇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回头多瞅几眼。
他也仔细地端详着她。她又出息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瓜子脸,白净面,柳叶眉,樱桃口,粉嘴唇,珍珠牙,黑亮发,不高不矮的身材,不胖不瘦的体态,比例匀称的肢体。真不晓得,天天吃大苞米,怎么能长出这么标致的模样来。只是穿戴太寒酸了。头上围的红围巾补上了补丁。上身穿的是惠民去年探家时给她的一件草绿色的军装,下身穿的是一条蓝色的制服裤。衣服的肘臀膝等部位都上了补丁。衣服虽旧,但是往茉莉身上一穿,既干净利索,又贴身合体,大姑娘的动人曲线能充分体现出来。不愿村里人都夸,茉莉真是一个美人样子。
柳叶比茉莉晚到了一会。她到车站的时候,茉莉已经接到了惠民。
柳叶眼望着茉莉和惠民,五腑六脏里就像是灌满了老陈醋。
茉莉、惠民并肩走进了一个小饭店。
柳叶找了一个大车店,向店里的伙计要了一碗开水,嚼了一个从家里带来的棒子面窝头。
茉莉和惠民吃过饭后,上了回家的路。
柳叶拖着沉重的脚步,远远地跟在茉莉和惠民后边。
惠民和茉莉的思绪都回到了从前。
三年前,送惠民参军时,茉莉流着泪把一双亲手做的布鞋塞进惠民的挎包里。今天,惠民穿的就是那双鞋。鞋还是崭新的,看来他始终没舍得穿。
三年里,无数次鸿雁传书,倾诉心里不尽的相思。
熬过那么多思念的日夜,终于又盼来了重逢的日子。
他们走得很慢,为的是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倾诉相思之苦。两人步行在回家的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边走边说,一对恋人有说不尽的相思,道不完的情话,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落山之时。
红霞的映衬下,
寂静的山冈上,
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悄悄地走近,
完成着一次期盼已久的长吻。
紧紧地手拉手,
实实地口对口,
密密地心贴心,
牢牢地头挨头。
没有多少爱语的表白,
没有多少情话的诉说,
只有滚烫的热泪和紧紧的拥抱。
深爱无言,
彼此知道亲爱的人心里在说什么。
时间停止了,
空间凝固了,
宇宙膨胀了。
混沌世界,万物顿逝。
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
金风玉露相逢,
胜过人间无数。
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的相思之苦,
在顷刻间烟消云散。
“亲爱的,俺怕啥,爱何罪之有。”
急促的心跳表达的是内心的强音,
无主的鼻息展示的是肺腑的呼唤,
忘我的呢喃抒发的是由衷的快感,
滚烫的热泪流动的是积累的厚爱,
发烧的脸庞散发的是压抑的深情,
扭动的身躯传送的是爱慕的心声。
你匆匆离开时我牵肠挂肚,
你迟迟无信时我没着没落,
你久久不归时我魂牵梦绕,
你缓缓走来时我脸热心跳。
在酷暑里想起你神清气爽,
在寒冬里想起你寒意顿消。
多少次梦境里梦话惊醒爹娘,
多少个不眠夜泪水浸湿发稍。
“亲爱的,俺怕啥,爱何罪之有。”
紧紧地拉住你,
是怕你再走掉。
实实地抱住你,
是想把你栓牢。
我以虔诚的心祷告上苍:
风不要刮,树不要动,
鸟不要鸣,犬不要叫。
让一次长吻到天亮,
让一次拥抱到明朝。
吻他个海枯石烂,
吻他个地动山摇,
吻他个天长地久,
吻他个神魂颠倒。
让大地为爱飞歌,
让江河为爱奏乐,
让长空为爱喝彩,
让山峦为爱撑腰。
惊他个闭月羞花,
吓他个灵魂出窍,
骇他个沉鱼落燕,
折他个霜剑风刀。
惠民为茉莉拭去泪水,借着星光,仔细端详着茉莉的芳容。劳累夺去了应有的娇嫩,山风吹去了应有的红润,生活的艰辛使她显得有些憔悴。惠民心疼地说:“莉妹,你又瘦了。”
“惠民哥,我天天劳累不说,还天天想你,家里又逼着我和一头圪猱结婚,你说我还能有个人样吗?这回好了,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我又有主心骨了。”
“莉妹,你爹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爹和一头圪猱他爹喝酒时商量过这事,让小混子听到了,小混子把这事告诉我弟弟了,我弟弟又告诉了我。说是日子定在阴历九月初二。还设计了一个圈套,要把我弄迷糊以后接去。你听说过吗?可天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爹啊。”茉莉把易八卦和一枝花设计的“瞒天过海”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说到伤心处,茉莉泪如泉涌。
惠民说:“莉妹,别着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是指定不让他接去。”
茉莉说:“二脱产说了,不给人就要钱,不还钱就要人,两条道,让我爹任选一条。”
惠民问:“你家一共用了二脱产家多少钱?”
茉莉回答:“我问过我娘,我娘说,这些钱不是一次要的。我爹就认钱,一有个为难着窄,就去求人家老金家,他把我当成摇钱树,把老金家当成了他的聚宝盆了。我听我妈念叨过,说是他们闹悔婚之前花了人家八百多元,闹悔婚当时人家一次给了一千。这几年,我娘我爹治病又花了人家很多钱,叽叽嘎嘎,零拉不可整算,今天五十,明天一百,积累起来,往少说又有一千多了。这样累计起来就是两千八百多。
“要是咱们提出退婚,二脱产肯定要利钱。连本带利总有五千多了。凭良心说,我家确实花了金家不少钱。就我家那种情况,想还钱,除非是驴长犄角牛打滚。所以我爹下了狠心,非逼我和一头圪猱成婚不可。
“前几天,二脱产手里掐着那几张毛头纸,找过我爹,说是按着当时的约定,早就过了娶我的期限了。我爹也给我看了那些毛头纸。我从我爹手中接过毛头纸一看,那上头果然写着‘金玉柱钱茉莉到了法定年龄,即可完婚。结婚的具体事宜,由金、钱两家商定’的话。在一气之下,我撕碎了那些毛头纸。我爹气得暴跳如雷,打了我一巴掌。要不是哑巴哥拦住我爹,我爹准得狠狠地揍我一顿不可,到现在他也不和我过话。
“惠民哥,你快给我拿个主意吧。这么多钱,上哪弄去啊?何况再有二十多天就到日子了。都说钱不是万能的,我现在可知道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是有钱,这婚早就退了。惠民哥,你没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我要走,跳出这个火坑,出去打工挣钱,攒够钱把婚退掉。眼下只有逃走这一条路了,不然,这一关指定是过不去。我要是能逃出去,就一定能挣够钱,还上二脱产家的债。那时候,我们就自由了,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嫁给你了。不过,我没出过远门,城里也没有可投靠的亲戚朋友,你想想法子吧。惠民哥,这件事你可要抓紧啊,在你归队前必须有个着落。不然,他们非得把我逼死不可。”
惠民说:“我同意你出去躲一躲,找一个地方打工挣钱。一来可以积攒一些退婚的钱,二来可以躲开他们的算计。
“眼下,把你从火坑里拉出来是当务之急。我明天就给我的老首长宋总打电话,联系你打工的事情。
“这个宋总叫宋文南,是咱们的同乡,我入伍时,就是他接的兵。原来在我们部队当参谋长,转业后在市黄金公司当老总。他对我非常好。他早就说过,等我退伍时,可以去他那工作。给你找工作的事,他一定会帮忙的。有了消息,我就安排你走。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往远了想,还得从改变咱们小山沟的面貌上找出路。原来我曾想在部队转一个志愿兵。现在看起来,这条路不能继续走下去了。我已经下了决心,等到了年底就复员。复员以后,我就扑下身子在咱这穷山沟里拼了。
“茉莉,你细想过没有,是谁为咱们套上了枷锁,是什么让咱们活得这么憋气,是咱的老爹老娘吗?不是,天下哪有不疼儿女的爹娘啊,他们也想让儿女活得好一些。可是他们做不到啊。生活逼着他们,贫困压着他们,他们不得不屈服。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命运?我认为就是两个字。一个字是“穷”,另一个字是“愚”。为什么穷,是咱们这里的环境吗?我认为不是。环境不好是现实,如果环境好,我们固然可以过得比现在好一些。可是,外地也有一些环境不如咱们的地方,为什么人家过得比咱们好呐?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愚”。咱们这个地方,人的思想观念落后,因循守旧,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不铲除“愚昧”,就拔不掉穷根。
“我是下了狠心了,复员以后,就在咱这穷山沟里煞下身子,治穷治愚,拼搏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不改变咱们穷山沟的面貌,不铲除愚昧,不拔掉穷根,不罢休。我有这个信心。复员回来之后,我要到大队的金矿去挖金子。这几年,我在黄金部队,学会了找金矿、挖金子、炼金子的全套技术。我要搬倒二甲山,把山里所有的金子都抖搂出来。挣到钱后,分给乡亲们每人一份。要把买卖婚姻、封建迷信、赌博吸毒、出勤不出力、七咬八争这些落后的东西清理一下,引导和帮助乡亲们走勤劳致富、共同致富、和谐致富、文明致富的道路。只有铲除落后和愚昧,我们才能挣断枷锁,真正得到解放。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眼下只能火烧眉毛顾眼前了,把你送走是当务之急。”
茉莉始终听着惠民说话,不住地点头。惠民的话落音后,茉莉接着说:“惠民哥,你说的真好。我也经常想这些事,就是想不出这些道理来。你的想法,我赞成。我先出去打工,躲过眼下这一劫。等还清二脱产家的债以后,我就回来给你做帮手,和你一起治穷治愚。”
茉莉和惠民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头道沟村头了。无巧不成书。天下就是有很多巧事。夜色之中,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骑驴的,一个赶脚的,从一个沟塘子里钻了出来,正好和茉莉惠民走了个对面。
谁啊?原来是一枝花和易八卦两个货。
走得很近了,互相之间才看清对方的脸面。
“这不是惠民吗,回来探家来啦?”易八卦先搭上了话。
“是啊。天都黑了,您二位去哪啊?”惠民问。
“可别说了,就是个操心的命啊,没有闲着的时候。今个晚饭后,四道沟来人送信,说是他们村老了人了,请我们去料理料理。老邻旧居的,有了危难着窄,求到跟前了,哪能不管啊!别说是天黑了,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去啊,谁让咱面矮呢?”易八卦回答。
“茉莉,还是你的消息灵通啊。你这是专程去接你的救命大恩人去了?”一枝花的话里透着几分阴阳怪气。
“是啊。惠民回家,你们可能不知道,你说我能不知道吗?我和惠民哥是啥关系,您还不清楚吗?我既然知道惠民哥回家,你说我能不去接吗?”茉莉的话音也带着一些刺,尤其是把“惠民哥”三个字叫的特别亲。
“接是应该去接,不过,这黑灯瞎火的,看不清道,一脚深一脚浅的,可别走到沟里去啊!”一枝花瞥着嘴说出来的话,弦外有音。
“谢谢您的关心。请您放心,我大瞪俩眼,咋也不会往沟里掉。我倒要嘱咐你老一句话,夜路不平,可千万加点小心,别从驴背上掉下来。”恐怕一枝花听不清楚,茉莉的话音比平时高了八度。
双方擦肩而过,背道而驰。
易八卦对一枝花说:“我看钱茉莉和郑惠民勾搭得挺紧啊。这时候惠民回来,真不是时候。有这小子一掺和,我看柱子的事,怕是不那么顺利啊。”
“我看不光柱子的事不顺利,就是玉叶的婚事也恐怕要出杈啊。”一枝花说。
“你得和脱产二哥说说,抓紧张罗那件事,尽快把茉莉接过来,可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是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