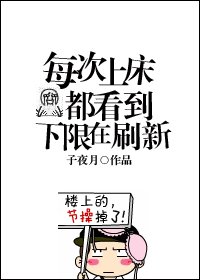魔鬼有张床-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
德五爷打了一个哈哈,“好,好,好。义气,义气。想当年,爷也讲过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的就是给自己长个脸,给江湖落个名声。看在咱们乡邻的份上,赁辆车给你,八九成新的,别人一天五毛,你给四毛得了。天上掉元宝,记住爷的好就是了。”
表叔舅连忙道了谢。
德五爷又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既然入了车行,我就给你说说车行的规矩:[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第一条——旧不挨新。
一般的车行,都有三种人,老,壮,少。因为租份儿少,年纪大的愿意拉最旧最破的车,去揽最重最脏最廉的生意——瓜市果市菜市杀场里拉货物;因为他们有绵力,又不需要快走,也只有他们这样的年纪的人干得下来、且愿意干。不干,自然没有饭吃,只有等死。年壮的呢,自然愿意拉最新最漂亮的车,多招生意。他们甩的是腿脚上的功夫,挣的是力气钱。这些人一般拉包月,住宅门儿。年少的,便只能拉六七成新的车,因为他们一没辈份,二没资格,而且力还没有长够,不敢快跑,长跑,所以只能拉拉散座儿。
第二条——强不欺弱。
两个车夫,狭路上相逢了,轻的只能让着重的;如果不小心,两个车夫撞上了,不能抡拳头,瞪珠子,得找个说理的地儿;车口上候生意,须等坐车人自个儿选车,然后讨价还价,决不能上前抄生意。
第三条——白不混黑。
拉白天的,天黑应收车,不能混夜里的生意;拉夜里的呢,自然也不能混白天的生意,天亮回家睡觉去。
第四条——东不过西。
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各门做个门的生意,不能窜了门道。东门到南门的生意,只须拉到南门口儿,叫声‘哥儿们,接生意了,某某地儿的。’摊了钱,自然有人送到点儿。
越规做生意,那就叫不懂行,轻者挨骂,重者挨打;轻的是给你一个警告,叫你胡子白了不能忘;重的是给你一个教训,叫你牙齿缺了还记着。”
……
表叔舅一边听,一边点头,努力地用心地记住德五爷的话,直到最后,德五爷说:“说到底,拉车虽是苦差事,但行行仍然有等级,有高低;这里和海上和京城里相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那里最上等的是洋车夫——白褂白裤,汗毛巾,青布鞋,不着号服,都没人跟他们抢生意。因为他们懂外国话,尽管他们不会说,但他们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就凭这,也足可以维持一个上等车夫的面子和尊严了。”
到现在,我都还在惊奇,在那时我的心里,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多,那么详,那么深?也许,是因为那时的冷,冷到了骨子里;那时的饿,饿到了灵魂里;那时的低下与卑贱,常泡在血泪里;更也许是表叔舅为了我们一家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所以到了今天,那些场景,那些话,仍是那么的刻骨铭心,仿佛就象是昨天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临走时,德五爷叫表叔舅看了车,说:“瞧仔细了,软弓子,大雨布,双风灯,大喇叭,样样不差离。小心着点儿,别出了茬子。”
表叔舅拍拍胸,说:“五爷放心,车能给我饭吃,就是我的爹,我的娘,”
回来后,表叔舅翻了历书,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放了鞭炮,出了车,打算图个好利市。
正文 手记8 生死两茫
仗真的打起来了,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许多的富人、贵人、官人,像惊弓之鸟一样,纷纷从大城市逃到了小城市或者乡下。这一来,可苦了他们的正房偏房,公子小姐,金银细软,都需要人拉,都需要人扛。
几乎是一夜之间,车夫的生意似乎一下子好了起来。战争竟然红了车夫的生意,这已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而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真理。车夫似乎也沾了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的光,终于多捞了几个乱世的臭铜。
有了这样的运气,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有了一些好转。难道是老天爷开了眼,菩萨亮了心?我的心里,似乎生出了一棵嫩芽,虽然弱小,却充满希望——明天会好起来。饥饿与寒冷,终将过去。
还没进入深冬,下了一场雪——多年未见的一场雪。这雪虽然小,纷纷扬扬,一落地便化成了水,但在人门的眼里,都梦想着一个好年景的到来。那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多少有了些苦难的笑声。
心里有了希望,手脚便显得灵便。一有机会,我便偷偷跑到巷子口去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车夫,怎么样把窝窝头和稀糊糊变成汗水,再用一滴一滴的汗水换来一只一只的小钱。
去巷口的次数多了,时间一长,我便发现,虽然同是最受苦、最受累、最受气的车夫,却也分成几种人。
一种是象表叔舅那样的,无非是失了业的工匠,折光了本的小贩,再不能下煤坑的黑子,超过了年限的街巡……平日里,他们不说话,沉默得象块石头,一个心思把力气放在手脚上,如一只只陀螺,南北西东,人家手一指,嘴一张,说到哪儿,就只能到哪儿,半点由不得自己。有时候,多走了一段路,仍然不能多得几个子儿;遇到无赖的主儿和抠门的妇人,也许还少得几个子儿,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说不利索,讲不出理儿,急了,也不敢挥起拳头——他们没那个胆儿,所以也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赶紧去找别的生意,想办法找回一些亏欠。
一种是油子车夫。这种人,多是些好吃懒做的败家子。早些年,守着祖上的基业,坐吃山空,眼看家道中落,仍是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妄想着空手套白狼;干着指头蘸把盐。结果是可想而知,渐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他们不甘心,象秋后的蚂蚱一样,还想蹦几下,跳几下,伸手去水中捞月亮。到了最后,家破了,人亡了,心才冷了,血才凉了,不得不操起这车把儿。
操起了这车把儿,他们还是不安分,变着法儿取巧,想着道儿摆俏。成天里,他们耳朵上总夹着吸了一半的烟屁股,摇头晃脑,吹着口哨,一副吊儿啷噹的样子。他们拉车,低着胸,到抬腿,跑一步,弯一下腰,点一下头,双腿跑得象扇扇子。他们拉车,说到哪儿,就只到哪儿,绝不肯多走半步路。要多走路?行,添钱来!只有钱能支动手脚,管你老弱病残,天皇老子,绝不能吃半点亏。
一种是霸王车夫。这种人多是充当杂皮、阿飞、喽啰到最后混不下去才该行拉车的。向上,他们成不了蛇,成不了龙;向下,他们不愿意做鱼,不愿意做虾。他们幻想着在这两者之间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然而,上面压着,下面拱着,哪里有他们的道场?最终,他们还是做了驴,卸了磨,便没有用了。
虽然走上了这条不甘心的路子,这种人,吃喝嫖赌抽,都是样样俱全;坑蒙拐拿骗,更是样样精通。他们拉车,只有在这些都行不通的时候,才走上那些从前是他们横行霸道的街头。
这种人拉车,抬头,挺胸,走的八字步,象扭秧歌,满嘴哼着下流曲儿,一条街不够一个人走。大街小巷,想怎么钻就怎么钻,想怎么窜就怎么窜,不怕巡警,不让汽车,心情好,拉到地儿;心情不好,半路便甩了人。照样一分不少拿钱。要打架,那可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三天不打还手痒痒呢。进了局子,还可省了三五天的饭钱;这进局子的次数多了,反而红了他们的字号。坐车的遇到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角色儿,只好自认倒霉,给钱走人,心里骂娘,以后把这种灾星和瘟神的样子刻在心骨里,再不去坐他们的车。
表叔舅的事就是出在霸王车夫身上的。快到年关了,人人都在争着抢生意。平日里,那些最忙和最闲的时间里,表叔舅总是时时记着德五爷所说的规矩,有时虽然油子车夫和霸王车夫前来抄生意,表叔舅忍一忍,退一退,也就过去了。时间一长,他们把表叔舅当成了好捏的柿子,总欺负他;表叔舅心中有些生气,多了些恼火,以至于最后忍无可忍,同一个抄生意的霸王车夫打了起来。
可怜的表叔舅,哪里是霸王车夫的对手,三拳两脚,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掉了几颗牙齿。车口儿的车夫们,躲都来不及,又哪里敢去劝,自讨苦吃;那来来回回巡视的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象没看见一样,生怕引火烧身,招鬼上了门。
表叔舅挨了打,犯了牛劲儿,非要找霸王车夫去德五爷那儿评理。在他心里,德五爷就是这儿的天,这儿的地,这儿的公理!
霸王车夫怒了,将表叔舅一脚踢了出去,滚到街心,被一辆跑过来的黄包车刹车不住,整个儿碾了过去。拉车人绊倒了,摔坏了车,摔出了坐车人;这下子,可惨了,也热闹了——那车夫要表叔舅赔车,表叔舅躺在地上直哼哼;那个坐车人更是不依,抓着拉车人的衣服要个说法儿。那车夫许是认得霸王车夫,不敢去找他说理,只一个劲儿东张西望,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
人群渐渐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好象在看一场精彩的猴戏。那个拉车人上前碰碰表叔舅,表叔舅没动,不知死活。那个霸王车夫似乎看出了名堂——知道要出大乱子,嘴里一个劲儿骂着,心里却有几分虚了,趁个空档儿,脚底抹油,连车也没要,不见了影子。
悲惨的表叔舅,是被几个好心的车夫给抬回来的;躺在床上,吸进去的气多,吐出来的气少,连哼哼声也听不到了。
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当头下,我的妈妈,几乎吓傻了,呆了好久,才返过魂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泪儿象断了线的珠子,噼哩啪啦地落到盆里。
看着妈妈哭,姐姐哭,我的泪儿又掉下来了。
哭够了,妈妈呆呆地坐在凳子上,忘记了手上的活儿。我知道,妈妈又要遭难了,这接二连三的变故,击碎了她的心,也磨灭了她的思想,什么主意、办法,都成了一根根套上脖子的绳索。
不久,德五爷来了,看了看表叔舅,出来骂道:“狗日的羊羔子,翻了天了?这还了得,简直没有王法了。他妈的,在这个盘儿上,敢不把五爷放在眼里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放心,五爷给你们作主,为你们讨回公道。”说完,急忙忙、气匆匆地走了。
望着床上躺着的表叔舅,我的心,象是经受了一场风雨,心中的那一棵嫩芽,一下子被打折了。希望就象那皂角儿的泡沫,升起得快,消失得也快,不用风吹,眨眼便不见了影子。
下午,德五爷来了,丢下了几块钱,说是那霸王车夫赔的;先用着,不够的话,再找他作主。德五爷不愧是德五爷,谁也不敢在他头上找刺儿。他说:“好个王八蛋,见了五爷,象条秋丝瓜,磕头作揖,乖乖认罚,还算识相,不然,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望着德五爷离去,我明白了:原来,软的怕着硬的;硬的怕着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着不要命的;不要命的还怕着管你命的。而且,同是最下等的车夫,仍然是强的欺负弱的;刁的欺负良的。为了生存,人还得象动物那样你争我夺,哪里有什么正义和公理。
人,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没有了命,一切都是扯蛋,一切都是狗屁!
大夫来了,又走了;表叔舅的药吃了又换了。然而,好多天过去了,表叔就仍然只能躺在床上,时不时地还吐出几口血水。不久,就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而且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德五爷没有再来过。表叔舅的病就这样有钱治着,无钱拖着。妈妈终日里,不是以泪洗面,就是愁眉苦脸;船儿出去,船儿回来,换来的,不过是一些草药和垃圾似的烂菜。
时光,不会因为我们的凄凉而过得很慢,也不会因为我们的饥寒而走得更快,大年终于来了。
街上,依然有春联儿,有红灯笼,依然有笑声,有炮仗声,在生与死的空档里,还是有几分动物似的热闹与欢腾。我们有什么呢?有的,不过是一碗可以照见影子的稀糊和破成莲蓬儿似的长夹袄,解决不了我们肚中的饥和身上的寒。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还没大亮,我和姐姐被妈妈一阵阵长哭声惊醒了过来。原来,表叔舅,我们的恩人,可怜的表叔舅,悲惨的表叔舅,抛下我们母女仨人,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来到表叔舅床前,只见他大张着嘴,口边有许多血渍;一双眼睛定定地睁着——不甘心、冤、怒!双手弯着,双腿曲着,好象一只被吸干了油水的大虾。一条破棉被上,腥,臭,分不清哪里是棉花,哪里是布,上面那大滩小滩的血迹,早已干成硬壳了。
妈妈靠在表叔舅床前,拉过我和姐姐的手,跪下,哭道:“他叔舅啊,是我们害了你呀!……老天爷呀,你真的是瞎了眼哪!……这是什么世道,全是恶魔的天下!……”
我和姐姐哭成一团。我们的表叔舅离我们而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好象半夜的流星一样,只在半空

![[周平] 故事床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