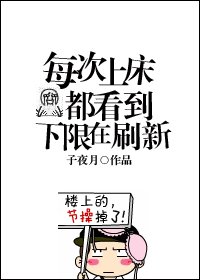魔鬼有张床-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世事真是难料,人生更是莫测,想不到儿时的伙伴,长大了却是阴差阳错,张冠李戴,时代的洪流,淘尽了多少人的命运。
看着小兰儿哭哭笑笑的样子,我没有安慰她,由她哭去,哭够了,心里或许会好过些。
不能久待,我得走了,看到小兰儿今天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未来。
临走,小兰儿送我出来,哭着向我招手道:“好姐姐,慢些走,走出巷子口,就忘了这个妹妹吧,我们不是一路的人。”
这个傻女人,她怎么知道,我和他一样,都是被人践踏的牲口!
正文 手记36 呼风唤雨
德先生走了,法先生来了。
入庄子,我心里再哭;入堂子,我心里在笑;入书馆,我心里在醉。我一步步走来,一步步高升,像爬蔓的牵牛。到了这里,我成了初上市的稀物,再也不愁没有生意。
还是一个有月色的夜晚。
整个园子,水、草、花、山、树、鸟、亭、桥、阁,一切都还是那样的美丽与迷人,悠悠而深长,淡淡而悠远。一首清曲,一杯清酒,就可以消磨完人一夜的时光。
来人是个带兵的头儿,先生说是个司令官。虎眼,熊嘴,弥勒肚,大象腿,铁塔儿一般。
秋荷领了法先生进来,法先生将手一挥,侍卫捧上了两个盒子,交于秋荷收了。
先生的主儿,先生自然知道,他只对我交代了一句话:这是一只猴,他要上树,给他根竿子;他要上房,给他架梯子。明人不用指点,响鼓不用重锤,见人一万,识人一千,不用先生交待,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法先生朝屋里扫了一下,将身上风衣一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腿朝几上一放,冲我说:“小百合,给爷们来支曲儿吧。”
法先生一挥手,两个侍卫,退了出去,虚掩了房门。
小时候,我爸爸也是司令官,什么样的兵儿我没有见过?风风雨雨走过来,我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失去了姐姐,世态与人心,早已经成了过眼烟云。伺候这样的主儿,还是那句老话,杀鸡焉用宰牛刀?我只要万分之一的心思,就游刃有余了。
听了先生的话,我走过去,打开留声机,为他放起了我的一支名为《盼君早回头》的曲儿。
红纱巾,轻轻挥在手,妹妹送哥泪花流。柳絮双双飞,蝴蝶双双求,盼了太阳盼月亮,如今正是春来到,哥在妹妹眼里头。
绿荷包,轻轻放胸口,妹妹留哥泪花流。白云双双飞,比目双双游,盼了太阳盼月亮,转眼又是夏来到,哥在妹妹心里头。
平安符,殷殷你带走,妹妹念哥泪花流。落叶双双飞,大雁双双愁,盼了太阳盼月亮,转眼又是秋来道,哥在妹妹梦里头。
鱼传书,殷殷藏枕袖,妹妹恨歌泪花流。大雪双双飞,鸳鸯双双守,盼了太阳盼月亮,转眼又是冬来到,哥在妹妹魂里头。
法先生一听完,一把搂我过去,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腿上捏了一把,大声笑道:“爷们是大老粗,一变大了是扁担,看见草绳就当蛇。就爱听这样的曲儿,哥儿妹儿的叫,听着才叫心里舒服。那象海堂阁的海棠,太冷,象冰块;牡丹园的牡丹,太热,象黏糕。”
我连忙说:“爷喜欢什么,百合就给爷什么。只要爷看着高兴,听着喜欢。”
法先生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摸着我的脸颊,笑道:“爷喜欢划拳猜谜儿。”
我说:“爷,先划拳吧,百合输了,给爷一个嘴巴;爷输了,罚一杯酒,如何?”
法先生手舞足蹈,马上与我七个三八个四地划了起来。这个痞子,不愧是行伍出身,果然厉害,十之八九都是他占上风。我在他脸上左一口右一口地亲着,一会儿,他就成了一个红脸的关公。
乘着他高兴,我说:“爷,您说海棠冷,牡丹热,那百荷呢?”
法先生拿手指在我鼻子上一刮,笑道:“你呀,不冷,不热,就象怀里的小手炉。”
我笑道:“那爷是喜欢上百合了?”法先生笑道:“当然啦,我的小傻瓜。”
兵儿的兴趣,如出了堂的子弹,来得快,去得快,玩了一会儿,他便改了辙,要我给他出谜儿。
我随口就来,笑道:
一个东西八只脚,
两个大钳一个壳。
眼睛长得像绿豆,
不住岸上住在河。
法先生张口接道:“哈哈,那不是螃蟹嘛!”我笑道:“爷不愧是带兵打仗的,见的多,识得广,一猜就中了。”
法先生把头一摇,在我嘴上咬了一口,有些飘然起来,对我说:“想想爷,五岁死爹,六岁死娘,七岁成了人家的放牛郎,十二岁就成了壮丁里的兵蛋子,风里来,雨里去,上刀山,下火海,白骨成山,血流成河,踩着别人的尸体,一步一步爬上来,才混得如今的人模狗样。想想爷,带兵打仗大半生,先受东北虎那王八蛋的气,接着受川耗子那龟儿子的气,后来又受土皇帝那狗娘养的气,到了最后,老子干脆不替他们卖命了,投了委员长,才混得了现在的一官半职。”
“这个乱世,就如一个大杀场,装孙子,充大爷,各有各的招,还有那个张宗昌,球样不懂,放屁当炮,还猴子戴帽,冒充斯文。你听他做了一首诗:‘天上突然一火链,疑是雷公要抽烟。不是雷公要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这狗屁不通的诗,竟被人传来传去,放在案头,当成宝贝,说他深得李杜之风,却被老子给骂了个狗血淋头,瓜皮垫脚。他算什么东西?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老子也作了一首诗回敬他:‘好个张宗昌,狗屁当文章。如果本司令,至少说电光。’”
法先生一边说,一边笑,等到他说完,我也笑痛了肚子,笑出了眼泪。这个家伙,老鸦说猪黑,五十步笑一百步,原来都是一丘之貉,混蛋一双。
不过,他也说得不错。这些年来,那些军阀们,你吃我的地盘,我抢你的山头,你堵我的前门,我烧你的后院……闹得天下乌烟瘴气,四分五裂。更有的,拜把子,结干亲,认同生,搭本家,谁有势力便去投靠谁,只要吃到奶,就可叫声娘;只要讨到赏,便可喊声爹。这些披着狼皮的人,恨不得天高三尺,地薄三尺,院上一个小太阳,不照他人房。
笑归笑,我可不能过了头,笑掉了大牙吞肚里。我对法先生说:“爷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当然劳苦功高,日后封侯挂帅,定是坛里抓鳖,手到擒来。”
法先生一拍大腿,两眼放光,一脸豪气,起来搂着我立在窗前,对着外面的星光明月,说:“那个什么《三国》说得好,自古天下,久合必分,分久必合。乱世才能出英雄。如今天下,群雄四起,正是我们这些武夫莽汉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说:“英雄爷,你也出一个谜吧。”法先生清清嗓子,拉我在椅子上坐下,笑道:“小百合,给爷听好了。”
尾巴短,
脑袋长,
背上一张八卦床,
龙王封它做丞相。
我听了,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却不急于回答他。故意低着头,装出一副推敲的样子。
不待我回答,法先生双掌一拍,哈哈大笑道:“不就是乌龟王八嘛。”我也抚掌笑道:“原来爷在捉弄百合,玩些乡下人猜的小玩意儿。”
法先生握住我的手,得意地说:“蛇肉上不了灶台,狗肉上不了天台,爷就是乡巴佬,弄不来那些咿咿呀呀的玩意儿,”
我笑道:“别人骑马我骑牛,乐得逍遥又自由。爷是异人,当然不与常人一般。”
法先生两眼放光,拥我坐下。我端过茶,喂了他一口,说:“爷说了这么久,吃口茶润润嗓子吧。”法先生接过杯子,放在几上,一把搂住我说:“爷不吃茶,要吃你。跟爷做乌龟王八去啰。”说完,在我脸上狠狠捏了一把,抱起我的身子,丢到床上,三两下扒光了我的衣服,把我压在他的身下,象带兵打仗一样的冲啊杀啊的叫过不停。
一翻云雨之后,这个主儿,还没有尽兴,抱着我说:“今儿爷高兴,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好玩玩。”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什么地方,牛随犁走,马随鞭走,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跟着他去。穿戴好,我们携手出了书馆,上了车,一声呼啸,绝尘而去。
等到车子停下来,来到的,竟然是一个赌坊。
整个坊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吵声、叫声、吆喝声、叹气声、拍掌声、跺脚声混在一起,牌九、色子、押宝、……赢了的、输了的,每个人都眼瞪象铜铃,耳竖如兔子,背弯似米虾……这些人,手长脚快,都想空手套白狼,谁知道却是在倒两碗水,到了最后,碗里空空如也,水流地下,不知所踪。
选了一张桌子坐下,我们去玩二十一点。法先生一挥手,侍卫去换了筹码,立在身后;法先生拥着我,坐定之后,不慌不忙的等着发牌。
玩了一会儿,我们输得多,赢的少,很快就输了几百块钱。我看看法先生,有些难为情;他笑笑,捏着我的脸蛋说:“小傻瓜,不过是玩玩,只要高兴,输几个钱算什么?”
接着玩下去,我们面前的筹码蚂蚁搬家一样的不见了。法先生满不在乎,叫过侍卫,又去换了些筹码来。
正玩着,忽然场中一片骚乱。有人叫道:“这人出老千。”只见场中一押宝桌上,几个赌徒捉住一人,摁在桌上,红着眼,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将此人生吞活剥了。
早有护场的进去禀报,幺哥出来了,大眼一横,朝四周看了看,一挥手,说道:“先放开他。在这个地盘上,谁也别想找一根刺儿。”
那几个赌徒只好放了那人,坐在椅子上,气鼓如蛙,等待着小管事的裁决。
那老千倒也有几分胆量,取过一把椅子坐下,耸耸肩,跷起了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根本不把幺哥放在眼里。
幺哥看看他,一声冷笑,高声道:“有请虎爷。”护场的一一传了进去。
稍顷,方出来一人,头秃脸狭,肩削背突,肚大腰小,一身蓝绸,脚登虎头靴,双爪似猴,好像地狱里出来勾魂的无常,索命的判官。
幺哥搬来椅子,待虎爷坐下。虎爷皮笑肉不笑,冲那老千道:“朋友,那条线上的?”
那老千一拱手,算是给了虎爷面子,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逢山开路,遇水塔桥。你说我是那条线上的?”
虎爷一扯嘴角,笑道:“原来是把老枪。失敬失敬了。不过……”他眼珠一拧,话头一转,不怒自威,出语如刀:“朋友,这个点上,只认老面,不认老枪。”
千手不想示弱,道:“大家跑马江湖,饥求一碗饭,渴求一瓢水。还望阁下高抬贵手,放在下一马。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相连。他日有缘,自当奉还。”
虎爷摇摇头,道:“帮有帮规,行有行规。今日放你一马,明日放他一马,你叫我以后怎么开场子?自己打自己耳光,我虎爷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
千手红了脸,一咬牙,道:“阁下真不给面子?”虎爷笑笑:“朋友,对不住了,别说你,前儿来了个神鞭,犯了规矩,惹了众怒,也只能给办了,这样才能服人心,不然,谁还顾及江湖规矩?”
千手见此,叹口气,道:“虎落平阳,白某今日认栽了。既然如此,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白某皱皱眉头,就算不得英雄好汉,白来世上一遭。”
虎爷大笑道:“好好好,敢做敢为,敢为敢当,不是孬种。冲你这句话,本来要削你五指,虎爷做主了,断你一根指节,算是在下给江湖朋友的一个交待。”
千手将头一昂,一撸袖,将手放在桌子上。
虎爷一努嘴,幺哥叫过执事,喷了一口酒在老千手指上,叫声:“得罪了。”一刀下去,干脆利落,断去了千手一根指节,用布包了,扎好。
千手倒也血性,没叫一声,脸色由红变成了灰白,道声:“谢了。”捂住手离开了赌坊。
虎爷冲他背影一拱手道:“得罪了,朋友走好。他日相逢,虎爷自当以酒谢罪。”
了了这桩事,大家又继续玩着,司空见惯了,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影响大家的兴致。个个都象红了眼的兔子,死死的盯着桌子上的押码。
玩下去,不久,我们有输光了桌上的筹码。我对法先生说:“爷,不玩了,回去吧。”
法先生笑道:“小傻瓜,你怕爷输了光屁股走人是不是?不用担心,天塌下来由爷顶着,出来了,就玩他妈个稀里哗啦。”说完,又叫侍卫去换了筹码来。
到了最后,我们又输了个精光,前前后后一共输了一千多块。法先生的脸上终于挂不住了,对那庄家说:“朋友,赢一把输三把,你当爷是长的猪脑袋啊。你就不能让爷连赢几把,就是输了,也输得心甘情愿、大快人心。”
那庄家冷笑一声,扬扬手中的牌,横声道:“大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输谁赢,得靠个人的运气。”
法先生笑道:“这么说来,你们开场子的,也是靠自己的本事,从不玩弄些什么手段?”
庄家有些恼了,恨声道:“猫是猫命,虎是虎命。输了就是输了,别怨天尤人,倒打一耙;哼哼,更别想找碴儿,死胡同里牛打

![[周平] 故事床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