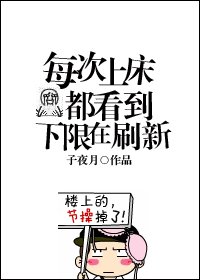魔鬼有张床-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人,如果两头都占不了便宜,走时会大呼冤枉,说庄子里照顾不周,吃干净桌上所有的残汤剩水,因为给了钱,连要命的酒儿也不能省下,红了眼,宁愿喝了伤心,也不愿丢掉痛心,东倒西歪的出庄去,一路吆喝不停。
当然,对于一般的客人,自然用不上什么手段,玩不上什么心思。一个买,一个卖,只要价值公道,完了事,一拍两散,互不亏欠,各走各的路,谁也不会有心记着谁。
一日复一日,一月复一月,我咬着牙,数着分秒,希望把一切都练得滚瓜烂熟,然后可以把一切都应付得游刃有余,这样才不枉到了窑子走一遭,做了一回活死人。
时间,可不管任何人,春兰夏荷,秋菊冬梅,照样红的红,绿的绿,那风,那雨,那雪,该来的时候依然要来,那云,那星,那月,还在重复着它们的千古光华,这富人在盼、穷人在躲的年关,还是顺着它的脚步走来了。
庄子里,生意照做,一切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时不时还添着新面孔,为老鸨子招兵买马,犹如源头又添了活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这人来人往的柳庄子,改头换面象唱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就有万年说不完、唱不尽的故事。
只有到了迎灶那一天,庄子里换上了新的大红灯笼,举行一年例行的祈福会,庄子里才显出几分喜气来。
一大早,庄子里所有的人都得候在中堂,由老鸨子叫着一一轮流上香,祭奠红楼青窑的保佑者——白眉女神,以求一年的运道旺盛,财源滚滚。个个婊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装着一副虔诚的样子,给救不了自己的菩萨磕头作揖。
祭祀完毕后,由老鸨子领着众人来到前堂跨火炉,以求冲去一年的晦气,更望来年火气大旺,烧红一片天地。一个瓦炉,装的是碳火,上面撒了香粉,放在屋中央,婊子们依着先后,提着裙摆,快快地越了过去,每个人的嘴里,都念着避邪的六字真言。
跨过火炉,众人还得去后堂骑木马。每一个婊子都知道,做皮肉生意一辈子,要遭千人压、万人骑,好象庙宇上的木鼓一样,只要奇 ^书*~网!&*收*集。整@理上了供,人人都可以敲几下。为了下辈子不再做牛马,不再做猪狗,好好做一回人,去主宰别人的命运,骑上了这木马,就当自己翻了身,做了主,在心灵上给自己一个空幻的梦想。
做过了这一切,吃过饭,大家却不能闲下来,得照例做生意。在这里,是没有假日,也没有节日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得做,牛死下了枷,马死脱了鞍,才算结束了。
到了中午,饭菜虽然比平常丰盛一些,却没有一个人吃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年到了头,每个人的眼里,看不到希望的憧憬;每个人的嘴里,听不到希望的呼唤。
到了晚上,庄子里搭了台,请来了戏班子朝贺,嫖客婊子一起热闹到深夜,这样一来,客人助了兴,婊子添了喜,庄子讨了彩,落了个皆大欢喜。
散了场,回到小屋子,没有点灯,坐在床边,我想到了妈妈,她还有希望吗?她的腿虽然好了,却落下了残,走路一瘸一拐的,人看上去老了一大截,好象棕树皮。生意是做不成了,谁愿意把钱塞进解不了风情的婊子手里呢?她只能呆在家里,苦苦地等待着她的女儿去养活她,延续那薄如纸片、轻如鸿毛的生命。
我想到了妈妈,那些姐姐呢,她们想到了她们的亲人了吗?在自然中,羊跪乳,鸦反哺,这些低等的动物,都知道本能的亲情,这下等的庄子里,平日里,她们打着情,骂着俏,笑着滚滚红尘众生丑态相,闲下来的时候,在那内心的深处,是不是还有一角不染风尘的净土,为自己的亲人一生守候与祈祷?
我可怜她们,更可怜我自己!
可怜归可怜,歌还得继续唱着,琴还得继续弹着,舞还得继续跳着,笑还得继续卖着!
正文 手记24 妈妈四嫁
又是一年春来到,杨柳绿了,桃花红了,风吹梧桐,雨打芭蕉,自然间的山山水水,还是要多美有多美,一年不同一年,翻着花样地粉饰着人间飞絮似的空梦。
正是在这样美丽的时节,妈妈却要走了——不是嫁人,是跟了别人,一个老头子,去和他过下半辈子。
这就是妈妈所寻的依靠,他是一个烧饼店的店主,五十多岁,背有些驼,头发全白了,一脸麻子,胡子拉茬,一双手伸出来,仿佛一块老树皮,那张嘴里,只剩下稀稀疏疏几颗烂牙,张口说话,牙不关风,吐字不清,好象敲闷鼓;断了接、接了断,脚上穿的,不分春夏秋冬,都是一双麻草鞋。
这个老头儿,他对别人说了:他不怕扫把星,更不怕天狗星,各人是各人的命,一个克夫的女人,不可能有猫那么硬的命,每一次都把男人送上望乡台。他五十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能活几年?要能趁有几口活气的时候,找一个人来端汤递水,过几天有帮衬的日子,就算是被女人克死了,也值了,瞑目了。
听了他这些话,我的心里,比刀子割还难受,只有那些有钱的男人,才有资格老少配,我的妈妈,竟然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跟了他,可见命运对我们的捉弄是多么的残酷!
妈妈走上这条路,寻到这个归宿,肯定是她不情愿的,万般无奈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在她心目中,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女儿,永远是个需要人怜惜和眷顾的孩子,她是把自己活生生卖了来养大我和姐姐的。到了如今,她还在为我着想,恨不得把自己的骨头做了钮扣押出去,来把我拉出苦海。
明知道这是一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妄想,妈妈还是一头扎了进去,把自己推入一个虚幻的梦境,希望捞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可是我怎么也料不到,妈妈找了这么一个主儿,三闷棍打不出一个响屁来,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妈妈过去了,岂不是要做他的奴隶?看了那个老头儿,我不愿意,对妈妈说:“我能养活您。”
妈妈摇摇头,背着身子对着我说:“你……你能养活我一辈子吗?”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她在悄悄流泪。
妈妈的话是不错的,这几年,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还积下了一点儿钱,那不过是表面的风光,我们是拿一月当一天,拿一年当一月活着,这种饭是吃不长久的,就如那神坛上的泥像,各领风骚三五年,余下的,都是强者和后来者的交椅!
只要能留住妈妈,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对妈妈说:“只要能过就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妈妈说,既然她决定了,就不会再回头了,来来往往几十年,她什么都看过了,什么都听过了,什么都想过了,世道,原来就是那么回事,从生到死,来的时候,光溜溜一个身子,活着的时候,伸着手捞月亮,提着篮子打水,死的时候,空荡荡几块薄板,就是最终的所得!所以妈妈觉得,趁现在还有人要她,她得赶紧走,不然,再过几年,白发黑皮老骨头,想叫人要,也没人敢要了。
我明白妈妈的心,残酷的世态早以摧毁了她的一切,命运从天上掉到地上,又从地上掉到地下,一步一步,风刀霜剑,就是一块铁石,慢慢消磨,也早被蚀化了,成了粉了。
我们的生命之可悲,由此可见。乱世里,群魔狂舞,我们的活路,只有针尖那么小。
春天还没有完,妈妈就要走了。
离别的时候,那天早上,如过去一样,妈妈一直默默无言地收拾着东西,我在一旁默默无言地立着。我知道,我再也留不住妈妈,她这一走,我们就如同成了两个世界,什么办法,什么语言,都如那过往的云烟,飘散了。
天刚刚亮,那个老头儿就来了,一个人。一路上的温风,吹得他胡子上气了水珠儿。他知道我不喜欢她,更不愿意见他,车子停在院门外,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把手藏在袖子里,缩着脖子,踱着步子等着妈妈。
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也懒得理他。虽然,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本份人,老老实实地做着活儿,维持着自己的生路,但在我心里,不知怎么的,就是有一种无由的厌烦,莫名的嫌弃,让我看到他不顺眼,不顺心。
行李收拾好了,我和妈妈,还是没有说话。妈妈呢,连头也没梳,还是穿着原来的衣服,虽然不脏,但却是补丁叠着补丁,脚上只穿了一双步鞋,帮子裂了几处。她挽着那个灰布包袱儿,走出了屋子。
来到院子里,她的身子,在春天的轻寒里,微微地打着颤,走到院门口,我的好妈妈,她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了我一下,红了眼,身子哆嗦了一阵,想说话,可话到嘴边又给她咽回去了。她只能长长地叹口气,咬咬嘴唇,挪动步子走了。
看着妈妈走出去,我们都没有哭。世道如此,我们的心,早已如一把稻草,被烧了,变成了灰,成了烟了。
妈妈走在前面,那老头儿在后面跟着,一直到巷子口,立了一下,那个老头儿才叫上那辆黄包车,和妈妈一同坐上去,车夫吆喝一声,摇响了铃当,小巷入街,慢慢溶进了人流,消失了。
我呆立院门口,一直目送着妈妈。她没有回头,没有留下任何叮嘱,狠下心走了,离开了她那万般无奈的女儿。
对于别人,我不再叹谁,也不再怨谁;对于我自己,行动是语言的傀儡,心是身子的奴隶,身前身后,梦里梦外,真实就好象一个影子,分不清虚实与有无。
有时候,想想,这样也好,妈妈寻到了一个主儿,死了,至少还有人捡尸骨。我一年到头的不在家,妈妈突然去了,我是连一点儿消息也得不到的,更别指望给她送终了。对我而言,多多少少免去了我的几分后顾之忧,庄子里,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稳扎稳打地对付那帮乌龟王八蛋了。
我是卖笑的,卖肉的,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得给他们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快乐,才能满足,老鸨子才能高兴,才能赏识。我念过那充满血泪与罪恶的书,不再是直肠子,眼睛会绕几个圈儿,心思会转几个弯儿,我会想着法子,变着花样儿地讨好那些嫖客的欢心,让他们为我做宣传,我将来身价提高了,就可以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了。
再看看我的那些姐妹们,卖了十几二十年的笑与肉,仍然还守在这烟花似的庄子里,血快干了,肉快烂了,骨头快碎了……我明白,她们这一辈子,在这个活地狱,就熬到头了。
我是不甘心的,投了一回人生,做了一回婊子,命运如此,就得象那没过河的卒子,一直往前走,永远不回头,只要不被吃掉,就得一步一步地靠向那最大的主儿,待到过了河,前后去讨好,左右去卖乖,一旦有朝穿了九宫心,便可擒了老将帅。从此得到半壁江山!
每当我有了这样的念头时,我又觉得是多么的可笑。这个世道,真的怪的可以,人分九等,婊子还在九等之外,可婊子呢,还得再分几等,终于弄得青楼上下、红楼内外,个个婊子都想混上第一等,成为章柳魁花,从而日进一斗银,夜进一斗金。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样荒唐的想法竟然没有错。我的力气没有白费,心思没有白花,我连连讨得了嫖客们的赞美,博得了老鸨子的欢心。我的行动,比起其他姐妹来说,渐渐多了几分自由,没事时,可以满园子打转,想天上的神话,听地上的人话,说地下的鬼话。
我付出的代价,终于有了回报,客来客往,生意好得不得了。等我想起去看妈妈的时候,我已经攒下了一大笔钱。
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闲下来的时候,对着窗外,有月无月,有花无花,我的心,都在挂念着她。妈妈走了,是为我而走的,为钱而走的,根本不愿意去受那份苦,那份罪。钱是什么东西?说起来,钱还真不是什么东西,然而,一旦离开了这个东西,人,就将成为不是一个东西!
对于用来活命的钱——人的命根子,那个老头儿,我对他是没有一丝指望的,我的妈妈得我自己顾、自己管、自己疼,心尽了,今天死,明天死,不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是黑发人送白发人,全让鬼神去主宰吧。
好不容易,得老鸨子开恩,给了我半天的假,让我去看妈妈。这个天大的赐与,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庄子里的姐姐们,有的三年五年都不能回家去看一下亲人,祭一下祖坟。
胭脂、水粉、耳坠、手镯、帽子、手套、风衣、提包……要出这个庄子,我得好好收拾打扮自己,让别人认不出我,更让别人刮目相看。一路上,我可再也不想看到那些指手与划脚,扰了我的心境,误了我的功夫。
天还没有亮,我便去拜别老鸨子。小丫头传了话进去,老鸨子才慢吞吞地起来,叫我进去,坐在椅子上对我说:“傻女儿,看把你急的,吃过了吗?”
我说:“吃了,特地来告辞妈妈,好让您放心。”
老鸨子叫人上了茶,拉着我的手说:“好女儿,

![[周平] 故事床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