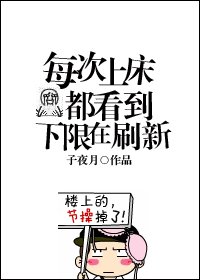魔鬼有张床-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旁边搭的一个小草棚,半道栅栏做成了一道小门。
屋的后边,有一棵大树。正是春天,它已开始发芽,嫩嫩的,油油的,象一只只小铜板,所以我们都叫它青钱儿。它长得好高,好大,好壮,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树的枝干开了裂,象八十岁老太婆的脸;一条条树根突出地面,好象露了半截身子的乌梢蛇,互相搭着、缠着、绕着。
屋子前面,有一条小河,象一条小青蟒似的,不知延伸到哪儿去。河里没有鱼虾,没有蚌蟹,没有蛙蟆……只有一些水草,相互纠缠在一起。水暗暗的,发着绿光,上面漂着许多垃圾,发出浓浓的臭味。偶尔可以看到一块两块突出水面的石头,黑黝黝象老乌龟的背。
小河上,有一座独木桥,到处都是虫蛀的小窟窿,生着些拇指大小的草菇儿。人走在上面,一摇一晃,好象荡秋千,叫人提心吊胆,生怕掉下去。
家的不远处,是条窄窄的小巷。很曲,很短,青石板上长青苔,旁边常常开着许多不知名的小花。许多时候,呆在家里,就可以听到巷子里的叫卖声……卖花的小姑娘,卖纸风车的小男孩,卖针线荷包的货郎,卖冰糖葫芦的老女人,卖梨花糕的老头儿……他们拖着长长而有气无力的声音,传得好远好远。
来到这个新家,这个又破又烂的新家,我曾问妈妈:“我们为什么要住这么破烂的房子,什么都没有。”妈妈说了,我们只是暂住,只要爸爸来接我们,我们就离开了,不再受这份苦了。
我不喜欢个地方,我好想我的老家。老家的房子又宽又大又亮,床又长又软又香;那些花儿草儿和鱼儿,常常会引来鸟儿蝴蝶和蜻蜓,好看极了,好玩极了;还有那些布娃娃、狗宝宝、猫咪咪;那些长命锁、项圈儿、手镯儿……都是我的朋友,姐姐的朋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床又窄又矮又旧,坐上去吱嘎吱嘎地响,象只饿了的小猴子。整个屋里,除了两口箱子之外,剩下的就只有空空的四道墙壁了。地上又湿又黑,透着些霉味儿和腥味儿。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我们住不了多久,这样想着,我便放了心,只盼着爸爸早点来接我们。
不久,我和姐姐便有了一帮子小朋友。
那是我们搬来的第三天。天刚大亮,因为处处不同,事事新鲜,我和姐姐都起个大早,坐在屋外玩抓石子。传来一阵歌声:
大红喜,大红花,大红灯笼跳青蛙。竹节疤,木疙瘩,棉是棉来纱是纱。都说哥是唐三娃,洞房变成猪二八。可恨媒婆子,害我女儿家,明年明年要当妈,葫芦上结个大东瓜。
大红轿,大红马,大红盖头藏乌鸦。白蝴蝶,黄蚂蚱,鱼是鱼来虾是虾。都说姐是白天鹅,过门变成癞蛤蟆。可恨媒婆子,害我男儿家,明年明年要当爸,米团蒸笼糊麦粑。
歌儿唱完,船也到了。是一只乌蓬船,象一条乌鱼似的。撑船的是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穿着一件灰布褂儿,赤着脚,整个身子透着黑亮。船儿靠了岸,那小子将篙一插,抵住船尾,然后纵身一跳,下了船,道声:“下来吧。”后面舱里便钻出了一个剃着锅铲头的小男孩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锅铲头男孩很矮、很瘦,象根烧火棍。衣服又脏又破,已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了;那羊角辫女孩模样儿生得好看些,却拖着两道又浓又长的鼻涕,一身衣服又长又大,显然是大人的衣服改小做的。他们和那个虎头娃一样,光着脚丫子,上面粘着湿漉漉的黄泥。
姐姐见有人来,忙跑回屋去,转眼却又伸出半个脑袋来,倚着门边朝这边望。我比姐姐胆子大,不怕他们,看着那个锅铲似的头和羊角似的辫,我反而笑了。
那虎头娃上来,问道:“打哪儿来的?”我说:“东边。”那虎头娃一匝手,又上前一步,说:“入我们伙儿,怎么样?”我说:“我得问妈妈。”
妈妈自然是同意的。她希望我和姐姐多几个伙伴,还拿出一些枣儿和花生来,分给他们吃。他们都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说先闻闻香儿。
我和姐姐上了船,告诉了他们名字,也知道他们一个叫二虎子,一个叫二竿子,一个叫小兰儿。
二虎子将篙一拔,在岸边轻轻一点,待船离了岸,又引了一个头,唱起那首歌谣。于是船在歌声中悠悠前行,两边水草象遇上了一条大乌蛇向两边唰唰窜开。一会儿,待到歌声一停,船已转入了另一条河中。
二虎子一边撑船,一边说:“白露,你们有歌吗?”姐姐听了,笑着点头;我却不怕,抢着回答:“我们会唱神仙谣。”小兰儿说:“可以教我们吗?”我说:“除非你们教我们唱刚才那首歌儿。”大家同意了。船在婉转歌声中缓缓前行。
不久,船又转了向,驶入一条更大的河中。就好象从瓶口到瓶底,越走越宽。船到这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蓝天很高,很远,彷佛一块通灵的碧玉,然而,里面好象什么也没有,如一面大大的空镜子。云在天边,很轻,很淡,象一块块飘动的白纱巾。阳光很柔和,很温暖,如同妈妈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我的身,我的心,也都是暖暖的。岸边的草,碧绿了,还一个劲儿地疯长,占据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地方。
这是阳春的三月。三月的水乡,正是烟草时节,又是烟花时节。远处,是一排连着一排的房子,房子之间到处是数不清的花红,花的香味从那红得含着烟的颜色里漫漫传来,软软的,甜甜的,就象水珠落到沙子上,倐地一下子钻进了心里;那几分草香,几分泥土香,几分水香,几分花香,便开始融合了,酝酿着,渐渐变成了发酵的香糕。
桥不再是我家门前的独木桥,变成了石拱桥——单拱,双拱,三拱,多拱……宽宽的,上面是青石板,两边有护拦,护拦上都錾着些扇形大小的图画,或松或竹,或梅或兰,或虫或鱼,既有几分古朴典雅,又有几分轻灵秀美。二虎子说,桥上青石板之间,全都是细卵石填着,长满了淡淡的绿苔,绿苔下面是红红透明的蚯蚓,是勾鱼最好的饵。
船渐渐多了起来,南来的,北往的,象梭子一样。那些船夫,他们早地出来,晚晚地回去,一张鱼网,就网住了他们大半生的岁月。
渔船上,这些戴着麦帽的渔夫已经开始捕鱼了。一排排打鱼郎,全身乌黑发亮,长长的嘴似一把大钳子那样坚硬;细细的脖子象水蛇一样灵活;一双铁勾一般的爪子紧紧抓在船舷上;一对圆眼睛低低地贴近水面,不断的左右巡视着。一盏渔灯,晃晃悠悠地悬在舱口。渔人一声呼哨,只见竹篙一抹,所有的打鱼郎便纷纷射下了水,扑腾着翅膀,一下子扎进了水中,水面上窜起了无数细小的水花。不久,一只两只打鱼郎钻出水面,跃上船头,奔向渔夫的竹篓。渔夫一弯腰,一把卡住打鱼郎的脖子,用力一挤,条条鱼儿便纷纷落入了篓中。渔夫也会赏它,从篓中捡起几只小鱼,轻轻一抛,打鱼郎将头一迎,小鱼已落入了它的口中。渔夫提过打鱼郎,用力一甩,打鱼郎又潜入了水中。有时,几只打鱼郎圈在一起,抬起一条大鱼,渔夫便奔过去,一把擒住大鱼的鳃,用力一拉,那条大鱼弹入了船舱,一蹦一跳地翻动着身子,吐着豆子大的泡儿。
再走一会儿,我们已离先前的那一排排房子不远了。二虎子在一处柳枝上折了一片柳叶,含在嘴里,吹起了哨儿。二竿子说:“那三个小王八蛋今天怎么了,还不来。”我不知道他们约的是谁,问小兰儿,小兰儿说:“这三个小子都是大户儿的儿子。”
二虎子急了,丢掉柳叶儿,把手指放在嘴里,一撅屁股,长吸了一口气,吹了一个响哨儿。这哨儿刚停,不知从哪儿应了一声。二虎子笑了:“土羔子,你们终于来了。”
不一会儿,只听一声吆喝,从不远处的水巷转角钻出来一只船。到了叉口,却见船尾一摆,船便转了向,向着我们这边行来。船上三个人,一个人撑篙,一个人摇橹,还有一个人双手叉腰,立在船头。
船不是乌蓬船,是一只红船。舱是双门的,挂着布帘儿,舱上有窗,窗上有绣像,不知是关公还是门神。
二虎子指着撑篙的胖子说:“那个光头儿是保长的儿子,名叫久荣;那个双下巴是甲长的儿子,名叫长贵;他们前面那个腰里别着假火枪的对对眼是保安队长的儿子,名叫永富。”
近得来,两船轻轻一碰,再往前几尺,便稳了身。三个小子,头上是青缎帽,身上是白纱袍,脚下是黑绸鞋,脖子上还戴着个明晃晃的圈儿。真是几个有钱的主儿。
那个叫永富的腰里别的是一只小木枪,乌不溜鳅,闪着油光。他歪着脸,左右打量了我和姐姐几眼,对二虎子说:“怎么,又添新帮儿了?”二虎子没吭声,嘻嘻一笑。
那个叫久荣的插稳了篙,对我姐姐说:“喂,哪里来的?”姐姐刚要回答,却被二竿子抢过了话:“东边来的。怎么着,想欺生是不是?“长贵嚷道:“谁欺生了?你们是不是想以多胜少。”二虎子笑着一指永富:“放心,不会欺你人少。敢比吗?”永富双手一叉,拍拍腰上的小木枪:“怕你是狗熊。”
接下来我才知道,这一穷一富两帮子,见面总是要比一番,看看谁的本事大。因为见面的机会少,穷小子要做活,富小子要读书,所以每次见面,总要分出个胜负,做为下次比赛的老底儿。
这一次,大家先玩的是占山为王。乌船上五个人,红船上三个人,需要一个人去红船,才能平等。因为我和姐姐是初到,所以二虎子叫小兰儿跟他们。小兰儿撅着嘴,老大不高兴,最后是长贵给了她一粒玻璃珠作为代价,她才不情愿地去了红船。
比赛占山为王,因为这里没有山,只好在远处一个地方插一根竹竿,上面扎一根布条儿,作为标记。两船同划,谁先到达取了布条儿,谁就称王,得受拜,奖品呢则是十粒杏仁儿。比赛的规则是不用篙,不用橹,得用手。
站在船头,二虎子大声说:“我是林冲。”二竿子说:“我是武松。”轮到我和姐姐,我们不知该说什么了。二虎子说:“你们是女娃儿,就免了吧。千万别当母夜叉。”
红船上,永富说:“我是宋江。”长贵说:“我是吴用。”久荣说:“我是花荣。”小兰儿不作声,还撅着嘴,一副老大不愿的样子。
大家报完了名号,一切准备好了,二虎子报了个一二三,两只船上的人都喝着号子,急急向前划行。起初,两船都还并头而行,可过不了多久,我们那只船便落了后。我和姐姐使劲的划,仍然赶不上去,急得二竿子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干叫唤。
两只船渐渐拉开了距离,永富时不时回过头来瞅我们,眼中露出了得意的神色。继续下去,我和姐姐都划出了汗,可前面的红船已越来越远,怎么也赶不上了。
到了最后,当我们的船到了终点之时,永富早已站在船头,挥动着布条儿,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大声叫道:“怎么样,林冲?怎么样,武松?还是宋江厉害吧!”长贵接口说:“还是吴用厉害吧?”久荣也说:“还是花荣厉害吧?”
二虎子别别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带头跪在了船头。二竿子气得咬牙,冲红船上三个小子直瞪眼,但也没办法,也跪了下来。我和姐姐看着,不由捂住嘴笑了起来,也跟着跪在了船头。二虎子大声道:“在下林冲,拜见四位大王。”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朝红船的人作揖磕头。
红船上三个小子直乐得手舞足蹈,可小兰儿好象做错了事似的,几分高兴之中又带着几分害怕。
拜完王之后,二虎子对永富说:“小子,还敢比吗?”长贵抢上口说:“比什么?”二虎子眨眨眼,朝岸边一指说:“谁输了去岸上摘豆角和麦穗。”
小兰儿嚷道:“我可不去!”久荣说:“胆小鬼,还不是他们输?”小兰儿嘟着嘴,不吱声了。
两只船便又返回了原地,重新比过。奇怪的是,这一次我们的船在一二三的口号之后,一下子便划在了红船的前面,直气得永富大骂起来,三个小子奋起直追,却怎么赶也赶不上我们的乌船,渐渐的落下了一大截。
到了终点,三个富家子象斗败了的公鸡,直冲二虎子瞪眼,不知他玩了什么诡计。二虎子笑了,说:“怎么样,宋江,认输了吧?快去做贼吧!”永富将胸一拍,说:“我老子是队长,我怕谁。去就去。”小兰儿死活不去,气得三个小子直跺脚,只好让她留在乌船上,三个人去了岸边。
待红船走远了,二竿子对二虎子一竖大拇指,说:“原来你又把他们蒙了。”二虎子说:“怎么样,咱们又可以打一回牙祭了。”原来我才知道,第一次二虎子是故意输的,让三个小子上了一回大当——打了一个平手却成了输家。
不一会儿,红船回来了。三个小子偷了一篓子豆角和半袋子麦穗。大家来到乌船上,

![[周平] 故事床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