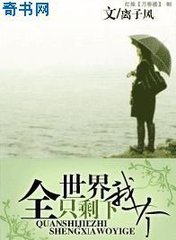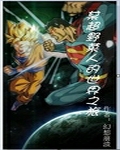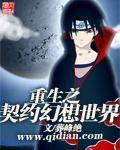天坑世界-第48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屠肟硖宓牧榛甑幕疃!�
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极大的满足了先民们的思亲之情,同时也给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内容。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3'同时,也表明了那时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迈进了一大步。当然,从单纯的思亲之情,到灵魂不死观念上的转变,有一个相当长的互容阶段。
人的灵魂不死,拓宽了先民们的想象空间。于是,从葬式、葬具、葬地的选择,以及随葬物品的多寡,都随着当时社会的lun理思想、经济文化诸现状的变化而变化。仅以随葬品为例,在新石器早器。“所有死者都有随葬品,不是斧、镰,就是石磨盘和磨棒,或陶制生活用具。”'4'夏时认为“人死无知,用不堪用器物埋于墓中”;殷时认为“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于墓中”;周时认为“人死也许无知,也许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国并存、诸侯争战时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毁器”、“折兵”现象逐渐消失'5'。随着社会对“事死如事生,礼也”观念的认同,随葬品无论数量与质量也急剧增加和提高。中国墓葬在春秋时期尚无庇护后人的“职能”,尽管当时墓葬中出现了“礼崩乐坏”、“僭越无礼”的局面,究其实质,还是没超越墓葬礼制的范围。
如果说人的灵魂不死观念产生的早期,还能反映先民们文化进步的一面;那么,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这个观念也就被浸泡在无数生灵的鲜血里了。私有主、奴隶主以及封建统治者,为了死后仍能享受生前的富贵,除了随葬大量的陪葬品以外,还用活人殉葬。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是被纳入礼制规范的,也是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如商代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和武官村王陵大墓中,生殉、杀殉、杀祭的人数都在三四百人左右。从目前有关资料来看,距今约4200—3900年的齐家文化的墓葬中,便出现了殉人现象;到了殷商时期,殉人制度达到鼎盛。死者的权力越大,社会地位越高,殉葬的人数就越多。此后,西周初年殉人现象开始有所节制,直到明英宗皇帝临终前的遗诏废止殉葬制度,其间殉葬现象从未间断。中国历史上这种殉葬现象。人数之多、年代之旷久,为世界所罕见。
中国墓葬从单纯的亲情,发展到对神灵的敬仰,又被统治者异化,成为进一步奴役、愚弄、统治人民精神的一种工具,借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有一个长期的、社会的历史演绎过程。在氏族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母系社会,妇女成了初期农业的承担者和领导者。反映在墓葬中,妇女的随葬品往往多于男性,而且男女分葬。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男性逐步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居主要地位,从而逐步取代了女性的地位。在墓葬中出现了男女合葬墓,并且男性居中,女性仰身或侧身一旁。在奴隶社会时期,统治者为了强化其统治地位,往往在死后或祭祀祖坟时肆意杀戮大量的奴隶,并建造宏大的墓葬。中国墓葬到了封建社会,更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张扬到了至极。由于融入了“葬地兴旺”、“庇护后人”等迎合封建lun理观念的墓葬文化新内容,以致上到帝王将相有殡葬典制、下到庶民百姓有民俗民风,成了全民的自觉行为。所谓“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至幽之故也”,正是当时墓葬文化的思想基础。这种文化现象,确实将中国古墓葬的文化推向鼎盛,但由于掺杂了更多的封建道德lun理思想,甚至愚昧迷信观念,因此对后世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如果拂去依附在中国古墓葬上的二千多年封建迷信观念,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中国古墓葬的两个显著的本质特征:首先,墓葬能寄托、包容生者的亲情。其次,墓葬能反映死者生前权力的大小。前者是人性的必然,后者是社会的必然。中国墓葬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及形式(如墓葬、火葬、土葬、水葬、天葬、洞穴葬以及复合葬等),它的实质不外乎亲情与权力。亲情使得墓葬文化有了丰富的民众土壤,如河东旧时的丧葬礼,从病危到死后百日,包括了停尸、报丧、封棺、守七、择坟地、油棺、打墓、请祖、立神主、吊丧、送葬、守孝、成服等等'9'。还有的地方程序更为复杂,名目可多达五六十种。用其冗繁的丧葬礼的形式,来表达生者的哀思。权力又使得墓葬文化变得富丽堂皇。西周出现的“列鼎”墓葬,将奴隶贵族按等级的大小,规定使用列鼎的数目,大体可分为一、三、五、七、九,五个等级,其九鼎墓,为当时墓葬制度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到了战国初期,“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就坟头而言,孔子为了不忘亲情,以便识别,不过为其父母坟“崇四尺”高。可是刚过了几百年,修筑秦始皇陵时,其坟头的封土竟高达115。5米,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亲情与权力在墓葬文化中的作用。在整个封建社会,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12'。所谓“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过是统治者借厚葬先人,以宣扬礼教为表,炫耀权力为实,打出的一面欺世盗名的旗号而已。
中国古墓葬的出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同时,也派生出许多其他文化现象,给后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墓葬文化派生出的风水文化,又反作用于墓葬。这种反作用,不是制约了墓葬文化,而是逐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理念化,并溶入了“为了死者后代繁昌”的封建墓葬文化新内容。反过来,墓葬文化又成为风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墓葬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墓葬文化罩上了挥之不去的封建迷信阴影,因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古籍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墓葬与风水有关的书籍,不下几十种,有数百卷之多。“风水”作为专有名词,始见托名为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中:“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尽管这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很早就被人置疑,但该书将墓葬与风水相联系的基本观点,还是与墓葬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相吻合的。
墓葬与风水发生关系,是先民们对灵魂不死文化观念认同的产物。早在风水文化形成系统理论之前,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就已经渗入到先民们的文化意识中了。先民们基于亲情和灵魂不死的文化信念,对死者的葬地有了明确的选择。我们可以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来看,当时的公共墓地坐落于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深6米、宽6米、长约300米的大围沟把它与村子隔开。再从临潼姜寨出土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布局来看,其居住地的东、南两个方向,与公共墓地之间被两条壕沟阻隔,居住地的西面既无壕沟,又无墓地。因此,这几条壕沟与其说是先民们部落之间、人与兽之间的防御,莫如说是先民们文化意识中的一条生死阴阳界,是风水文化发展初期中的一个链节的真实写照。先民们的风水文化意识究竟萌发于“相宅”,还是萌发于“相墓”,其实,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没有墓、宅文化做为基础,就不可能派生出风水文化。风水文化意识,由初期的亲情,对死者的敬念,演绎成“为了后代的繁昌”,并上升为一种理论,似乎在秦汉以后才形成的。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韩信因家贫,母亲死了虽不能依当时的排场安葬,却因择了一块又高又宽敞的“旁可置万家”的风水宝地,竟成了韩信由布衣成为汉朝功臣的诠释,不仅被韩信的乡人所认同,就连太史公也点头称是。据《汉书。艺文志》提及的两本书即《堪舆金匮》、《宫宅地形》,以及东汉张衡的《冢赋》来看,韩信的择地葬母行为,确实是被当时社会特别是文化人所认同的。《幽明录》中儒生袁安为父求葬地,路遇三书生告之的故事,虽不足信,但表明当时文化人参予葬地的选择是风行的。
墓葬作为一种形式出现后,专事墓葬营生的工匠也随之诞生。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当然,早期的工匠水平不高,也许还从事其它的职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加上人们对神灵的敬仰、审美情趣的提高,专事墓葬营生的工匠职业应运而生。如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标识——人面鱼纹,是新石器时期葬小儿的瓮棺棺盖上的图饰,恐怕也是最古老的墓葬文化艺术家的杰作吧。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墓中的饰物、器物、俑以及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进入阶级社会后被王侯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寝、墓厥、墓碑、神道两侧的石雕、华表、石望柱等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工匠之手,并由墓葬派生出的一种文化艺术。仅以石雕为例,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早在秦代就有了神道前的石雕:“五柞宫有五柞树……树下有石骐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现见最早的实物是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其浑厚天然又气势雄健,是中国古墓葬的一组里程碑。每件石雕以原石为基础稍加雕琢,使之出现动人的形象,颇有中国传统的大写意的功力和效果。
第五百一十一章 宫殿与“墓地”
第五百一十一章 宫殿与“墓地”
其中马踏匈奴石雕最为后人所称道。是石雕群中的杰出代表,再现了霍去病当年率轻骑深入草原、驱匈奴于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从霍墓附近出土的两块石刻上的文字看:“大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造”,“以此推断,霍墓石刻可能是出于专为制作陵墓随葬品的专职作坊的工匠之手”。这些由工匠创造的石雕艺术,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如目前南京市的市徽,就是取自江苏南京江宁的梁临川靖王萧宏墓前石刻辟邪的形象;天安门城楼前后各有一对华表,也是“起标志作用的柱状建筑,上端镶有横板,原多木制,后改石制。唐宋以后,矗立在墓前的石望柱、石华表往往刻有装饰花纹,与石人、石兽等组合在一起,具有表示等级、炫耀身份的意义”。至于出自墓葬工匠之手派生出的其它文化现象,暂不一一例举了。
墓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为中国古典文学所重视与吸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素材,一类反映在神话、小说、笔记、传奇故事中,如《穆天子传》、《搜神记》、《吴越春秋》、《西京杂记》、《幽明录》等等。如果剔除其封建糟粕,有些作品就是在今天来看也是很优秀的。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等篇目,韩凭夫妇魂化鸳鸯。不仅表达了作者的良好愿望,也鞭笞了统治者的荒yin无道,其影响还可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化蝶”一场,祝英台投身梁山伯墓中,又化作美丽的蝴蝶,双一起飞出墓茔,一下子将人们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拾遗记》中“怨碑”一节,记叙秦始皇陵竣工后把筑墓的工匠活埋在墓内。汉初掘开陵墓时,发现工匠没死,还多出了一些石雕龙凤、仙人像和碑文辞赞,这些碑文就是被活埋的工匠所为。因为碑文都是表达的怨恨,所以叫作“怨碑”。这个故事以秦始皇陵为背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人民的悲愤,在幻想中寄托着强烈的反抗精神。韩国古代文豪崔致远少年来中国留学,考中进士后任溧水县尉时,曾游历当地的花山,在双女墓门上即兴题诗,事后梦见墓中二女与他幽会。崔以此事为题材,写出一篇名为《仙女红袋》的传奇故事,编进《新罗殊异传》并载入《太平通载》等文史典籍,千余年来,在韩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品中用墓葬作为题材或引子,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再一个高潮的出现是明清时期。最突